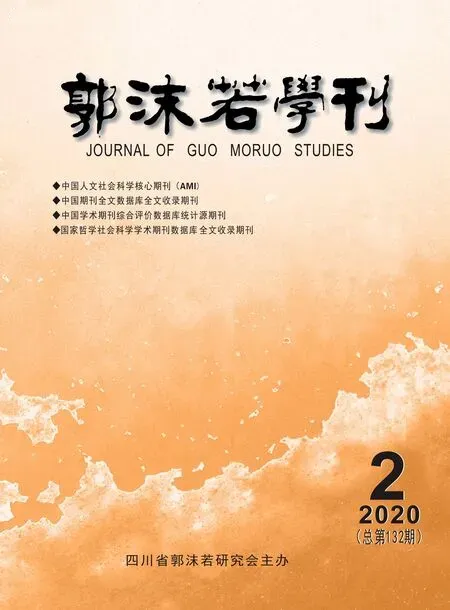郭沫若的文化價值取向
桑逢康
郭沫若的文化價值取向,是其文藝思想、藝術風格和政治立場鮮明而突出的集中體現,具有獨特性、時代性、階段性、前后一致而又多變的諸多特質。
眾所周知,郭沫若最初是以現代新詩登上文壇的,偉大的“五四”運動給他提供了最佳的時代契機。正如郭沫若自己所說:“個人的郁積,民族的郁積,在這時找出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將近三四個月的時間差不多每天都有詩興來猛襲。”①郭沫若:《序我的詩》,1944年5月重慶《中外春秋》月刊第2卷第3、4期合刊。每當這個時候,郭沫若的腦袋便成了一個灶頭;他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煙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煙霧,飛起火星,他的耳孔里還轟轟地只聽著火在叫;灶下掛著的一個土瓶──他的心臟──里面的血水沸騰著好像干了的一般,只進得他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郭沫若抓住這瞬間迸發出來的思想的火花,并及時把它們寫在了紙上。其代表作《鳳凰涅槃》,用古代阿拉伯神鳥自焚的一小則神話,植根到我國現實社會生活的基礎上,大大生發開去,創作出了一首充滿理想與激情的長詩,譜寫出了一部宏偉的中國更生的交響樂。詩中用“五百年來的眼淚傾瀉如瀑”、“五百年來的眼淚淋漓如燭”對歷史進行了總結,說明對于備受剝削和壓迫的人民群眾,對于備受侵略和欺侮的中華民族來說,歷史并沒有記載著什么幸福和歡樂,只有寫不完的悲哀和流不盡的眼淚,是一部辛酸的血淚史。這和魯迅通過狂人之口所總結的“這歷史沒有年代”,“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盡管寫作手法和表現形式有很大的不同。此外,郭沫若對青春幸福的懷念和對美好生活的眷戀,使詩人對丑惡的現實生活更加感到憤懣。他勸告人們不要在黑夜里做著“酣夢”,像“睡眠當中的一剎那的風煙”一樣庸庸碌碌度過一生,而要投入到推翻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偉大斗爭中去。詩人堅信革命能改造“身外的一切”和“身內的一切”,能改造中國,改造世界,一切的一切都要在革命烈火中受到考驗:或者被燒成灰燼,或者像鳳凰一樣在烈火中永生。
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熱情歡呼“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郭沫若在《女神·序詩》中也自詡為“我是個無產階級者”、“我愿意成個共產主義者”,并在《匪徒頌》中頌揚了列寧(1928年改版時又增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不過,《匪徒頌》盡管對“西北南東去來今”的一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宗教革命”“學說革命”“文藝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即革命者們三呼“萬歲”,但熱情有余,詩味寡淡,只有文學史和思想史的意義,即對研究郭沫若的思想演變提供了某種根據。
郭沫若的詩歌創作,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或曰時代特征。
詩人曾經在《湘累》中借屈原之口這么說過:“我的詩便是我的生命!……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創造,自由地表現我自己。我創造尊嚴的山岳、宏偉的海洋,我創造日月星辰,我馳騁風云雷雨,我萃之雖僅限于我一身,放之則可泛濫乎宇宙。……我有血總要流,有火總要噴,不論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馳騁!”①郭沫若:《湘累》,1921年4月上海《學藝》雜志第2卷第10號。《天狗》《晨安》《浴海》《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太陽禮贊》《梅花樹下醉歌》《我是個偶像崇拜者》,這些詩作充滿著狂風暴雨般的激情,既是詩人的自我表現,他幾乎把自己視為日月光電“全宇宙底Energy底總量”,像“滾滾的洪濤”一般“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郭沫若說他的詩不是“做”出來的,而是“寫”出來的,“一有沖動的時候,就好像一匹奔馬。”②郭沫若:《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于創作上的態度》,1922年8月4日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因此他的詩風雄渾豪放,汪洋恣肆,揮灑自如,總以表現自我為第一要著。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惠特曼《草葉集》的影響。在《我的作詩的經過》中郭沫若曾這樣說:“惠特曼的那種把一切的舊套擺脫干凈了的詩風和五四時代的暴飆突進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徹底地為他那雄渾的豪放的宏朗的調子所動蕩了。”③郭沫若:《我的作詩的經過》,1936年11月上海《質文》月刊第2卷第2期。不過,外來的影響如果沒有同自身的創作個性緊密融合起來,終究是身外之物而沒有外化入心,“內因”終究是起決定性的因素。
五四時期的詩人中受惠特曼影響的不止郭沫若一人,至少還有被某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譽為“詩哲”、“詩豪”的徐志摩。胡適主張“詩的原理”應以“明白”和“有力”為主要條件,徐志摩不盡以為然,他認為massively(雄偉、莊嚴)才是一個要件,其所作長詩《天寧寺聞禮懺聲》采用自由奔放的體裁與音節,讓胡適讀了更是覺得“氣魄偉大”。1923年10月25日胡適在日記中說:“英美詩中,有了一個惠特曼,而詩體大解放。惠特曼的影響漸被于東方了。沫若是朝著這方向走的;但《女神》以后,他的詩漸呈‘江郎才盡’的現狀。余人的成績更不用說了。我很希望志摩在這一方面作一員先鋒大將。”④胡適著:《胡適全集第30卷日記1923-192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頁。其實真正稱得上“先鋒大將”的是郭沫若而非徐志摩,《女神》早在1921年8月就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了,徐志摩的《天寧寺聞禮懺聲》寫于1923年10月,比郭沫若晚了許久。
讀者由于個性與興趣愛好的不同,對詩的感受與評價也會有差異,這實質上也是文化價值取向在接受層面上的反映。就我自己來說,我就不大喜歡郭沫若那些“啊啊!”“喲喲!”一個驚嘆號接一個驚嘆號的標語口號式的詩作,而比較喜歡《爐中煤》《地球,我的母親》以及《女神》之后寫的《天上的市街》《峨嵋山上的白雪》,正如徐志摩的詩我喜歡《再別康橋》并不欣賞《天寧寺聞禮懺聲》一樣。
郭沫若在詩的形式上是不拘一格的,他主張絕端的自由,絕端的自主。《女神》中的許多詩是自由體,徹底擺脫了舊的格律,但《爐中煤》在形式上卻是相當規整謹嚴的。全詩共分4節,每節5行,每行字數大致相同(6~11字),而且押韻。從思想內容和表達方式來說,它無疑是一首現代的詩歌,體現了現代人的思想感情和審美情趣,同時又具有較為整齊的段落和詩行,有著近似于古典詩歌一般的嚴謹和內在的神韻,讀起來有如音樂般的鏗鏘悠揚。開頭一節和最末一節均是“我為我心愛的人兒,/燃到了這般模樣!”這樣反復、呼應,使人讀后有回腸蕩氣之感。從藝術表現形式來說,《爐中煤》可以視為現代格律詩的一次嘗試。
以上種種都和他早期的文藝思想有直接的關系。郭沫若在1925年出版的《文藝論集》中,曾一再宣稱:“文藝本是苦悶的象征,無論它是反射的或創造的,都是血與淚的文學。”⑤郭沫若:《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于創作上的態度》,1922年8月4日上海《時事新報·學燈》。“文學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現,是我們人性中一點靈明的情髓所吐放的光輝,人類不滅,人性是永恒存在的”。⑥郭沫若:《論文學的研究與介紹》,1922年7月27日上海《時事新報·學燈》。郭沫若還把三種主要的藝術形式界定為:“詩是文學的本質,小說和戲劇是詩的分化”,而“詩是情緒的直寫,小說和戲劇是構成情緒的素材的再現。”總而言之:“文學的本質是有節奏的情緒的世界。”⑦郭沫若:《文學的本質》,1925年8月15日上海《學藝》雜志第7卷第1號。在他看來,詩是人格創造的表現,是人格創造沖動的表現,所以真正的詩人的詩,不怕便是吐訴他自己的哀情、抑郁,我們讀了足以增進我們的人格。詩的功能就在于此。
由上述文藝觀,決定了郭沫若的創作個性,創作個性決定了他選擇何種創作方法,呈現出了什么樣的藝術風格。而這一切的綜合,決定了他的文化價值取向。
浪漫主義是郭沫若詩歌最顯著的藝術特色,也是他運用最嫻熟的一種創作方法。
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是中外文學史上兩種主要的文藝派別,也是兩種主要的創作方法。一般來說,抒情的詩歌與詩劇較適于采用浪漫主義手法,而敘事的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以及傳記與報告文學比較適于采用現實主義手法。郭沫若說:“我個人傾向于浪漫主義跟現實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側重于主觀的創造與激情,幻想的表現,帶有新鮮生動的進步內容,我想,這是可以稱之為‘新浪漫主義’的。五四以后我和聞一多的詩歌,以及壽昌的戲曲,具有這樣一種共同的傾向,不妨認為是‘新浪漫主義’的前驅。”①郭沫若:《致陳明遠信》,《郭沫若書信集》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頁。
郭沫若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是在“五四”新文學中高擎浪漫主義旗幟的先鋒人物,他的那些成功的詩作充滿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部分小說和戲劇或其中的某些篇章也洋溢著濃厚的浪漫主義氣息。這同郭沫若的藝術個性有很大的直接的關系,郭沫若是一個偏于主觀而又外向的抒情詩人,熱情奔放,才思敏捷,幻想豐富,對外在事物(無論社會還是自然)的感受特別強烈且易受刺激與撥動。長于抒情、慣作奇想的浪漫主義最適合郭沫若的藝術個性,而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要求事件、人物、情節的藝術真實性,要求描寫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對于郭沫若來說很難做到,因為他不善于像魯迅那樣對社會現實進行深入的體察和深刻的分析。所以,用浪漫主義創作方法進行創作,郭沫若獲得了絕大的成功;反之,他一旦嘗試采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則往往失敗,個性和藝術性在很大程度上喪失殆盡。比如現實主義小說中人物的性格包括語言都是“這一個”而非“那一個”,讀者聽其聲如見其人,《紅樓樓》對王熙鳳的描寫就是很好的例子,但郭沫若的小說中,人物的語言(對話)和作者的敘述語言都是郭沫若自己慣常使用的語言,而非人物個性化的語言。相反,郭沫若小說、傳記、散文某些吸引讀者之處,恰恰是(或者說往往是)那些充滿浪漫主義激情的段落,《行路難》的結尾處那一大段就堪稱激情澎湃、詩意濃郁、哲理與抒情高度結合的精彩華章。
五四時期的“平民詩人”劉半農曾在致胡適的一封信中,用嘲笑的口吻說:“聽著《鳳凰涅槃》的郭沫若輩鬧得稀糟百爛”②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32頁。,這其中既有意氣的成分,也有創作方法的差異,胡適和劉半農的詩作基本上是寫實主義的。但郭沫若卻在宗白華、田漢(壽昌)那里尋覓到了知音,于是有了《三葉集》(即三個人的通信)的問世。宗白華稱郭沫若是“東方未來的詩人”③田壽昌等著:《三葉集·宗白華致郭沫若》,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年版。,聞一多自謂“我平生服膺《女神》幾乎五體投地”④顧一樵:《懷故友聞一多先生》,1947年《文藝復興》第5期。,聞一多和田漢還被郭沫若視為和自己同為新浪漫主義的前驅。
在現代文學史上,大概是出于國情的需要,現實主義成了主要的創作方法,為大多數進步和革命作家所采用,浪漫主義則受到歧視以至鄙視。郭沫若本人在世界觀轉變的過程中,也一度對浪漫主義采取了否定與批判的態度,甚至在聽到別人說自己是“浪漫派”的時候,都感覺著是在挨罵。一直到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了我國新詩發展的道路,提出:“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新詩)形式是民歌,內容應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對立的統一。太現實了就不能寫詩了。”這個講話為浪漫主義恢復了名譽,在肯定現實主義的同時也肯定了浪漫主義。在毛澤東講話的基礎上,后來出現并形成了所謂“兩結合”的創作方法,即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
郭沫若對毛澤東的上述講話衷心擁護,完全贊成。他當時的喜悅之情真是溢于言表,因為毛澤東說出了他想說而未便說或未敢說的話!過去那種“挨罵”的感覺隨之一掃而空,壓抑了很長時間的浪漫主義又重新在他身上復活了:“……在我個人特別感著心情舒暢的,是毛澤東同志詩詞的發表把浪漫主義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來,使浪漫主義恢復了名譽。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認:我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了。這是三十多年從事文藝工作以來所沒有的心情。”⑤郭沫若:《雄雞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頁。
郭沫若從本質上來說又是一個入世的政治詩人。特別是當他接受并逐步樹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同“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相接觸,并實際參加革命斗爭以后,郭沫若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的文學活動更是自覺地與政治活動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反映在創作上,郭沫若于1928年本著“作一自我清算”的精神①郭沫若:《離滬之前》,《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頁。,對其代表作《女神》進行了重大的修改,比如把《巨炮之教訓》中原先的“為自由而戰”、“為人道而戰”、“為正義而戰”改為“為階級消滅而戰”、“為民族解放而戰”、“為社會改造而戰”,就標志著他在思想上明確接受了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類似的例子還有《匪徒頌》,1928年郭沫若將羅素、哥爾棟改為馬克思、恩格斯,反映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變化,這時郭沫若已經成為一個共產黨人,并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作上述修改正是順理成章、合乎邏輯的事。不僅如此,他的詩歌創作告別了一度“低回的情緒”和“虛無的幻美”,在新的形勢下呈現出了若干新的面貌。
郭沫若的文化價值取向,因勢而變,與時俱進,具有階段性。
出版于1928年的《前茅》堪稱為現代中國第一部無產階級的詩歌集,詩人號召男女工人們“打破這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的“魔宮”,堅信“秉著赤誠的炬火,前走!前走!”就一定能“使新的世界誕生”。這些鼓舞人心的戰鼓式的詩篇,的確不愧是“革命時代的前茅”。《恢復》作于1928年初,是大革命剛剛失敗后的作品,憤懣之情溢于言表,希望的火焰仍在燃燒:“但不幸我們的革命在中途生了危險/我們血染了的大旗忽然間白了半邊/不過我們也沒有一個人在抱著悲觀/我們相信著革命是操著最后的勝算”。當革命處于低潮的情勢下,在黑暗如磐、腥風血雨的日子里,詩人更加清醒地意識到了肩上的重任:“我今后的半生我相信沒有甚么阻撓/我要一任我的情性放漫地引領高歌/我要喚起我們頹廢的邦家、衰殘的民族/我要歌出我們新興的無產階級的生活”。《前茅》和《恢復》兩部詩集中,郭沫若“以英雄的格調來寫英雄的行為”②郭沫若:《我的作詩的經過》,1936年11月上海《質文》月刊第2卷第2期。,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戰斗性與《女神》相比是進一步增強了,盡管當時受到“純藝術”的詩人們許多冷落的潮笑,但隨著革命的推進,郭沫若的這些戰斗的詩篇獲得了愈來愈廣大的讀者。
“革命文學”的口號是郭沫若率先提出來的,1926年他寫了《革命與文學》一文,較早地從理論上探討了文學與革命的關系,指出文學和革命是一致的,文學的內容跟著革命的意義而轉變。文章號召文藝工作者“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漩渦中去。”③郭沫若:《革命與文學》,1926年5月上海《創造周報》第1卷第3期。1928年有關“革命文學”的論爭爆發以后,他又陸續寫了《英雄樹》《桌子的跳舞》《留聲機器的回音》等文章,進一步闡述了對革命文學的基本見解。他認為“社會上有無產階級便會有無產階級的文藝”,而“無產階級的文藝是傾向社會主義的文藝”④郭沫若:《英雄樹》,1928年1月上海《創造月刊》第1卷第8期。。他主張文藝青年們“先要接近工農群眾去獲得無產階級的精神”,“要克服自己舊有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⑤郭沫若:《留聲機器的回音》,1928年3月15日上海《文化批判》第3期。郭沫若早在20上世紀20年代末就有如此見解,充分說明他不愧是革命文學的先行者之一。同時也需要指出: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以至30年代,革命文學在中國還處于草創階段,比較幼稚,許多標榜“革命文學家”的作品中經常出現標語口號式傾向。郭沫若也未能完全避免,因此他有些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
從歷史上看,同那些張揚個性主義,視“我”為唯一存在的“理論”相反,郭沫若早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當他接觸了下層悲慘社會并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始起,就改變了已往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思想,主張:“在大眾未得發展個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時,少數先覺者倒應該犧牲自己的個性,犧牲自己的自由,以為大眾人請命,以爭回大眾人的個性與自由!”⑥郭沫若:《文藝論集·序》,1925年12月16日上海《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7號。1948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又進一步闡釋說:“……須有‘我’自然是要緊,然而反過來主張無我,卻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失為最高的品德。”具體而又辯證地講,“對于為人民大眾的服務須無我,對于反人民的一切須有我。”⑦郭沫若:《關于“尾巴主義”答某先生》,香港《自由叢刊》第10種《欺騙必須揭穿》。郭沫若本人就是如此立身行事的一位典范。
換句話說,海內外有人攻擊他是消解了“自我”因而喪失了“人格獨立”的“御用文人”、“文學弄臣”,郭沫若自己卻認為一個人如能達到“無我”的境界,忘我地為人民大眾服務,方“不失為最高的品德”。否則,名為“大眾”,實則為“我”,就很可能成為“巨奸大憨”。他所謂的“無我”即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大眾服務,如魯迅那樣“附首甘為孺子牛”。
文學觀指導文學家的文學活動。從全國解放后郭沫若對收入《文藝論集》中的許多文章的修改,還可以看到他在文藝思想方面的諸多變化。
《文藝論集》初版于1925年12月,共包括論著31篇。在同年12月16日《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7號上發表的序言中,郭沫若說道:“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作風,在最近一兩年之內可以說是完全變了。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兩年之內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有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丟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的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由,總不免有幾分僭妄。”他主張“要發展個性,大家應得同樣地發展個性,要生活自由,大家應得同樣地生活自由”,并認為“這兒是新思想的出發點,這兒是新文藝的生命”。這些見解在郭沫若1925年以前寫的一些文章中雖然不無一些端倪,然而從大體上看來還是處在混沌的狀態,所以郭沫若把《文藝論集》看作是自己的“墳墓”、“殘骸”。如果進一步把1925年初版的《文藝論集》,和1958年郭沫若在《沫若文集》第10卷中對《文藝論集》所作的修改加以比較,就可以發現在許多文藝問題上郭沫若的觀點前后有顯著的差別,甚至可以說是判若兩人:
對于文藝本質的界說,郭沫若將原先認為文藝是苦悶的象征,改為文藝是生活的反映;原先強調作家個人的主觀感受,改為強調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原先認為藝術“是喚醒人性的警鐘”,改而認為藝術“是喚醒社會的警鐘”;原先主張文學表現人性,改為主張文學表現時代和人生;原先認為“人性是普遍的東西,個性最徹底的文藝最為普遍的文藝,民眾的文藝。其所生之效果對于淺薄的功利主義的通俗文藝,其相差之懸隔,不可以道里計”①郭沫若:《論詩》,最初發表于1921年1月15日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后收入1925年版《文藝論集》。,《沫若文集》中則改為:“人是追求個性的完全發展的。個性發展得比較完全的詩人,表示他的個性愈徹底,便愈能滿足讀者的要求。因而可以說:個性最徹底的文藝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藝,民眾的文藝。詩歌的功利似乎應該從這樣來衡量。”②郭沫若:《論詩三札》,《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339頁。總之,郭沫若原來把文藝看作是“苦悶的象征”,改變為視“文學是人生的表現”,“文學是批判社會的武器”③郭沫若:《暗無天日的世界》,《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頁。,是他文藝觀具有重要意義的變化。至于他摒棄唯美主義和人性的說教,承認“藝術本身是具有功利性的”④郭沫若:《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于創作上的態度》,《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5卷第226頁。,強調“生活的源泉”等等,則顯然是受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影響。
進入20世紀50年代,即新中國成立以后,郭沫若雖然像工廠批量生產那樣寫了許許多多的詩,但像過去那種激情燃燒的精品之作卻很難從他那里再尋覓到了。錢杏邨(阿英)用“死去了的阿Q時代”來批評魯迅固屬謬談,但用“逝去了的女神時代”來概括郭沫若后期的詩歌創作,卻是大致不差的。《新華頌》《長春集》《駱駝集》除個別舊體詩外,大都不成其為詩,而是流行于當時的一些標語口號和政治術語的堆積。說得客氣和文雅一點,是那個時代政治概念的延伸和詩歌樣式的排列,有的恐怕連“詩化”也談不上。有些作品(比如歌頌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鋼鐵等等)本來詩味就不多,藝術上相當粗糙,隨著內容的被否定更是成為了敗筆。關于國際形勢的詩作多系配合當時對外斗爭的需要,時過境遷,自然沒有多少流傳的價值。但作者飽滿的政治熱情還是應當肯定的,有一小部分詩寫得也還不錯,如《駱駝》《郊原的青草》《西湖的女神》《月里嫦娥想回中國》《波與云》等,感情真摯,想象豐富,比喻妥貼而又奇特,說明郭沫若詩魂猶在,詩風猶存,詩人畢竟是詩人。至于詩集《百花齊放》,拋開配合形勢這一點不談,也并不都是“白開水”,其中一些詩用比興的手法,人看花,花比人,寓有某些人生的經驗與生活的哲理,情趣盎然,還是值得一讀。如《芍藥》《梨花》《睡蓮》《山茶花》《榆葉梅》諸詩,昔日的“花之奴”翻身做了主人,花朵開得倍有精神;多愁善病的林黛玉如果生活在今天,一定十分健康……這些無疑都是詩人對新生活與新社會的贊歌。用山茶花比喻山地里的姑娘,“頭上帶著山茶花,哎呀,真好看!”生動活潑,富有生活情趣。“我們毫不名貴,也并不希望名貴”,作為普通一花是如此,人也應當具備這樣的“二月梅品格”。郭沫若去世前一年為關良畫作《醉打山門圖》所作的題詩:“神佛都是假,誰能相信它!打破山門后,提仗走天涯。見佛我就打,見神我就罵。罵倒十萬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①關良口述;陸關發整理:《關良回憶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頁。如果作為郭沫若的自題詩的話,不妨視為“五四”精神與其真性情的回歸。
總而言之,對郭沫若后期的詩歌創作需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具體的分析,不應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郭沫若說過他是“傾向于愛寫自己生活的人”②郭沫若:《我怎樣開始了文藝生活》,載香港《文藝生活》海外版第6期。,只要寫自己,只要自由地抒發自己的豪情,他就能寫出名篇佳作來,否則就寫不好甚至寫得很糟糕。“詩味不多,熱情有余;少有佳作,不乏敗筆。”──大概可以作為郭沫若這一類作品的評語。郭沫若本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說自己“詩多好的少”,又叮囑“不要把那些應景或酬酢之作收入我的文集”。③王朝柱、郭漢英:《郭沫若晚年二三事》,原載《書屋》1999年第5期。
郭沫若既是文學家又是歷史學家,兩者的最佳結合是他的歷史劇創作。在現當代文學史上,郭沫若的歷史劇不僅數量最多,而且質量最好。他是當之無愧的“中國歷史話劇的杰出代表”。
郭沫若是一位浪漫主義大詩人,他的歷史劇同樣充滿了浪漫的激情,籠罩著濃烈的詩的情調和詩的氛圍。最早的《棠棣之花》和《湘累》本來就是以“劇詩”的形式出現并收入詩集《女神》的,在以后的史劇創作中郭沫若將這一特長更是發揮到了極致。他的歷史劇總是將戲劇性與抒情性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以敘事為骨架,以抒情為靈魂,詩入劇,劇為詩,每一部波瀾起伏的歷史劇都是一首蕩氣回腸的長篇抒情詩。尤其是當劇情發展到高潮的關鍵時刻,戲劇沖突最為強烈的時候,主要人物面臨生與死、愛與恨、善與惡的巨大考驗,都會有激情澎湃、動人心魄的詩篇像火山爆發一樣奔涌而出,如《屈原》里的《雷電頌》,《虎符》中如姬在父親墓前的獨白等等,它們是人物內心的傾訴,靈魂的吶喊,是詩是雷是電是火是奔騰翻滾的長江大河。濃郁的詩情并不僅僅存在于這些精彩紛呈、膾炙人口的獨白中,而往往是時隱時現、時強時弱地貫穿于劇情的始終。這是因為郭沫若賦予歷史上的那些志士仁人以悲劇性格,極力謳歌他們為真理和正義而獻身的悲劇精神,因此許多劇中主要角色都是被他“詩化”了的完美人格,有著用生命和血肉凝鑄塑造的“詩的魂”。像屈原、夏完淳、聶政、嬋娟、如姬、高漸離以及段功、阿蓋這些藝術形象,本身就是詩,就是絕好絕美的詩,他(她)們屹立于歷史之巔,長存于天地之內,流芳于萬世,激勵并昭示后人于永遠。這是郭沫若的歷史劇給觀眾和讀者最有意義的啟示。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郭沫若的激情在史劇創作里反倒比在詩歌中保留得稍多一些。作于1959年的《蔡文姬》,郭沫若的初衷之一是通過重新解釋文姬歸漢的故事,謳歌曹操的文治武功,達到為其翻案的目的,以迎合現實政治上的某種需要。坦率地說,郭沫若的上述目的并未達到,他筆下的賢主(曹操)遠不如羅貫中筆下的奸雄(曹操)那么傳神;他所加在曹操頭上的光環遠不及羅貫中涂在曹操臉上的白粉那樣歷久不衰,使讀者傾倒。就為曹操翻案這一點來說,《蔡文姬》是失敗了的。然而這部歷史劇在另一方面卻達到了很大的成功,那就是作者主體意識、個人情感的充分展現:蔡文姬從遙遠的匈奴返回故土時的悲喜交集,她和左賢王及胡兒胡女兩個孩子訣別時的痛徹肺腑……這種種矛盾而又復雜的心情,正是當年郭沫若別婦拋雛,從日本回祖國參加抗戰的寫照。郭沫若在蔡文姬這個人物身上,“克隆”了自己的影子,再現了自己類似的經歷,相近的感情。他一再說過:“我寫《蔡文姬》含著很深沉的愴痛”④郭沫若:《致陳明遠》,第111頁。,“其中有不少關于我的感情的東西,也有不少關于我的生活的東西”,甚至說“蔡文姬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⑤郭沫若:《蔡文姬·序》,《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頁。演出時,每當舞臺上蔡文姬為思念一雙兒女仰天嘆息或掩袖而泣時,作為劇作者的郭沫若也禁不住淚珠滾滾……總之,郭沫若是用全部心血來塑造蔡文姬的,這也再一次說明:作為浪漫主義大詩人的郭沫若,他的感情有時會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
在郭沫若晚年寫的《李白與杜甫》中,也反映出了他的文化價值取向。郭沫若自小喜愛李白,不甚喜歡杜甫,更多的是個性與情趣使然。李白狂放不羈,自由灑脫,上天入地,斗酒百篇,均隨心而動,任性而為,在追求個性解放的少年郭沫若的心中,自然成為了崇拜的偶像和楷模。杜甫作詩太苦,一生過得也太苦,恐怕不是郭沫若這樣的青年人所樂意效法的。再說杜甫律詩的嚴格也會讓郭沫若受不了,那未免過于束縛思想了。以后他創造自由詩體,是打破了一切格律的束縛和限制的,而李白作詩“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于格律對偶”(引自趙翼《甌北詩話》),某些詩篇可以視之為唐詩中的自由體。不過,個性與情趣的偏好,不能代替嚴肅的學術研究,更不能完全左右對歷史人物的正確評價。當郭沫若成為著名的學者以后,尤其是當他成為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以后,他對李白與杜甫的評價減少了一些個人的感情色彩,在稱贊李白的同時,也說了不少肯定杜甫的話。郭沫若當然不贊成“揚杜抑李”,但也沒有走到“揚李抑杜”的地步,他基本上取的是“李杜并稱”的態度,用他的話來說李白和杜甫構成了中國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應當說這種態度是比較公允的,也符合大多數人對李白和杜甫的評價。只是郭沫若在書中評價李白與杜甫時,往往同一問題采用了雙重標準,有時不免失之偏頗。這正應了那句古話:“江山易改,秉性難移”。既然喜歡李白不甚喜歡杜甫是由郭沫若的個性與性情決定的,是他個人的藝術口味,所以很難轉變,前后幾十年來幾乎沒有多大區別。
對于同時代的作家,郭沫若按照自己的文化價值取向,高度贊揚了郁達夫的《沉淪》,說“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枯槁的社會里面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于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①郭沫若:《論郁達夫》,載《人物雜志》,1946年9月30日第3期。何以如此高的評價?因為郁達夫采用的同樣是浪漫主義創作方法,兩個人都同樣擅長抒發個人情懷,稍有差別的僅是郭沫若擁有更多的激情,郁達夫有著較多的感傷。郭沫若還肯定了曹禺的話劇《雷雨》“是一篇難得的優秀的力作”②郭沫若:《關于曹禺的〈雷雨〉》,1936年4月1日東京《東流》第2卷第4期。。
郭沫若和魯迅兩人氣質和風格迴異,雖然同在文化戰線上工作,卻從來沒有見過面;而且,在有些時候,在有些問題上,產生過尖銳的爭論,甚至以筆墨相譏。然而,他們戰斗的大方向始終是一致的,文化價值取向上的差異如同黃河長江匯入大海,在建立革命文學的道路上殊途同歸。正如周恩來所說:“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③周恩來:《我要說的話》,《周恩來論文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3頁。
文化價值取向屬于意識形態范疇,和政治立場緊密相關。郭沫若批判胡適,斥其“學無根底,僥幸成名,近二三年來更復大肆狂妄。蔣介石獨裁專擅,禍國殃民,而胡為之宣揚‘憲法’,粉飾‘民主’,集李斯、趙高、劉歆、楊雄之丑德于一身而恬不知恥。”④郭沫若:《斥帝國臣仆兼及胡適》,1948年2月12日香港《自由叢刊》第12種《渡江前夜》。又借為胡適改詩,嘲笑胡適作了蔣介石的“過河卒子,只得奉命向前。”⑤郭沫若:《替胡適改詩》,1947年1月30日上海《文匯報》。胡適早年對郭沫若有褒有貶,一方面說“他的新詩頗有才氣”,一方面又說郭沫若“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⑥參見胡適1921年8月9日日記,胡適著:《胡適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0頁。。晚年更是咒罵郭沫若為共產黨的“文化奴才”。在現代中國復雜尖銳激烈的政治斗爭中,兩位“文化班頭”的互罵均植根于敵對的政治立場。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一文中,分別對沈從文、朱光潛、蕭乾貼上與代表革命文化的“紅色”相對立的“粉紅色”、“藍色”、“黑色”的標簽⑦郭沫若:《斥反動文藝》,1948年5月香港生活書店《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文藝的新方向》。,也都是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批判,事出有因,不足為怪。問題主要在于意識形態范疇的文化價值取向,也會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發生某些改變,“否定之否定”的事情不時會發生甚至屢見不鮮,在郭沫若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在信念與宗旨的原則問題上,他是不會也沒有改變的,但對具體的人和事(包括作品)的評價卻往往變易多多。有人據此說郭沫若是“風流文人”,不過是皮相的見解,變與不變在郭沫若身上其實是統一的整體,“變”是郭沫若,“不變”也是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