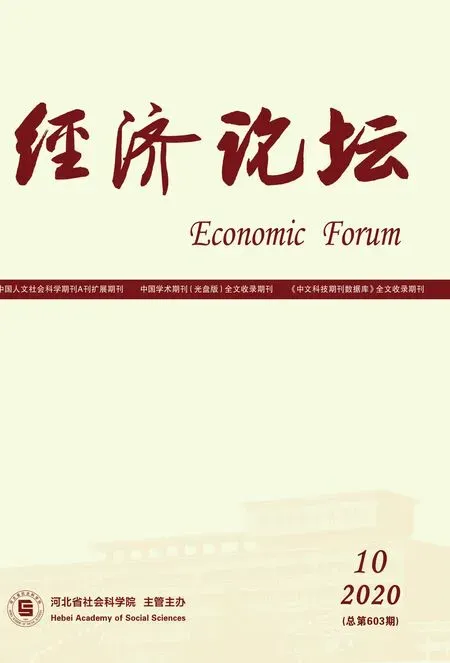黃河中段生態安全、重化工業升級與智慧綠色發展
魏曙光 姜宏陽
一、引言
黃河及其沿線地區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位置是毋庸置疑的。寧夏、甘肅、內蒙古、山西、陜西等黃河中段5省在發展資源型產業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資源密集型產業占比較高。長期以來,重化工業的大規模發展為沿黃中段各省的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經濟粗放式高速增長模式嚴重威脅到了黃河流域的生態安全,黃河流域生態本底脆弱,流域內生態承載力有限,地區環境容量緊張,工程性減排空間有限。一方面,重化工業的大規模發展在消耗大量水資源的同時帶來超出環境容量的污染排放,黃河流域以占全國2%的水資源總量承擔了全國近10%的污染排放,工業廢水排放量平均每年超40億噸左右,已遠遠超出水生生態的承載能力。工業用水增長擠壓了生態用水,導致水資源更加緊張;另一方面是地方環保基建滯后,企業和地方政府對于環保基礎設施的建設重視不足、投入不夠使得原本脆弱的生態更是雪上加霜。這意味著,如果在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不對環境污染加以控制,“黑色”經濟發展模式將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限制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的枷鎖。但是,考慮到當前黃河中段地區產業發展體系以及使用新能源成本,完全放棄重化工業發展是不現實的。黃河流域的高質量發展必須轉變觀念,變原有的“黑色”模式為“綠色”模式,對未來經濟發展加以“約束”。那么,應該如何將“綠色化”有效嫁接到經濟發展過程中,建立經濟與環境之間的平衡關系?面對這一問題,智慧綠色發展將成為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破局之選。
二、相關文獻回顧
(一)黃河流域生態安全研究回顧
生態本底脆弱和資源環境的高負載是黃河流域生態環境的基本特點。特別是流域內的高原生態系統、干旱與半干旱地區的草原或農業系統,脆弱性尤為突出,支撐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能力有限(金鳳君,2019)[1]。加上長期高強度開發,使流域內資源環境處于高負載狀態,以占全國2%的水資源總量,承擔了全國大約10%的污染(陳曉東、金碚,2019)[2]。
水資源供需矛盾制約了地區生態保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首先,黃河流域生態用水不足,2017 年黃河流域用水結構中,農業用水達64.86%,生活用水14.13%,工業用水15.06%,僅有5.93%為生態用水,可見,工農業和生活用水對生態用水造成擠壓,導致水環境自凈能力不足,進而加劇了黃河流域的生態污染(郭晗,2019)[3]。其次,寧蒙陜甘沿黃地區作為我國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傳統粗放型發展模式產生的工業污水、工業固體廢棄物等加劇了流域的環境污染、生態退化(董鎖成、李雪,2010)[4]。另外,重化工業的發展由于設備陳舊,工藝落后,不僅消耗大量水資源還造成水資源浪費嚴重,重復利用率較低,大城市的重復利用率僅為40%~60%,小城市更低(趙秉棟等,2003)[5]。
(二)沿黃流域重化工業發展研究回顧
黃河流域重化工特征突出,產業結構層次和綠色化水平偏低,2018 年陜西省能源工業增加值占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48.2%,寧夏重化工業增加值占全區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63.7%,流域內主要省份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銷售產值占本區規模以上工業銷售產值的比重普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姜長云等,2019)[6]。流域內市場化水平總體較低,2008—2016 年的數據顯示,除河南和山東外,黃河流域其余六省的市場化指數均顯著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王小魯等,2018)[7]。資源產業的繁榮一定程度上會抑制區域的創新活動(安樹偉、李瑞鵬,2020)[8]。2015年寧夏、甘肅、內蒙古、山西等的TFP貢獻率均不足10%,說明經濟增長仍然取決于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投入,創新驅動不足(張健華、張豪,2018)[9]。此外,由于產業支撐不足,黃河流域工業化與城鎮化發展的總體協調度較低,除山東、河南、青海外,其余省份的NU值均低于1.2,處于工業化滯后于城鎮化狀態,然而黃河流域面臨著工業化發展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突出矛盾,黃河流域推進綠色發展與產業轉型升級還任重道遠(魏后凱、王頌吉,2019)[10]。因此,提升重化工業發展層次,打造綠色環保、精致高端的重化工業發展模式就顯得非常重要(金碚,2014)[11]。
(三)智慧綠色發展的研究回顧
1989 年大衛·皮爾斯(David Pierce)在《綠色經濟藍圖》中首次提出“綠色經濟”的概念。Jack Reardon(2007)認為可持續性、生產和分配的本地化是綠色經濟的中心思想,并尊重生態的局限提倡更公平的分配資源[12]。國內關于綠色經濟的研究正在不斷豐富與深入,但還處于初期探索階段。胡鞍鋼(2014)認為綠色發展就是綜合考慮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為一體的發展道路,最終達到增加人類綠色福利,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目標[13]。具體來講,企業綠色發展與轉型是推進產業結構升級、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因此要健全環境評價和信息強制性披露,用嚴懲重罰的制度推進企業綠色發展與轉型(江濤,2020)[14]。另外,高管具有綠色認知,并采取前瞻性的綠色管理戰略對綠色技術創新、綠色生產以及末端治理企業綠色行為具有驅動作用,通過將節能減排作為創新目標,設計綠色產品、研發清潔技術(鄒志勇,2019)[15]。在依靠大數據驅動智能制造發展的同時,全面推行綠色制造,利用智能制造子系統的智慧化對綠色制造子系統進行合理規劃和利用資源,進而實現制造過程綠色生產效率最大化(王婷,2020)[16]。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重化工業對沿黃中段地區的經濟發展無疑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生態負擔。實現黃河流域的高質量發展,必須要妥善解決好重化工業的轉型升級與黃河流域生態安全的兩難問題。
三、黃河中段面臨的生態威脅
(一)能源礦產開發與自身生態脆弱相疊加,加重了中段地區生態壓力
黃河流域生態環境本底脆弱,關鍵性水資源匹配條件差,中段5省普遍氣候較為干燥,降水匱乏,地表蒸發量大,土地荒漠化嚴重,山西、陜西大部分地處黃土高原地區,植被覆蓋率低。但是,作為中國能源礦產資源富集區和加工區,黃河流域擁有支撐現代工業發展所需的煤、石油、天然氣以及各類金屬礦產等眾多關鍵資源。山西、陜西以及內蒙古西部地區是中國的主要煤炭產地,從2010 年開始到2019 年,這三個省的煤炭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大約60%,大部分煤炭開采都集中在呂梁、忻州、臨汾、鄂爾多斯以及榆林等這3.3 萬km2的范圍內,能源基礎原材料部門在地區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高達70%。此外,甘肅、山西、內蒙古等多地市還分布有鈾礦、鎳銅鈷礦、鉛鋅、鋁土等多種金屬礦。煤炭金屬礦區分布較多,不僅改變了地質構造,導致地面塌陷和地表植被破壞,還加劇了表層水資源的蒸發和水土的流失。據統計,全國水土流失總量大約為50 億噸,單單陜西、山西、內蒙古三地的年水土流失量就已經達到了16 億噸。總體來看,寧夏、甘肅、內蒙古、山西、陜西這些省份礦產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本底的沖突較顯著,對生態環境本底的脅迫程度較高。
(二)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致使空氣污染嚴重
沿黃中段5省以煤化、鋼鐵、水泥、焦化等重化工為主的產業結構和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導致空氣中污染物激增。圖1為2017年黃河中段5省的能源消費結構圖,2017年中段5省煤炭消費總量約為9.34 億噸,占到流域內煤炭消費總量的51.4%。工業二氧化硫與工業煙塵排放的高值主要集中于鄂爾多斯、包頭、陜西榆林、渭南,以及山西大部分地市,這些地區的能源基礎原材料工業部門占工業部門總產值的比重都在50%以上。巨大的煤炭消費導致烏海—鄂托克—烏斯太—石嘴山和汾河流域(包括運城、呂梁、忻州、臨汾)形成典型的煤煙型污染區,二氧化硫年均濃度值超標。另外,一些小型重化工企業,因為生產的技術水平不高,節能環保工藝設備落后,也會造成SO2、PM10、PM2.5等污染物濃度超標。加之大面積的露天煤礦開采造成地表土層破壞,棄土堆積,在干旱、少雨、多風的氣候環境下極易造成揚塵風險。
(三)重化工業發展加重地區水資源與水環境壓力

圖1 2017年沿黃中段5省能源消費結構
途經寧蒙陜甘晉五省的黃河中段流域降水稀少而蒸發量高,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用水需求超出了流域內水資源承載能力。由于煤炭資源開采和農業灌溉用水的增長,截至2010 年,內蒙古已有近34%的湖泊干涸。山西和寧夏更是全國水資源貧乏的省份,受氣候地形影響,多以季節性河流為主,水資源利用率不高,人均占有量較低,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1/5。水資源不足成為制約當地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由于煤炭資源優勢,流域內布局眾多能源化工基地,如寧東能源化工、山西煤化工基地等,而煤化工所需的大量水資源恰恰是區域最為缺乏和敏感的資源。另外,大規模能源重化工業產業發展導致流域結構性污染問題突出,2005 年黃河流域的工業廢水排放量為32 億噸,占污水排放總量的73.5%,這些工業廢水主要來自化學原料、煤炭開采洗選、石油加工和造紙等行業。工業用水增長不僅對居民飲水造成威脅,還會擠占生態用水引發生態問題,2017 年黃河流域水結構中,生態用水僅為5.93%,生態用水補水不足,一方面導致地下水水位降低,引發濕地萎縮,局部生態環境退化;另一方面導致水環境自凈能力不足,進而加劇了河流水質污染。
四、黃河中段重化工業轉型升級測度
(一)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為了更好地規劃重化工業升級和綠色發展方向,首先需要準確把握當前時期重化工業的發展水平。結合黃河中段5省重化工業發展實際,并參考王玉燕(2016)[17]、楊立勛(2016)[18]等構建的產業轉型升級評價指標體系,依據科學性、主導性、相對獨立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則,本文將選取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環境改善、產業結構四個方面共15 個指標來反映重化工業轉型升級發展水平。具體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黃河中段重化工業轉型升級評價指標體系說明
(二)數據來源與處理
以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五省為代表的沿黃中段區域既是能源資源富集區,同時又是生態脆弱區和重要的生態功能區。現下轄的沿黃城市共18 個(表2),作為全國能源、原材料基地,資源型產業已發展成為地區的主導產業,很大程度上起著支撐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重化工業轉型升級滯后不僅制約沿黃中段地區綠色發展,也造成了五省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因此,本文以這18 個沿黃中段城市作為研究對象,基礎數據來源主要來自于《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和各相關省市的統計年鑒等。為消除不同量綱的影響,本文擬預先對原始數據進行規范化處理。
(三)研究方法選擇
因為主流研究方法包括AHP、Delphi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等并未充分考慮客觀歷史數據的重要性,而十分主觀。為此,本研究擬用熵權TOPSIS法進行評估。熵權法是通過各個指標的信息確定每個指標的權重,并作為權重的熵權,在決策時客觀反映了某個指標在指標體系中的重要性,同時還強調指標權重隨時間的變化。故而,此方法非常適合區域經濟評價的相關研究,同時TOPSIS方法的思想核心以判斷決策問題的最優解和最劣解的距離為基礎,再通過計算出與最優解和最劣解的相對貼近度,從而實現對方案的優劣進行排序的目的。(杜挺等,2014)[19]。熵權TOPSIS 法的計算步驟:
①假設有m個被評估對象,并且每個被評估對象有n個評估指標,形成一個判斷矩陣:

②標準化處理:

③熵值的計算公式:

④定義指標j的權重:

⑤計算加權矩陣:

⑥確定最優解和最劣解

表2 黃河中段5省區18個沿黃城市

⑦計算評估對象與最優解和最劣解之間的相對距離:

⑧計算綜合評價指數:

(四)黃河中段重化工業轉型升級發展水平測度
為了對重化工業轉型升級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本文依據熵權法的計算步驟,算出重化工業轉型升級評價體系各指標的權重(表3)。運用TOPSIS 法計算出沿黃中段18 市重化工業轉型升級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數。
根據得到的2003-2017年重化工業轉型升級綜合指數(表4),觀察沿黃中段18 城市的重化工業轉型升級水平的整體分布特征以及變化趨勢。

圖2 重化工業轉型升級綜合指數變化趨勢圖

表3 重化工業轉型升級能力指標體系
從表4中可以發現,沿黃中段各市區重化工業轉型升級水平存在明顯差異。2003 年至2008 年各市重化工業轉型升級綜合指數雖然有微弱變動,但總體變化不大,均處于0.1~0.3 的水平之間;2008年以后鄂爾多斯、包頭和呼和浩特3市重化工業轉型升級綜合指數開始逐漸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呼包鄂特色經濟圈發展戰略的確立,呼包鄂城市群注重通過技術跨越、協同創新的共同發展來促進產業升級。以鄂爾多斯為例,通過加速整合淘汰落后產能,短短幾年間煤礦數量縮減了近85%,產能卻增加到1.7 億噸,形成了一大批擁有高技術設備,高機械化和強大競爭力的大型煤炭集團。2011 年榆林市綜合指數達到0.41,到2014年更是超過包頭市達到0.561的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是2011 年發布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明確將呼包鄂榆列為國家重點開發區,形成以呼包鄂為中心,以榆林為依托,以黃河沿線主要交通路線和產業帶為軸的空間發展格局,促進了優勢特色產業的升級和區域一體化的發展。
四、沿黃中段重化工業轉型升級影響因素分析
(一)研究假設
本文在借鑒產業轉型升級的相關理論及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構建影響重化工業轉型升級因素的SEM模型(見圖2)和相關研究假設(見表5)。
該模型中涵蓋了四個內因觀察變量為經濟增長、科技進步、環境改善、結構優化;一個潛變量為重化工業轉型升級;以及四個外因觀察變量分別為投資結構、人力資本、科技創新和經濟開放程度。其中,以重化工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來表示投資結構,重化工業投資的增加可以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教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表明了對人力資本的重視程度,傳統的重化工行業缺乏技術創新,這主要是由于研發人才儲備不足;以科技財政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來衡量科技創新的投入水平,黃河中段地區整體科研水平要明顯落后于東部發達省份,重化工業發展過程中新產品研發,節能環保等關鍵技術的發展嚴重制約了重化工業的轉型升級;以實際利用外資的金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反映重化工業發展的外向程度,黃河沿線城市的重化工業轉型可以借助“一帶一路”經濟帶建設和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程度,化解過剩產能,為國內產業轉型騰出足夠的時間和空間。

表4 重化工業轉型升級綜合指數

表5 結構方程模型相關研究假設

表6 KMO 和巴特利特檢驗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設(表5)。
(二)數據分析與討論
為確保SEM 模型是合適可以執行,首先需要對各個潛變量指標進行KMO 檢驗和巴特利特檢驗(見表6)。通過操作SPSS.17 統計軟件,發現該模型潛在變量的KMO 檢驗值是0.830,是大于0 的;同樣,巴特利特檢驗的卡方值也達到顯著性要求。因此,運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分析是可行的。
代入數據進行軟件操作,最終結果如表7 所示,所有指標數值均在參考判斷標準范圍內,這表明所構建的結構方程模型對本研究是適用的,具有較好解釋能力。
表8 和圖3 分別給出了參數顯著性檢驗結果和標準化以后的路徑系數圖。總的來說,所有路徑系數顯著性水平較好,除了“重化工業轉型能力<---經濟開放”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外,其他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假設關系全部得到支持。
第一,“投資結構”和“人力資本”這兩個變量的路徑系數均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標準化以后其路徑系數分別是0.22和0.21,表明投資以及人力資本對重化工業轉型升級具有較大影響。

表7 模型擬合指數

表8 模型的參數顯著性檢驗結果
第二,“科技創新”同樣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并且其顯著性水平最高,在進行標準化后其路徑系數為0.32,表明沿黃中段重化工業轉型升級顯著受到科技創新力度的影響。
第三,顯著性水平檢驗結果顯示,“經濟開放”的顯著性水平僅通過10%,而其標準化后路徑系數只有0.14。不難看出經濟開放對重化工業的轉型升級具有一定影響,但影響力度有限。
(三)結論分析
重化工業轉型升級是一個復雜、全面的系統工程。最終的模型結果描述了重化工業轉型升級各影響因素的相互關系,以及它們對重化工業轉型升級的影響路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科技創新和研發力度對重化工業轉型升級產生了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其影響程度最大,排在第一位。這充分說明現階段技術創新對于重化工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性。通過對技術創新與技術擴散兩方面施加影響,一方面提升生產要素的投入產出和要素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提升企業節能環保水平。黃河中段五省地區現有創新體系薄弱,科技研發人才短缺,大部分重化工業企業在技術、生產設備以及高端產品研發上都相對落后,企業產品更新換代周期長。而高質量發展要求企業在綠色發展領域同步提高,所以,重化工業成功轉型的關鍵在于科技創新特別是綠色技術的創新。

圖3 結構方程標準化路徑系數
2.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對重化工業的轉型升級具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影響力位居第二。人力資本水平對重化工業的轉型升級產生積極影響,影響力位居第三。這充分表明,固定資產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對于促進重化工業的轉型升級至關重要。重化工業具有高投資需求和高運營成本的特征,當前重化工業轉型升級的資金主要來源于企業自身投資、財政投資以及專項撥款等,融資渠道狹窄,無法滿足長期大量的資金需求。重化工業發展水平低,人才和文化準入門檻不高,居民和政府不會在社會教育上投入額外的資金,降低了對教育投資和人才培養投資的熱情,造成人力資本投入不足。因此,還要適當拓寬重化工業的融資渠道,加大人才投入,保證有效的資金支持和人才支持。
3.重化工業轉型升級受到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的影響是最弱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地區的對外開放水平還較低,各個城市的重化工業企業發展水平較低,產業集聚程度不高,對外競爭力不強。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沿黃中段地區能夠更加有效的利用對外貿易來拉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進而對重化工業轉型升級也會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因此,制定適當的引資政策,將發達國家的新產品和技術引入該地區,并通過技術、管理、市場等方面的經驗溢出提升本區域的技術管理水平。這將對黃河流域重化工業的改造和升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五、黃河中段重化工業升級和智慧綠色發展的提升路徑
重化工業的轉型升級是保障黃河中段生態安全,實現智慧綠色發展的核心和關鍵。我們既不能人為地排斥重化工業的發展,也不能盲目地要求其服務化和生態化。相反,有必要將經濟建設、工業化和信息化以及生態社會的建設統籌在一起進行。既要促進傳統重化工業的轉型升級,又要大力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崛起。同時,還必須以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來限制能源重化工業的無序擴張。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本文以打破制約重化工業轉型升級的技術、資金、人才和市場瓶頸為著力點,提出推動沿黃中段重化工業升級的智慧綠色發展路徑。
(一)堅持產業建設和生態建設并重
黃河中段地區具備鋼鐵、煤炭、化工、冶金等重化工業的發展優勢。一方面,將煤炭、鋼鐵、化工冶金等重化工業調整為產業轉型升級的主攻方向,逐步淘汰一些技術落后、污染較高的小型落后產能,加快整合融合,實現企業和產品“專、精、特、新”發展。積極擁抱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不斷提高生產過程的智能性和生態性,以及產品的精細化和高端化程度。在主導優勢產業的基礎上,積累更多的資金、人才和市場等競爭優勢,著力推動綠色生產,逐步調整地區產業結構,轉向發展綠色環保產業、服務業和高技術裝備制造業,形成地區經濟競爭新優勢。另一方面,在轉型過程中,必須緊緊扭轉發展方式的關鍵環節。以綠色為方向,以智慧為手段,形成“綠色+智慧”的經濟發展模式。以行業大數據及模型為技術手段,構建智能能源管理系統,對主要能源消耗企業進行監測和分析以便準確了解能耗情況,為企業節能改造、優化運行提供數據支持。
(二)強化綠色科技創新,在技術創新過程中引入生態理念
而傳統技術創新中資源保護與污染治理的缺點日益突顯,為了減少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需要將綠色技術創新帶來的高效生產模式引入企業生產過程中,以求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從而達到降低企業環保成本,帶動產業體系綠色化轉型的目的。加強企業、高校等在綠色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形成產學研用一體化的綠色技術創新發展聯盟,加強對設計、工藝、回收等關鍵技術的研發力度,構建引領重化工業升級發展的綠色核心技術體系。建立和完善綠色技術轉移與轉化市場交易體系,完善綠色技術創新成果轉化機制,加快科研成果從樣品到產品、從產品到商品的轉化。要立足于優化綠色技術創新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建設、營造良好的融資和社會環境,強化相關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加強國際合作開放力度,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肥沃土壤。
(三)加強綠色人才隊伍培養,提升綠色認知
人力資本對綠色發展的貢獻在于提高生態效率、控制環境污染和促進環境保護。教育的綠色化導向是未來教育體系改革的重要方面。一是加強幼兒園的綠色觀念教育,培養孩子的節能環保意識;高校應積極改變人才培養方式,調整專業設置,以適應產業結構升級和綠色發展的需要,并在職業技術學校開設與綠色制造、綠色營銷、綠色物流和綠色管理相關的專業,夯實人才基礎。二是加強綠色技術人才隊伍培養和更新,既要培養高水平科學家和工程師,也需要培養優秀的高級技術人員,將綠色理念真正融入生產;綠色人才不僅僅局限于科技人才,還包括管理人才、法律人才、外交人才等各個領域的專門人才,要重視各個層次人才比例的均衡。三是積極培養人們樹立環保意識,不斷提高環境認知能力和參與環境保護的主動性,使綠色發展理念真正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四)保障智慧綠色發展環境,不斷完善金融支撐體系
綠色發展是一場持久戰,需要更多資金支持。目前,重化工業行業絕大部分資金來源于企業自籌,但由于產業轉型升級所需的高技術本身具有沉淀成本大、風險高、融資難等特點,進而反映出強化風險金融支持、創新融資制度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一方面,統籌綠色金融市場體系建設,增加綠色金融在綠色產業服務中的占比,通過創新金融產品,設立綠色發展基金等多種形式,力求綠色金融在重化工業轉型升級中起積極推動作用。亦或是金融機構可以通過限制性政策對一些污染項目或污染企業不提供信貸支持,切斷其資金來源,強迫其不得不進行轉型升級。另一方面,通過建立政府特定的產業發展基金,以市場化為導向,引導資金向綠色產業傾斜,充分發揮金融杠桿的作用,確保資金融通和產業融合,保障綠色項目的建設和運營,限制淘汰落后產能,引導資金流向綠色工業部門。
(五)統籌產業布局,強化區域空間聯動發展
區域間產業呈現“雁行形態”是整個地區產業高級化發展的有效方式。從重化工業增加值來看,蘭州、銀川、呼包鄂地區明顯領先于其他城市,處于產業結構的“雁首”位置,其他城市相對落后,當屬“雁尾”。因此,要強化蘭州、銀川、呼包鄂等一些重點中心城市的產業集聚能力,調整產業布局,中心城市重點布局包括總部經濟、設計研發、高端制造或銷售等環節,逐步打造成創新、綠色的經濟引領區,以帶動黃河沿線重化工業轉型升級。同時,加快推動中心區重化工業和工程機械等傳統產業向具備承接能力的中心區以外城市升級轉移,在產業轉移地之間建立利益共享機制,增加對重大產業轉型項目的土地和融資支持,確保黃河沿線的重化工業都能先后實現轉型升級。另外。要實現黃河流域的綠色大發展,不能僅僅寄希望于各個城市的“單打獨斗”,而是要加快推進利用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設立并建設“智慧黃河”工程,打造黃河中段地區的生態利益和經濟利益共同體,將信息知識、流域管控和社會公共服務一網融合,實現智能監測環境問題、智慧管理企業運營、科學治理環境污染的一體化協同聯動。推進黃河資源和產業協同協作共贏,黃河生態共治共享,為黃河中段生態安全和綠色發展一體化利益共同體提供智慧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