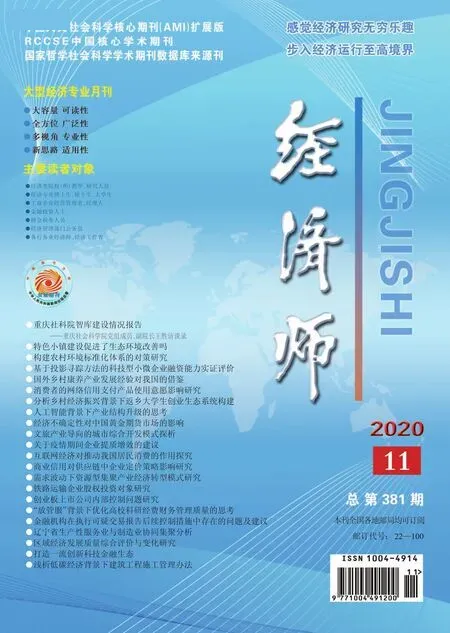農戶異質性對精準扶貧績效的影響
——基于我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空間計量分析
●左曉慧 劉思遠
一、引言
貧困問題威脅著社會的和諧穩定,與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本質相違背,所以國家一直非常重視脫貧攻堅工作。長期以來我國實施的扶貧開發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極大地改善了貧困地區人民的生活條件,顯著降低了貧困率。至2019 年,我國貧困人口已減少9000 多萬,貧困發生率降至歷史新低約0.6%,精準扶貧工作整體效果顯著。但并未取得根本性的勝利,貧困問題仍一直存在。而解決人民脫貧問題,首要任務應為精準識別扶貧對象,繼而針對不同類型的扶貧對象實施不同的扶貧政策。在全面小康的精準扶貧新時期,貧困人口呈分散式、碎片化特點分布,對精準扶貧績效的評估常面臨貧困率面板數據缺失、扶貧項目落實情況信息缺失等難題,難以形成科學的理論評估模型。因此,選擇何種方法科學地評估扶貧績效對扶貧政策目標實現極具重要意義。
二、文獻綜述
關于精準扶貧和精準扶貧績效評價的研究,國內外學者做出了巨大貢獻,研究成果豐富。本文梳理如下:
(一)精準扶貧的界定
貧困問題一直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脫貧工作將持續不斷地進行下去。國外學者從不同層面分析了貧困產生的原因,其中,Ragnar(1953)從宏觀層面以資本供求差異為視角探討得出貧困產生的原因在于資本的供小于求。
Rowntree(1901)從微觀層面將個人或家庭缺乏生產所必須的貨物或服務稱為貧困并運用“測算收入貧困線”界定貧困。而國內界定貧困一般選用微觀視角,以個人年收入為主的貧困指標評估個人貧困程度。為精準解決貧困問題,我國2013 年提出“精準扶貧”戰略。楊國斌、普戡倪(2020)認為我國“精準扶貧”戰略是對馬克思主義學派關于“消除貧困”相關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汪三貴、郭子豪(2016)指出精準扶貧應是扶貧政策和措施精準針對真正的貧困人口,通過針對性幫扶消除貧困。王錚、楊寬明(2019)指出現階段扶貧工作的重點應由盲目資助轉向重點扶持。呂若南(2019)指出精準扶貧重在“精準”貴在“精準”,要發揮好基層黨組織的作用將“精準”貫穿于整個扶貧工作中。參考上述文獻,本文將精準扶貧定義為:對符合多維貧困標準的貧困農戶,通過實施針對性的精準幫扶措施增加其可支配收入、提升其生活質量,使其脫離貧困。
(二)精準扶貧績效評價
在實施眾多精準扶貧新舉措之后,對于精準扶貧績效的考核,國內眾多學者并沒有得出相對一致的結論,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考核。一方面,正向來看,寧靜、殷浩棟(2019)通過PSM-DID 模型以及安慰劑檢驗,實證分析了產業扶貧項目對扶貧的正向作用。東梅、王滿旺、馬榮等(2020)以“產業扶貧”為例,基于三階段DEA 模型驗證了陜西省大部分貧困縣扶貧效率已達到最優。另一方面,李小云、唐麗霞(2015)等認為我國扶貧資源瞄準長期存在偏離,扶貧不夠“精準”。劉媛媛、吳玲(2020)指出當前在農村精準扶貧過程中存在著精準扶貧運行機制不科學、優秀人才匱乏、信息化程度不足以及扶貧主體較單一等問題。針對以上文獻研究得出的精準扶貧現有不足之處,本文為使精準扶貧目標盡快達成,從扶貧資源瞄準偏離以及扶貧主體單一等角度出發,以農戶異質性作為精準扶貧績效考核的落腳點,進而研究農戶異質性與精準扶貧績效的內在聯系。
(三)農戶的異質性及其對扶貧績效影響
不同農戶類型稱為農戶異質,Mancur Olson(1965)將異質性定義為資源分配不均等程度。楊曉云、鄧曉霞(2019)研究發現,中國農村家庭之間存在較為普遍的資產異質性。本文將農戶異質性定義為各農戶在個體因素與家庭因素兩方面存在差異。基于農戶異質性,何廣文、劉甜(2019)從農戶創業信貸需求差異角度,劉勝科、孔榮(2018)從農戶創業意愿層面,高富雄、趙丹丹(2020)等以耕地質量保護行為及耕地質量保護的選擇方式為視角研究農戶異質性對行為的差異,均得出一致結論:農戶異質性影響了農戶的異質行為。進一步,對于精準扶貧績效,劉魏、王小華(2019)通過對不同類型的多維貧困戶細分發現,土地流轉能夠緩解一般多維貧困戶的多維貧困,但對于極端多維貧困戶的影響效果并不明顯。
已有文獻對精準扶貧的界定及措施、精準扶貧績效以及農戶異質性單方面研究成果豐富,為本文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持。但從農戶異質性角度研究其對于精準扶貧績效影響的研究較少,該框架缺少文獻的支持和實證證據;并且已有文獻對精準扶貧績效的評估大多選定特定區域進行研究,忽視了省級間的空間效應。基于此,本文采用微觀省級數據,從省級層面考量農戶異質性對精準扶貧績效的影響并用空間計量模型進一步研究兩者的空間溢出效應。精準扶貧是現階段政策的關注點,本文的研究有利于政策制定者厘清政策重點,為精準扶貧更好地貫徹落實、全面脫貧提供理論支持。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2020 年是脫貧攻堅的關鍵時期,迫使我們對精準扶貧的績效進行考核。2013—2018 年我國各省級貧困率整體上呈逐年下降趨勢,說明我國精準扶貧戰略取得了大規模的勝利。但各省級貧困率依舊存在,劉媛媛、吳玲(2020)指出當前在農村精準扶貧過程中存在著精準扶貧運行機制不科學、優秀人才匱乏、信息化程度不足以及扶貧主體較單一等問題。在部分農戶長期難以脫貧,且國家精準扶貧機制運行不足的基礎上,本文基于農戶異質性對精準扶貧績效的影響做出如下理論分析并提出相應的研究假設。
1.農戶自身異質對精準扶貧績效的影響。農戶的自身因素包括農戶年齡、健康、性別、受教育程度等屬性,農戶自身因素異質影響了農戶生產能力及其脫貧能力。首先,隨著農戶年齡的增加、疾病發生率的增加,農戶勞動能力減弱、勞動時間減少,降低了能從增加勞動中獲得收益的可能性。其次,性別與勞動強度與勞動密度密不可分,男女農戶數量比例與勞動報酬直接掛鉤。再次,因教育投資帶來的農戶素質的提升將會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相應報酬,對精準扶貧績效影響顯著。基于此,本文建立假設1 及其子假設:
假設1:精準扶貧績效受農戶自身異質的影響。
假設1a:農戶的年齡對精準扶貧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1b:農戶的健康狀況對精準扶貧績效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1c:農戶的性別對精準扶貧績效具有負向影響。
假設1d:農戶的受教育程度對精準扶貧績效具有負向影響。
2.農戶家庭異質對精準扶貧績效的影響。農戶的家庭因素包括家庭規模、耕地面積兩個要素。農戶在農業生產經營中,所擁有勞動力人數以及耕地面積等資源稟賦的差異對農業產業發展績效影響重大。家庭所含勞動力數量越大,通過勞動獲得財富增加的可能性增加。家庭擁有的耕地面積越大,可供生產的可能性就越大,增加了農戶家庭脫貧可能性,兩因素對精準扶貧績效均具有顯著影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2 及其子假設:
假設2:精準扶貧績效受農戶家庭異質的影響。
假設2a:農戶的家庭規模對精準扶貧績效具有負向影響。
假設2b:農戶的耕地面積對精準扶貧績效具有負向影響。
3.農戶異質性對精準扶貧績效的溢出效應。從全國范圍看,本地區人力資本會對本地區的產業經濟發展影響顯著,且人力資本的空間溢出效應異質。本地區農戶年齡越大、健康狀況越差,本地區可進行勞動生產的農戶數量越少,本地扶貧產業職位的空缺會吸引周邊剩余勞動力流入,從而抵消了周邊地區部分精準扶貧績效。本地區農戶男性比例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本地扶貧產業發展越興旺,會帶動周邊地區上下游產業的發展,拉動周邊地區精準扶貧績效的提升。本地區農戶家庭規模越大,剩余農戶的外流擠占了周邊地區農戶勞動機會,抵消周邊地區部分精準扶貧績效。農戶耕地面積越大,在國家總耕地面積一定的假設前提下,就對應著周邊地區耕地面積的減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周邊地區精準扶貧績效。據此,提出假設3 及其子假設:
假設3:農戶異質性與精準扶貧績效存在空間溢出效應。
假設3a:農戶的年齡與精準扶貧績效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
假設3b:農戶的性別與精準扶貧績效具有負向空間溢出效應。
假設3c:農戶的受教育程度與精準扶貧績效具有負向空間溢出效應。
假設3d:農戶的健康狀況與精準扶貧績效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
假設3e:農戶的家庭規模與精準扶貧績效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
假設3f:農戶的耕地面積與精準扶貧績效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精準扶貧的主要目標是減貧和可持續發展,本文基于楊國斌和普戡倪(2020)認為我國“精準扶貧”戰略是對馬克思主義學派關于“消除貧困”相關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以貧困發生率度量精準扶貧績效,為模型被解釋變量的衡量指標。貧困發生率越低,精準扶貧績效越好;反之,精準扶貧績效越差。
2.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為“農戶異質性”,在解釋變量的選擇上,將農戶異質性具體分為兩類:(1)以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四項為主的農戶自身因素;(2)以家庭規模、耕地面積兩項為主的農戶家庭因素。
3.控制變量。此外,考慮到目前農村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情況較多,而農戶外流又會影響到本地與周邊地區精準扶貧績效,為防止回歸結果出現重大偏誤,特將非農務工人數作為控制變量,用農村非農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來衡量。
(三)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中選取的數據來源于民政部和國家統計局,作為被解釋變量的“貧困發生率”用農村低保人數與農村總人數比例衡量;解釋變量中的“性別”變量用農村低保中男性人數占農村低保總人數比衡量,“年齡”變量用低保中0~14 歲和65 歲以上屬于撫養范圍的人數占農村低保總人數比例度量,“受教育程度”變量用本專科以上學歷占農村低保人數比衡量,“健康狀況”變量用鄉鎮衛生院入院人數占低保總人數比例衡量,“家庭規模”變量用家中勞動力人數占低保總人數比衡量。
本文以2013—2018 年31 個省級(不含港澳臺)共186 個樣本面板數據為基礎,構建空間計量模型來系統性分析農戶異質性對精準扶貧績效的影響以及兩者之間的空間溢出效應。主要變量描述如表1 所示:

表1 變量說明與數據來源
(四)估計方法與模型構建
通常而言,研究者們對扶貧績效的評估只針對扶貧措施落點范圍內,因此以往學者們在評估扶貧績效時大多局限于特定研究區域范圍內,例如:某集中連片區或某市、某地區等,且假定與周邊地區變量數據相互獨立、無交叉影響。而現實中大部分數據都具有一定的空間性,各省級間聯系密切,空間溢出效應是研究省級面板數據不可避免的問題。為更準確評估精準扶貧績效的全局性,本文充分考慮面板數據之間的空間相關性并選取空間計量模型作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模型。為驗證上述假設,本文選取2013—2018 年31 個省份(不含港澳臺)的省級面板數據為研究基礎,從農戶自身因素和農戶家庭因素兩個維度,采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農戶異質性對精準扶貧績效的影響以及農戶異質性與精準扶貧績效是否存在空間溢出效應。根據對前人研究成果的整理歸納以及本文實際研究目標,本文在空間計量模型的選擇上選用空間面板模型,空間面板模型形式構建如下: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為研究農戶異質性對精準扶貧績效的影響,現對186 個樣本面板數據中的 pov、sex、age、edu、hea、gro、fam、job8 個變量進行原始數據描述性統計,樣本數據描述性統計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2 樣本數據描述性統計
由表2 可知,作為被解釋變量的貧困發生率,所選取的31個省級中貧困發生率最大值為22.8%,最小值為1.03%,最大值與最小值差異大,由此可見,我國各省級精準扶貧績效參差不齊。在農戶自身因素方面,性別因素最大值與最小值相差48.9%,可見在本文研究時間區間范圍內某些省級男性在貧困農戶中占比較高。年齡因素最大值為50.6%,最小值為22.7%,相差一倍多,說明各省級貧困農戶中年齡差異較大。其余農戶自身因素中最大值與最小值差異均較大,說明各省級間農戶自身因素異質性嚴重。在本文研究時間區間范圍不大的前提下,農戶家庭因素中的農戶家庭耕地面積與家庭規模兩因素最大值與最小值差異明顯,耕地面積因素最大值與最小值相差60%,家庭規模因素最大值與最小值相差3 倍,說明各省級間農戶的家庭異質明顯。在各省級農戶異質性嚴重的前提下,各省間較大的精準扶貧績效差異可以初步判斷,我國省級間農戶異質性與精準扶貧績效密切相關。
(二)模型的估計結果
本文利用貧困發生率作為精準扶貧績效指標的被解釋變量進行空間計量分析。首先計算各年份的莫蘭指數以檢驗精準扶貧績效是否存在空間效應。本文通過stata 軟件進行估計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 所示。
由表3 可知,2013—2018 年各年份莫蘭指數均顯著,該結果有兩方面含義:
第一,莫蘭指數為正,說明我國各省份精準扶貧績效存在“高—高”“低—低”集聚現象,精準扶貧績效的分布空間關聯性強。

表3 精準扶貧空間自相關檢驗結果
第二,莫蘭指數顯著表明精準扶貧績效存在著明顯的空間效應,為了無偏估計各變量的空間效應,需運用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分析。
不同空間模型的效應產生原因以及解釋能力有差異,因此需要通過實證檢驗選取最佳的空間計量模型進行檢驗。
首先,應對空間模型進行LR 檢驗,通過檢驗自變量空間滯后項及空間效應是否顯著來判別是否為SEM 模型。其原假設為:
H0∶θ=-βP
其次,對空間計量模型進行Wald 檢驗,檢驗自變量空間滯后項與空間效應是否為0 來判斷SDM是否退化為SAR,其原假設為:
H0∶θ=0
2 項檢驗統計量如表4 所示:

表4 各檢驗統計量
表4 檢驗結果顯示,LR 檢驗與Wald 檢驗均顯著拒絕了H0∶θ=-βP 與H0∶θ=0 原假設,則表明SDM模型可以很好地擬合數據,SDM模型并不能退化為SEM或SLM模型。因此,本文在進行空間計量分析時,初步判定應選用SDM模型進行檢驗。

表5 不同模型效應對比的擬合效果
表5 顯示SAR、SEM、SDM在隨機效應、時間固定效應、空間固定效應以及雙固定效應檢驗下,SDM在各效應檢驗下擬合數據程度均優于其他兩種模型,故進一步采用SDM模型進行空間計量檢驗。
再次,一般來說,當對指定變量進行樣本數據回歸分析時,在固定效應下模型回歸更為合適。表6 列示了不同固定效應下SDM模型的MLE 檢驗結果:

表6 固定效應下SDM 模型的MLE 估計結果
由表6 可知,時間固定效應與時間空間雙固定效應的空間相關系數rho 均顯著為負,而空間固定效應模型顯著為正。空間計量模型下,數據擬合效果的優良性由Log-likelihood 值表示,Log-likelihood 值越大表明擬合效果越好,時間空間雙固定效應的Log-likelihood 值最大,為574.9345。因此,本文選用時間空間雙固定效應進行實證研究分析。
針對雙固定效應下SDM模型的適用性,本文進行了進一步的檢驗,檢驗結果如表7 所示。

表7 SDM 模型適用性檢驗結果
上表LM 和穩健性LM 的檢驗結果均顯著拒絕了SEM 與SAR 模型嵌套于SDM的原假設,故更加證實了SDM的實用性。Hausman 檢驗結果顯著拒絕了選用隨機效應的原假設,因此驗證了固定效應的適用性。
進一步對采用時間空間雙固定效應下的SDM 模型進行空間效應分解,分解的系數估計值如表8 所式。其中,直接效應為解釋變量對本省份被解釋變量的影響,間接效應為解釋變量對鄰近省級被解釋變量的影響,總效應為兩者之和。

表8 雙固定效應下SDM 模型空間效應分解結果
農戶性別因素對精準扶貧績效的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分別為-0.035、-0.010,表明農戶中男性比例越大,貧困發生率越低,進而促進了本省與鄰近省級精準扶貧績效的提升。農戶年齡因素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分別為0.172、0.406,說
明農戶年齡越大,貧困發生率越大,不僅對本省級的精準扶貧績效有正向影響,而且對鄰近省級也表現出正向空間溢出效應。受教育程度的直接效應顯著為負,表明農戶受教育程度越高,對本省和鄰近省份的貧困發生率均有減弱作用。健康的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為0.016 和0.024,農戶入院次數越多,貧困發生率越高。耕地面積的直接效應為-0.001,說明了農戶家庭所擁有耕地面積與精準扶貧績效的負向關系。農戶家庭規模的間接效應為0.024,說明農戶家庭規模對精準扶貧績效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最后,非農務工人數的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均為負,說明了非農務工人數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
以上實證結果大部分驗證了本文的3 項假設,而農戶家庭規模因素的直接效應以及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積的間接效應檢驗結果與假設相反。經進一步研究發現,農戶家庭規模擴大,家庭生活負擔加重,因此與精準扶貧績效成正向影響;受教育程度在教育資源一定的前提下確對精準扶貧績效成正向溢出效應;而耕地面積負向空間溢出效應的原因在于由于市場的存在,資源的流動性拉動了周邊地區的扶貧績效。
(三)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上述結論穩定性,最大程度降低結果差異。通過替換回歸模型以及固定效應,選用空間固定效應下的SAR 模型重新檢驗,結果如表9 所示:

表9 穩健性檢驗結果
空間固定效應下的SAR 模型空間相關系數為0.0967,Log-likelihood 值為543.6502,數據擬合程度較高。故本文檢驗結果不受模型、固定效應與隨機效應選用變化的影響,均可以得出一致結論:農戶異質性對精準扶貧績效空間影響顯著。
(四)空間計量的局限性
本文選用的空間計量模型有一局限性:模型中所運用的空間權重矩陣并非根據數據的估計結果,而是研究者根據主觀設定,具有非隨機性,因此有無法完全反映不同省域之間復雜相互關系的可能性。
五、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基于我國31 個省份(不含港澳臺)2013—2018 年的相關數據,運用時間空間雙固定效應下的空間杜賓計量模型,分析了農戶異質性的不同表現對精準扶貧績效影響,實證結果表明:農戶異質性對精準扶貧績效有顯著的空間效應。具體結論如下:
1.各省份精準扶貧績效具有顯著的空間相關性,主要表現為“高—高”集聚與“低—低”集聚,從而形成鄰近省域間精準扶貧績效的同質性。
2.農戶異質性對精準扶貧績效影響顯著。農戶的年齡、健康與家庭規模三項影響因素對精準扶貧績效顯示出正向影響,其余影響變量對精準扶貧績效負向影響顯著。
3.農戶異質性對精準扶貧績效均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其中,農戶的性別與耕地面積倆因素對精準扶貧績效具有負向空間溢出效應,其余因素顯示出正向空間溢出效應。
(二)對策建議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結果,為了提升精準扶貧績效,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1. 根據農戶異質性建立多維貧困識別體系和精準扶貧瞄準機制。現有的貧困識別多以收入為主,應采取多維指標,建立以收入為主,其他指標為輔的多維貧困識別體系,精準識別貧困農戶。進一步依照農戶貧困原因的異質性實施不同的扶貧措施,豐富扶貧措施種類,精準對口扶貧。目前已有的扶貧項目大多未能與個體貧困戶相匹配,只是針對地區因地制宜,且部分扶貧政策難以落實,缺乏扶貧精準性。在常規扶貧舉措無法生效時,分析異質農戶貧困生成邏輯,采取針對性措施,降低“久扶不能脫貧”以及“主體缺位”的概率。
2.加大職業教育投入,提高貧困農戶自我發展能力。經研究調查發現,貧困地區大部分農戶僅受過基礎教育,對扶貧政策依賴度較高,為“輸血式扶貧”,政府資金投入壓力較大。基于此,一方面,對有脫貧能力但無脫貧意識的農戶進行在職培訓,增加其知識儲備,提高其脫貧素養。另一方面,對有脫貧意識但無脫貧能力屬于政策兜底的農戶,鼓勵加入農村合作社,以“能人帶動”形式幫助其提高生活質量,降低貧困風險。實現農戶脫貧由“輸血式扶貧”轉為“造血式脫貧”,降低貧困內生性以及陷入“貧困陷阱”的可能。
3. 鑒于貧困農戶發展生產資金來源大多依靠國家財政補貼和貸款,為避免稅收和還貸的負向影響,一方面,國家應評估貧困農戶潛在發展能力,設立最高貸款限額并設立多元還貸方式,減輕貧困農戶到期還貸壓力。另一方面,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完善土地流轉市場,廣泛吸收社會治理主體,實現互利共贏。
4. 增強扶貧績效檢測實時性。隨著現代化技術的進步以及近期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充分利用現代數字技術的實時性、完整性、準確性,構建數字化扶貧績效檢測體系,實時檢測扶貧措施實施進程與實施效率,及時增進優勢扶貧舉措、撤銷劣勢扶貧項目,提高扶貧措施的覆蓋廣度和實踐深度。
5.深化產業結構調整,開展多元扶貧措施。在農村耕地面積有限,剩余勞動力價值無法充分釋放的前提下,應深化產業結構、延長產業鏈、促進扶貧措施多元化發展。從研究結論來看,農戶家庭規模與非農務工人數負向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顯示勞動力人數越多,貧困發生率越低,精準扶貧績效越好。因此,應充分利用農村剩余勞動力,統籌協調,利用本地區的特色優勢,優化配套產業,開發特色扶貧項目,激發產業升級動力,防止勞動力資源的浪費。
6.加大與周邊省份的產業發展聯系,發揮區域作用。貧困的空間集聚效應要求扶貧措施應在省域層面推進農產業的協同發展,發展跨省域特色農產品加工業,建立省域間農民生產合作組織,打破潛在發展壁壘,加大區域經濟合作,擴大產業規模與規模經濟效應。增強扶貧舉措省域間上中下游的對接與耦合,實現鄉村振興和全面脫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