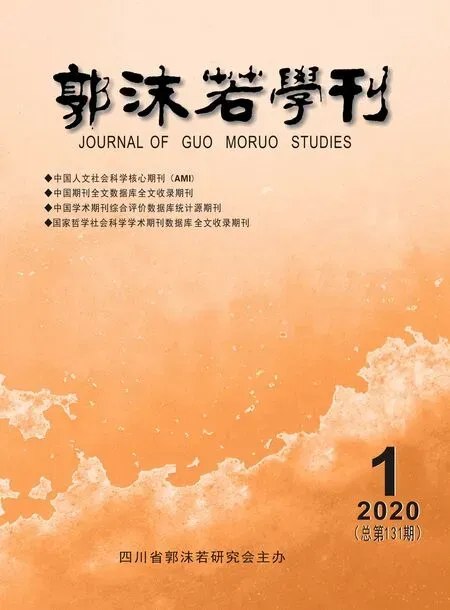《孔雀膽》的主題意識和演出效果
司空癡
劇作者:郭沫若,演出者:演劇二隊,地點:天津勵志社:
《孔雀膽》的主題意識,在去年春天讀劇本的時候便知道郭沫若先生和許多人都討論過了。而且也似乎曾引起了一陣論辯。《孔雀膽》的故事是大眾皆知的歷史題材。而創作歷史劇的動機可以統括的說:全是以歷史事件來作為現實社會的反映。這中間當然要含蘊了劇作者卓特而正確的思想與見地。李廣田先生將創作的動機分為四種:有一種稱為“由事實出發的創造過程”;另有一種稱作“由寓言故事出發的創造過程”。《孔雀膽》的故事可以視作一段歷史事實;也可以視作一個歷史故事。無論視作事實或故事,總是作者將自己的思想,批判像酵母一樣的揉合到事實或故事里,使死的事實死的故事活化起來,因此才使戲劇藝術的教育工作如蒲伯英在《戲劇之近代的意義》中所說“像再生一樣,不像別樣死教化,占據在人腦海的,就不容易抽換”。《孔雀膽》的創作動機我們由郭先生自己的話中知道郭先生的本意,最初是要將故事的重心放在阿蓋公主的身上,而一個重點是在民族團結,這凝結成為阿蓋的愛,和這對立的是車力特穆爾①“車力特穆爾”原文作“車里特穆爾”。的破壞。段功呢,則是把他放在副次的地位上。但是這一點卻又如同看過演出以后的郭先生也承認的,在演出上使觀眾得到的不是作者最初的創作動機,而卻在另一方面領受了深重的教育意義。郭先生說“在演出上,段功卻成了主人,因而主題也就更加隱晦了”。
正如所有的悲劇一樣的發展與結局,以寬大為懷,道義為本,主張“釋放一個人可以表示恩德,殺掉一個人不足以表示威武”的段功,因為他太把人當作人了;這種自以為是的善念,當然要造成自身的傾覆與滅亡。但是我們要作再進一步的追問,那將會毫不客氣的指摘段功的寬大與慈悲完全是一種動搖份子的妥協主義。因為他被梁王的偽善與阿蓋公主的情愛這兩條彩繩捆綁住,使他像他的好友楊淵海對他所下的批評說:“池塘里的荷花表面雖然開得異常繁榮,而它的根卻陷在深厚的泥潭里。”因此,他的自以為成功的錯誤觀念卻正是造成本身顛覆的因素。
郭先生說徐飛在《〈孔雀膽〉演出以后》的懇切批評是替他將孔雀膽的故事提醒了主題,又介紹徐飛先生的話說“造成這個歷史悲劇之最主要的內容,還是妥協主義終敵不過異族統治的壓迫,妥協主義者的善良愿望終無法醫治異族統治者的殘暴手段和猜忌心理。”是的。在異族統治者的殘暴手段和猜忌心理之下,一切妥協主義論者終究是將自己造成一個悲劇的人物而已。這種提示與批判的確是給觀眾們一個明晰的正確的提醒。當八年艱苦的抗日戰爭中間,我們敢很肯定的說是有著很多很多的人抱著妥協友善的政策,以企圖感化異族侵略者的正義與良心。但是在現階段的今天,我們更要申明而且強調一點,妥協主義者的善良欲望不是不僅無法醫治異族統治者的殘暴和刁詐,而且應該強調對一切統治者來表示這一種觀點的。即使是非妥協主義者的楊淵海卻為了另一種頑固的錯誤的觀念而陷于相似于段功的同樣的悲劇命運,但是這種以身殉友的忠誠我們也要視作另一種的妥協,因為本身自命為反對與惡勢力合流同污,主張與一切新的有生力量(故事中是指長江南北的一切義軍)合流的非妥協論者,但是我們要負責任的追問,為什么當一件艱辛重大的工作完成之前,輕輕的殉友來逃避開工作的崗位。
是的。“歷史是人類生活的腳印,這腳印說明著過去也提示著未來的路”。當我們讀完《孔雀膽》的劇本和看過《孔雀膽》的演出以后,我們承認我們領悟到《孔雀膽》的主題意識的指示。
現在我們就演劇二隊的演出作一個檢討。
我們首先要反對演出者對于原劇的任意刪改,這一點我知道是由于天津市的宵禁提前而作不得已的節刪,在現階段的惡劣環境之下是應該作退一步想的原宥,但是這一次的刪節,容易使觀眾產生一種誤解,也可以說是對主題意識的模糊觀念。例如第三幕中段功楊淵海審問提到的刺客,而暴露了統治者的陰謀,第四幕中在通濟橋旁行刺段功前一剎那化裝后的鐵知院對陰謀的態度,這一點對于觀眾的教育意義相當濃重,因為就演出上說,給神經錯亂的阿蓋公主清醒劑的化裝和尚,在觀眾意象中是很容易淡薄而疏略的。
就演員的表現技巧方面來說:飾王妃的張今呈似乎典型性格的不太適合,因此對于王妃的狠毒未能表現到淋漓盡致,王皇和羅泰都能將段功的沉毅①“沉毅”原文作“沈毅”。“王妃”原文作“王姐”。和楊淵海的忠義表現得恰到好處;飾阿蓋公主的梁國璋和飾車丞相的袁敏也確能把握住劇中人物的典型性格,尤其是梁國璋能將阿蓋公主的錯綜復雜的矛盾心理為觀眾的腦海里鐫刻上不可磨滅的印象。但是在服裝方面,阿蓋公主和施宗施秀好像應該有顯著的差異,例如施宗無意間偷聽到車丞相和王妃的陰謀的一場,很容易使觀眾認為是阿蓋公主(雖然第三幕中阿蓋自己有一個說明),開幕閉幕時燈光不能配合,象征火焰的效果不逼真,這一些后臺的問題是更特別需要顧及到的。
(原載天津《益世報》1947年11月24日第6版《別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