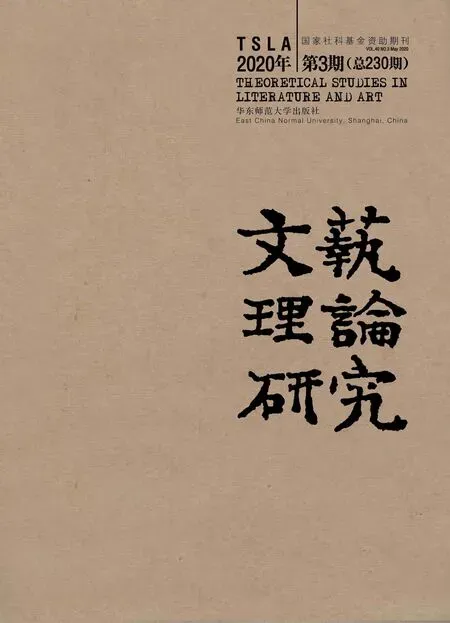報告文學,作為敘事性非虛構寫作方式
丁曉原
一
我們對報告文學這一文體最為基本的釋義,即它是一種新聞文學。顧名思義,這是由報告文學的文體名稱給出的詮釋。報告文學,既可解讀為“報告的”文學,突出它的新聞性、非虛構性,以區別于以虛構而成的文學;也可作“文學的”報告解釋,意謂與一般新聞寫作不同。學界對“報告的”文學研究,相對較為充分,基本義是新聞性,包括客觀真實性、時效性,擴展出時代性、現實性等含義。而對“文學的”報告,雖然相關的指涉很多,也有一些專門的研究,但總體而言,要么語焉不詳,要么未能及物得體。出現這樣的狀況,有多種原因。基本的原因是文學這個概念,似乎很難有規范統一的定義,文學的原初意思和后來的命意已發生了很多變化,中外對文學的理解也不盡一致。何謂文學,文學何以達成,內中具有一些不確定性。關鍵的原因則是文學各體,既有若干有關文學性的通義,也有相應的文學特性,小說、戲劇、散文和詩歌等文體,自有其文學的特征和文學性生成的要素。個性與共性的有機融合,才有可能真實地表征不同文體在文學性方面的建構和特征。這里,復雜的是我們對于文學各體文學性的認知很難抵達它們的本真,因此給出的一些表述無法反映文體的實際,離體甚遠。而這種情況在報告文學文體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基于近代新聞傳播而伴生的報告文學,是一種后來文體。一百多年來,這一文體在演進流轉中,沉淀凝結了如客觀真實的非虛構性、合時代受眾之需的現實性等一些基本特性。這些成為報告文學文體屬性的基本規定。相對于客觀真實性這一文體的“剛性”,報告文學中的“文學”則顯得富有彈性。在新聞性主導的作品中,報告文學的文學性較多地體現為真實地還原對象的客觀存在、語言表達的形象生動、適度的抒情導入等。因此這些作品往往可在新聞通訊和報告文學中跨體。到了文學的新時期,報告文學的結構形態開放多樣。在其中的集納式結構作品中,情節淡化,人物退隱,代之以鋪陳具有某種典型性的現象或問題。在這種類型的作品中,通常意義上的文學性已不復存在。而同樣在新時期,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癡情》和黃宗英、陳祖芬、柯巖的一些人物類報告文學,人物形象感人,篇章結構精致,語言表現力也較強,作品的文學性郁然可見。及至正在行進中的全媒體傳播時代,報告文學的形態和內容等發生著重要的變化。我們讀趙瑜的《尋找巴金的黛莉》、徐劍的《大國重器》、何建明的《浦東史詩》、李鳴生的《千古一夢》、王樹增的《解放戰爭》等作家的作品,表面的直觀是作品的長篇化。長篇作品在報告文學的寫作格局中占有很大比重,獲得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的作品,多數是長篇報告文學。與長篇化有著某種關聯的是作品內容新聞性的弱化。這種弱化不僅反映在史志類報告文學的規模化寫作上,也體現在現實題材作品內存的拓展與深化上。與內容新聞性弱化相對應的是文本故事性敘事的強化以及敘事中以人物為重心的設置。在這些作品中,文學性的面目與審美價值,與過往的報告文學又有了不同。由此可見,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是動態的。這種動態既與作品的題材類型、主題意旨、格局結構的不同有關,也會受到不同時期變化了的寫作審美取向的影響。因此,我們不能將報告文學作為一個固化的、封閉的、靜態的文體來討論它的文學性話題,而應當將其置于一個變量的視角下加以觀察。這種變量,既有報告文學與文學大類融通后的相異,更有其內部不同時空、不同結構作品間的轉承中的應變。也就是說,我們應在報告文學與文學其他門類、報告文學文體內部諸種存在的關聯和區別之中,尋找探討報告文學文學性話題的有效路徑,以獲得具體的、真實的文學性圖景和文學性達成的可能。
二
無論我們怎樣定義報告文學,都不能無視它作為一種文學的門類這一前提。因此,在報告文學這個指稱中,“文學”是它的中心詞,給出了它在文學中的定位,“報告”是其定語,規定了這種“文學”的特殊屬性。這是我們討論報告文學應以明確的基本邏輯框架。文體文學既有它的廣譜性,也有它的獨特性。因此,需要對討論的對象作一限定。這意味著討論的有限性,但正是這樣的有限性設置,才有可能獲得研究的有效性。我們在這里將報告文學界定為一種敘事性非虛構寫作方式,或寫作藝術。在這一界定中,“報告”中本有的新聞性由非虛構性置換。這種置換并不是主觀的任意而為,也不是對美國命名的非虛構的盲目跟風,而是基于對這一文體現實存在和發展趨勢的把握。我并不贊成隨意地以非虛構替換報告文學。“你現在翻開的,是一本關于敘事性非虛構文學的創作方法與技巧的書。千萬不要被‘敘事性非虛構’(narrative nonfiction)這個專有名詞嚇倒。相信我,這只是翻譯的問題。”(哈特1)“‘敘事性非虛構’作品就是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這類說法。我們只要稍稍回憶一篇叫作《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的文章,就能知道究竟什么是‘敘事性非虛構’作品。”(哈特1)這是美國杰克·哈特《敘事性非虛構文學寫作指南》中譯本譯者序言中的一段表述。譯者將被一些人提抬得高玄的非虛構落到了實處。非虛構其實就是所謂的紀實文學,而報告文學是非虛構大類中的一種主要的文體。但杰克·哈特的“敘事性非虛構”為我們重新認知報告文學提供了新的路徑,而這種新路徑正好契合了報告文學在新的媒體生態中所出現的敘事變化。移動終端等十分便捷且具有交互功能的傳播方式,消解了報告文學寫作原有的新聞性優勢。新的傳播和接受方式使得我們自主或被動地生活在碎片化的信息包圍之中,這些信息許多是以實時的文圖聲像融合的方式傳播。很明顯,面對這樣的媒體存在,那種作為新聞替代品的報告文學,已失去了它的基本價值。讀者閱讀報告文學并不在乎作品報道的人物和事件等的時效性,吸引他的主要是所寫內容的客觀真實性,即非虛構性。也就是說報告文學淡去了它的新聞時效性,強化的是新聞背面與新聞關聯著的非虛構故事。正是在這里,報告文學建構起文體自身新的優勢。
在這個界定中,另一個重要的關鍵詞就是敘事性。過往報告文學的文體特征研究,將新聞性、文學性和政論性等作為它的基本特征,很少涉及其文本構成的敘事性。政論性曾經是報告文學的重要特征,作者在書寫客體時會擇機主動出場,以敘議結合的方式直接揭示其中的意義,或歌詠禮贊,或沉思批判。但現在這種方式已不流行,作者和讀者公約的是讓意義內含于作品敘寫的人物事件之中。文學性作為報告文學的特征,這是它的題中應有之義。關鍵是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怎樣實現,對此言說者可能會從現場感、人物表現、結構方式、語言表達等方面加以論述。報告文學文學性的這種散在形態相對容易指說,但實際上在寫作文學性的達成中具有總體性的集成點。這個集成點主要體現在作品的敘事建構這里。這一點對于報告文學文學性的認知和實現具有重要意義。這一判斷首先是建立在報告文學作為再現性文學類型這一邏輯基礎之上的。根據文學敘寫對象、表達方式和基本功能等的不同,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再現性文學樣式和表現性文學樣式。再現性文學主要通過敘述、描寫等方式,真實形象地反映社會生活,人物、情節(故事)和環境(社會的、自然的)等構成了這一文學類型的要素。無疑,就報告文學的基本類型看,它屬于再現性文學樣式,是敘事文學的一種。在這一點上,報告文學和小說一樣。過往,我們只是強調報告文學的新聞性,只看到它與小說的區別,而忽略了報告文學內在的敘事性,無視它與小說的關聯。這從某種程度而言,表明了我們的研究缺少系統辯證的思維品質。其實,現代文學的前輩茅盾早在80多年前就曾指出報告文學“它跟報章新聞不同,因為它必須充分的形象化。必須將事件發生的環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寫著,讀者便就同親身經驗”(茅盾5)。“好的‘報告’具備小說所有的藝術上的條件,——人物的刻畫,環境的描寫,氣氛的渲染等等。”(茅盾5)茅盾的論述非常到位,一方面他給出了報告文學“新聞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他又明確地以“必須充分的形象化”,將它與“報章新聞”作了區別。“充分的形象化”是文學之為文學的基本前提,當然也是報告文學作為文學樣式的要素。何以“充分的形象化”,在茅盾看來,就當“具備小說所有的藝術上的條件”。這就是說,報告文學作為敘事文學樣式,其文本的基本構成與小說一樣主要是敘事,只不過小說的敘事內容是基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作者根據敘事的意旨,通過虛構想象、雜取種種等手段,結構出人物、情節、場景等敘事材料,而報告文學的敘事生成由書寫對象的實際存在給定,作者通過深入的采訪,多方的尋獲,以掌握更豐富、更具體、更接近本真的材料,作品的敘事內容是基于生活而“少”于生活。所謂基于生活,意指報告文學的敘事來源于對象本身已然的存在,作者不能以虛構越出這種已然存在的人與事、物與景等邊線。這里的“少”于生活,其大意包含在基于生活的表述之中。另外,“少”于生活,還指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性,決定了它只能是一種選擇性的寫作,即從已經掌握的有關寫作對象的素材中,選擇最能真實反映對象實際又能有效表達寫作主旨的材料。這里的真實反映,并不是對寫作對象作一地雞毛式的自然主義復寫,而是要求作者運用眼光發現并擇取其中具有典型性和表現力的對象加以呈現。這樣,寫入作品中的材料自然要比獲得的素材“少”,而這樣的“少”,既保證寫作的客觀真實性,又能以少總多,使作品的文學性達成有了可能。這是報告文學與小說在敘事生成方面最為殊異之所在。
正因為如此,所以報告文學寫作是七分采訪、三分書寫,真正的功夫要用在包括采訪在內的周詳細致的寫作準備上。有經驗的報告文學作家都深諳這一事理。“我一直秉承報告文學是‘走出來的文學’”,報告文學寫作“很大程度還取決于采訪是否到位”,“沒有采訪的寫作,不能稱之為報告文學”(黃傳會253)。黃傳會的體會從他長期的報告文學寫作實踐中得來。從某種角度而言,報告文學與其說是作者用筆寫就的,不如說是用腳走出來的。在文學諸體寫作中,無疑報告文學是最需要作者勤勉踏實的腳力、慧眼識珠的眼力的。這是作品寫作的前提,也是它價值生成的保證。寫作了“中國三部曲”《甲骨文: 流離時空里的新生中國》《尋路中國》《江城》的美國記者作家彼得-海斯勒(Peter·Hessler,中文名何偉),也很認同采訪對于非虛構文學寫作的前置性意義。他以其代表作《尋路中國》(CountryDriving)為例作了現身說法:“我就不能夠編造那些十分具有戲劇性的情節,比如工業事故、群毆或者犯罪之類的橋段。但是這意味著我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每一個作為個體的人的身上,關注他們平淡生活中的戲劇性。”“我需要更努力,更加專注,才能夠挖掘出這些細節。這也是我醉心于非虛構文學的原因之一。在創作非虛構文學時,不能夠編造,這就意味著你要竭盡全力去發掘事實,去收集信息。”①在海斯勒看來,“實事求是地還原現實生活”,是非虛構文學的價值所在和價值實現的方式。而要做到這一點,作者就必須“要竭盡全力去發掘事實,去收集信息”。而這才是一個優秀的非虛構寫作者應當具有的態度。不僅如此,采訪更具體的意義還在于:“深入采訪是對寫作對象的全面認知,以期獲得最飽滿的現場感和精彩的故事,挖掘到最鮮活的細節。”(黃傳會253)海斯勒也有“挖掘細節”,關注“平淡生活中的戲劇性”等近似的言說(黃傳會253)。“最飽滿的現場感”“精彩的故事”(“戲劇性”生活)和“最鮮活的細節”,這些構成了報告文學敘事不可或缺的要件,也是“文學的”報告文學性得以落實的關鍵點。正是在這里,可見報告文學的文學性存在于寫作對象本身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真實性亦即文學性,需要作者用力尋找,用眼發現,用心呈現。這是報告文學文學性生成不同于小說的最重要的特點。
三
如果將報告文學界定為一種敘事性非虛構寫作方式,或寫作藝術,那么相應地,我們就應當認同敘事文學寫作的某種“共識”:“敘事需要三大支柱: 人物、動作和場景。排在第一位的是人物,因為人物能夠推動動作和場景的發展。”(哈特74)這種共識實際上是常識。不只是意謂更普泛意義上的文學是人學,更是基于敘事文學內部結構組織的認知。敘事文學緣事而成,事又因人而生,同時人和事的存在離不開特定的時空場景(環境)。這樣,人物、事件(動作,情節)和環境(場景),就成為敘事文學敘事生成的三個基本要素。但這種情況在報告文學這里有些時候并沒有形成自覺。這是因為報告文學曾經有過某種作為敘事文學的非典型性,或者可以說是異敘事文學性。由此,直接影響到對報告文學文體建構及其價值的判斷。“報告文學在徹底擺脫其他文學樣式的時候,不要有一種羞羞答答的纏綿,這種纏綿不能要。這并不意味著報告文學本身不需要藝術性,比如小說家一直認為文學是人學,要寫人,我認為對我們報告文學家來說束縛最大的就是這東西。我指的是將來,還不是現在,最后的突破也將在于此。這個口號老是在束縛我們,可我們還一直堅信文學就是這個東西。它可以是人學但也可以不是,不一定非得要去那樣形容。報告文學在寫人時與小說絕對不一樣,用得著的時候就把人物拉過來,用不著就把他扔掉。我覺得整個文學最后將突破所謂人學這種模式。”(麥天樞 尹衛星等16—17)現在我們閱讀20世紀80年代報告文學作家尹衛星的這一段觀點鮮明的文字,感覺有一些突兀和費解。但如果將其置于當年的語境中,就很容易理解話意了。尹衛星很明確地主張報告文學與小說分離,否認報告文學寫人的必要性。這是他基于自己的寫作實踐和對1980年代中后期有關社會問題的報告文學的觀察后的一種判斷。尹衛星的《中國體育界》和《西部在移民》《中國的“小皇帝”》《神圣憂思錄》《走出神農架》《多思的年華》《伐木者,醒來!》等批量的作品,聚焦于種種社會問題和現象,由文學跨界到體育、移民扶貧、教育、心理學、生態環保等領域,在社會上產生了重大反響。這些作品與其說是文學影響,倒不如說是所寫問題的重要。這是一類主題在先的寫作,所謂主題就是作者要突顯的現象和展呈的問題,基于此,作品淡化人物,淡化情節;人物和情節因問題和現象而存在。在結構上,往往采用“集納式”組裝材料,也有的作品以“卡片式”機動穿插內容。這樣的設置,旨在以多時空的攝照收納集成所寫的嚴峻嚴重。問題報告文學少的是文學品相,多的是信息量以及它對社會現實介入的參與度。它的批量出現,順應了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大勢,顯示了報告文學干預生活的力量。但它與文學的分離,使其價值更多的只是某種專題的報告。
報告文學作為敘事性非虛構寫作方式,在全媒體時代,它已成為報告文學寫作的一種主型。更重要的是,報告文學作家對此有了更為理性的自覺。這種自覺一方面來自全媒體時代特殊語境的外部激發,另一方面也導源于文體自身發展內生動力的激活。現代科技的創新推動世界發展日新月異,人類生活及其精神存在光怪陸離,較之以前更具故事性,甚至傳奇性、離奇性,這使生活本身更多了某種“藝術性”。這種情形常常超出小說等虛構文學作家的想象虛構能力。全媒體時代是信息全球化的時代,人們通過各種媒體傳播方式,實時分享著遠與近、常態與新異的信息。媒體生活成為這一時代人們生活的重要內容。生活自在的豐富復雜、激變多彩,激發了主體對于紀實信息的極大興趣,由此推衍成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這為報告文學文體發展提供了更多的資源供給和市場需求。一代有一代的文學。現在的主流文體無疑是小說,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就有萬部左右,但普遍缺乏能夠抵達現實和歷史深部、具有生活和人性表現力的優秀耐讀之作,小說作家的想象能力和虛構能力有所不足。在這樣的語境中,報告文學可以通過與小說文體比較優勢的創建,形成新的時空中具有自身長項的文體價值,滿足日益增長的社會紀實心理之需。所謂與小說文體的比較優勢,就是小說文體所無,報告文學所有;小說文體所有,報告文學可以借取而優。小說文體所無的是非虛構性,是客觀真實性。小說本來是通過想象、虛構等手段,達成對生活的藝術真實的反映,現在這種藝術真實再現能力的弱化,更顯示報告文學這種寫實文體的意義。小說文體藝術所有的種種,除了虛構以外,報告文學都可從中借取。小說的結構藝術、人物表現技巧等正是補足報告文學文學性偏弱的有效方式。敘事藝術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源于主體生命的某種本能。因為“故事的生物學性”,表明敘事是我們內在的一種需求,“很難想象敘事不是我們本能的一部分”,“我們視自己的生活為一種敘事,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對他人的敘事如此著迷”(哈特4)。經驗告訴我們,讀者對充滿想象力而具有意味情趣的故事,別具特別的興趣。報告文學重視并借取小說的敘事藝術,一方面是對它作為敘事文學樣式內在規律的復位,另一方面也是對故事所具有的某種“生物學性”的尊重。
進入21世紀全媒體時代,報告文學的書寫形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盡管短、平、快的“輕騎兵”式的寫作,在數量上依然很多,但作為主型的則是具有文學“重器”功能的長篇。長篇寫作成為這一時期報告文學評價的一個基本的價值尺度。近20年間,魯迅文學獎共舉行了六屆,共有30部篇報告文學獲獎,其中長篇作品占比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一般而言,長篇作品的容量和厚重,不是短篇作品可以比擬的,它更適合于對重大題材的報告。而長篇作品的寫作則更依賴于敘事的推衍,故事成為文本建構的基本要素。這就需要作者在恪守非虛構原則的大的前提下,講求故事情節、核心細節,重視人物的再現,注重敘事的結構設置等。“頂尖的非虛構作家都是奇聞趣事的寫作高手。在他們的故事中,小的敘事弧線使故事變得更加有趣,無情地牽扯著讀者的心。奇聞趣事對于作者表現人物特別具有說服力。”(哈特87)所謂“敘事弧線”,就是客觀生活本身復雜曲折的存在,也就是客體自在的故事性。它不僅構成了文本的內容,而且非虛構敘事的審美表現力與此緊密相關。這樣故事性,乃至戲劇性、傳奇性,就成為作者寫作時必須優先滿足的構件。當然,這種故事性決不可以由虛構而生成,它就必須仰仗作者實實在在的深入采訪、扎實的田野調查以及檔案文獻的檢索等。而事由人為,故事的主角無疑是人物,作品的故事性由其中的人物,特別是主人公的行動線索而生成。這樣,曾經淡去的人物或只是作為手段的人物,在報告文學寫作中就需要重新建構它的敘事地位和價值。人物是敘事文學最為重要的元素,同樣也是作為文學樣式的報告文學的要素。不同于小說可以通過虛構進行典型化的綜合,報告文學由于必須客觀真實地反映對象的設限,作者只能從實然人物的已有的存在中,選擇最能反映人物生活真實和精神個性的部分加以報告。這就需要作者把切實的功夫下在寫作前的深入采訪上,通過采訪、體認、體驗等,走進所寫對象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只有這樣才會獲得獨特的發現,為作品真實而生動地寫實寫活人物奠定堅實的基礎。另外,報告文學的人物書寫,既要充分地展示其時代性的一面,同時又不可忽視獨特人物自在的個人性,應當注重人物特質化、性格化的真實書寫。
四
在新的媒體生態和新的寫作語境中,報告文學作家對于創造報告文學敘事之美,既有了在認知方面的共識達成,更有了與之相應的能力適配。“我以為,報告文學的文本、敘述姿勢和細節的挖掘則是文學性創意標高所在。其包涵了三個要素: 文本即結構,敘述即語言,細節即故事,唯有這三個因素的推動,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徐劍,《關于非虛構幾個關鍵詞的斷想》,3)這是報告文學代表性作家徐劍所說的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在徐劍看來,結構、語言和故事等是報告文學文學性生成的基本要素,而這些也是報告文學能否獲得敘事之美的關鍵所在。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報告文學作家對敘事之于報告文學所具有的重要本體性,不僅具有清晰的意識自覺,而且也注重與此相應的敘事能力的提升。唯其如此,報告文學作為敘事性非虛構寫作方式的審美景觀,有了整體上的前所未有的刷新。
首先,作為報告文學寫作前置的要件,許多作家對書寫對象本身所具有的故事性獨具敏感,注重選擇內含時代性、歷史性和人性內涵的故事,作有意味的敘事。報告文學是寫實性文體,但生活本身不等于文本,只有那些能滿足文本敘事性基本要求的客觀存在,才有可能轉化為既是非虛構,又有審美性的作品。因此,寫作對象本身所具有的故事性的含量,直接制約著報告文學的寫作。正因為這樣,所以有經驗的報告文學作家,會特別注意從蕪雜的生活中,尋找、發現有故事的題材。報告文學作家趙瑜,寫作之余喜歡收藏。偶得“巴金先生早年寫給山西少女的七封老書信,我無法平靜待之,反復追索不舍。得信后,展開考證落實,‘探索發現’這位女性。前前后后竟用了兩年多功夫。故事波瀾起伏,值得一記”(趙瑜1)。這里趙瑜給出了《尋找巴金的黛莉》這部作品發生史的本源。“尋找”是電影敘事的一種常見模式,“尋找”的曲折離奇,給觀眾制造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趙瑜的“尋找”則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作者洞察巴金早年寫給山西少女的七封信中必然有著故事,而作者尋找當年的少女又自有故事,故事與故事的疊加,使得“故事波瀾起伏”。而這正是作品進行審美的非虛構敘事的客體支撐。題材豐富的故事性以及故事深刻的蘊意,奠定了《尋找巴金的黛莉》的價值之基。作者并沒有只敘寫一個私人或個人的傳奇故事,而是將其納入70多年風云變幻的大歷史中加以呈現,這樣個人命運史與國家社會史交織在一起,其中多重滋味令人嚼味而沉郁。鐵流、徐錦庚《國家記憶》寫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他們尋得了具有傳奇故事性的重大題材——《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共產黨宣言》從國外傳至中國,關于它的翻譯、傳播和影響,其中有著感人至深的傳奇故事。這一獨特題材所具有的先在的故事性,成就了兩位作者一部重要作品的寫作。
其次,報告文學作家普遍重視作品對于人物的再現,人物的再現不只是作品主題表現的一種手段、一種載體,而是作品敘事的中心和本體。許多獲得好評的有影響的作品,大多是因為寫實、寫活了時代人物。這些時代人物不只具有時代精神,而且激揚著個體生命的特質。何建明的《部長與國家》《山神》、李鳴生的《發射將軍》、李春雷的《木棉花開》、陳啟文的《袁隆平的世界》、陳果的《勇闖法蘭西》等作品,以紀實的方式,為行進中的21世紀中國文學,塑造了各式具有不同事跡和精神個性的大寫人物,豐富了中國文學中人物形象譜系。《部長與國家》的主人公是老石油部長余秋里,“部長與國家”命題,是共和國歷史的一種給定,大慶石油會戰的傳奇故事,成就了感天動地的奠基者的精神史詩。《山神》中的黃大發,是當代中國的“愚公”,他帶領村民30多年挖山不止,開鑿“天渠”,改變了山村面貌。作者以真實細致的筆墨,描寫出一個可觸可摸可敬可愛的中國“硬漢”形象。《發射將軍》中的將軍是我國第一個導彈發射基地的司令員李福澤,作品中的李福澤既有軍人使命必達的職業精神、愛國情懷,也有作為一個特殊的個體生命所獨具的心性和品格。木棉樹是英雄樹。《木棉花開》以意象思維敘事寫人,一改政治人物書寫的標簽化,本真地凸顯任仲夷這位改革開放前行者的蒼勁挺拔的偉岸身影。袁隆平是一顆種子,他的世界浩瀚燦爛,《袁隆平的世界》通過人物的人生行旅、育種科研和精神世界的多維觀照,寫出一個立體的、豐贍的人物。相比以上的這些人物,《勇闖法蘭西》中的羅維孝,只是一個普通的退休職工,但他卻創造了歷時115天,穿越8個國家,從中國到法國騎行30 000里路的奇跡。作品通過個人傳奇的講述,寫出了尋常生命的堅韌、勇氣和力量。羅維孝“向自己出發”的性格稟賦,使之成為一個生命的勇者、精神的強者和蕓蕓眾生的啟示者。
不只是這些以人物作為敘事內容的作品,注重對于人的表現刻畫,而且相當多的工程類寫作,一改過往作品多事少人的工程化不足,既重事也能見人。如此這般,這類作品的文學品質便有了明顯的提升。工程類題材,在報告文學寫作中占比較大。如果只以工程事件為中心書寫,人物只是事件的推動者,那么作品很有可能變為某種工程史或更為具體的大事記,與通常意義上的文學建制相去甚遠。而如果能將工程事件與關聯人物作融合式的敘寫,即既注重工程建設的重大節點的報告,又重視與其相關的重要人物的再現,物與人相生,人以物而得形神,物因人而存真傳史,物性與人情合致,這樣就有可能達成具有文學意味的真正的作品。徐劍的《大國重器》,看題目就是典型的國家敘事,作品記寫的是“中國火箭軍的前世今生”,徑言之就是中國導彈事業的發展史。對于這樣一個重大題材,富有經驗、具有非虛構寫作高度的文學自覺的徐劍,自有獨特而有合乎對象邏輯的認知:“重器也,但非器也,大國國器是人,大寫的中國人,中國士兵、中國火箭官兵,他們才是真正的大國重器。”(徐劍,《我有重器堪干城》,2)基于此,作者將與導彈事業具有重要關聯的人物作為這部作品書寫的重心。作品既寫到高層的決策者,更不吝筆墨描寫李旭閣、向守志、楊業功等火箭軍的各級首長,還以大量篇幅為普通的官兵立傳。人物的出場都有特殊的場景,因人物而發生的故事,特別是細節,又使人物的形與神真實而生動地存活了起來。由此,一段大的歷史具有了靈性、溫度和厚度。何建明的近作《大橋》,取材于被人稱為世界“新七大奇跡”之一的港珠澳大橋的建設。極有意味的是,有人將大橋的“Y”形上部,視作“V”,比喻為“一國兩制”的偉大勝利(victory)。而在作者看來,“這‘Y’形橋還代表著另一個形象,它如一個大寫的‘人’”。“這是‘Y’形的港珠澳大橋最富深意的密碼,這里的‘人’是真實的人,他們是一群讓世界同行敬畏的中國工程師。”(何建明3)這是何建明富有詩意的想象,也是文本內在敘事重心的設置。《大橋》與其說是一部特大的橋梁建設的工程史,不如說是一部以林鳴為代表的創造奇跡的中國工程師的精神史。
另外,就是具有非虛構敘事自覺的報告文學作家,善于從客體自在的有意味的機理中,發現并建構具有某種藝術性的結構邏輯。這里所謂的結構邏輯是既得之于寫作對象的實際存在,是一種客觀實在,但又不是客觀主義的復寫,而是體現著作者主體對客觀實在能動把握后的一種“再結構”,或者說一種有機的“重組”。這種“再結構”或“重組”,非虛構性是它的屬性邏輯,即它的構件及其要素是真實存在的。這是前提。而敘事性則是文本再現客體的邏輯,這里需要作者遵循敘事藝術的基本規律,設置好故事敘述的關鍵要素,包括敘事主線的選擇、核心材料的安排、主要人物的出場,乃至對“故事可能的起點,扣人心弦的最佳部分,和其他戲劇化的手段”(哈特6)等的考慮,最終達成最優化的非虛構敘事的審美效果。因此,作者對于結構邏輯的處理能力,在具體寫作中顯得特別重要。這里,關鍵的是作者要深熟寫作對象,在此基礎上尋獲結構作品的內在邏輯和藝術契機。“2015年12月31日,歷史子午線與現實的子午線在這一瞬間重合了。六十年前,錢學森備課,次日下午提出火軍概念,六十年后,習近平主席授旗、訓詞,標志著火箭軍的序幕于此刻撩開了。”(徐劍,《大國重器》,532)這是《大國重器》所寫對象的一個自在的一個大結構。徐劍從客體機緣巧合之中,發現了結構全篇的線索和作品敘事的切入點。1956年元旦錢學森講授“導彈概述”,聽講座的大多是高級軍官,李旭閣當時還只是個校級參謀。“從聽錢老的《導彈概述》課開始,他的命運便與中國戰略導彈事業連在一起了。”(徐劍,大國重器,15)錢學森無法想象聽他講座的這位最小的軍官,日后會成為中國戰略導彈的司令員,而李旭閣也始料未及自己的命運之旅會是那樣的延展。這是真實的事實,而故事性和傳奇性也在其中。徐劍正是據此設計了足以牽引讀者興趣的敘事結構。李發鎖的《圍困長春》也是一部為讀者認可的作品。這不僅是因為這部作品為我們再現了林彪這位重要而敏感的人物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無法遮蔽的存在,而且也與作者嫻熟的敘事藝術有關。長春不只是長春,而是中國解放戰爭的一個重大節點。作者從宏闊的國際、國內全局中,建構出一個既符合歷史,又具有敘事召喚力的記述模式。作品高開啟遠:“1945年8月8日下午4時50分,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緊急召見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尚武”,宣布“從8月9日起,蘇聯對日本已進入戰爭狀態”,“這一震驚世界的軍事行動,各國領袖反應各不相同”(李發鎖5—6)。作者以富有意味的特寫鏡頭將他們的“反應”一一推置讀者面前。此后寫到圍繞東北的蘇美角力、國共角逐等重要的歷史情節,亦不乏具有戲劇性的細節。而整部作品的總體結構就是一種“角力”結構,矛盾沖突的推衍之中,敘事疾徐而來,有關的歷史人物立然可見,漸行漸遠的場景得以重現。
盡管報告文學是一種特殊的文學樣式,但是我們在強調它的特殊時,不應無視它作為敘事文學類型之一的事實。在恪守其非虛構特性之外,報告文學也得遵循敘事文學寫作的一般規律。如此,方為文學。這是常識。
注釋[Notes]
① 參見: 谷雨、南香紅、張宇欣:“為何非虛構性寫作讓人著迷?”,騰訊網2015年8月29日,2019年5月20日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杰克·哈特: 《敘事性非虛構文學寫作指南》,葉青、曾軼峰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
[Hart, Jack.Storycraft:TheCompleteGuidetoWritingNarrativeNonfiction. Trans. Ye Qing and Zeng Yife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2.]
何建明: 《大橋》。桂林: 漓江出版社,2019年。
[He, Jianming.TheGreatBridge.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9.]
黃傳會: 《大國行動》。北京: 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2019年。
[Huang, Chuanhui.GreatPowerAction. Beijing: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ublishing House, 2019.]
李發鎖:“圍困長春”,《中國作家·紀實版》3(2018): 5—161。
[Li, Fasuo. “Besieging Changchun.”ChineseWriters:DocumentaryEdition3(2018): 5-161.]
麥天樞 尹衛星等:“1988·關于報告文學的對話”,《花城》6(1988): 4—29。
[Mai, Tianshu, and Yin Weixing, et al. “1988: A Dialogue on Reportage.”FlowerCity6(1988): 4-29.]
茅盾:“關于‘報告文學’”,《報告文學論集》,周國華、陳進波編。北京: 新華出版社,1985年。3—7。
[Maodun. “On Reportage.”PaperssonReportage. Ed. Zhou Guohua and Chen Jinbo.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1985.3-7.]
徐劍:“關于非虛構幾個關鍵詞的斷想”,《中國藝術報》,2017年4月11日第3版。
[Xu, Jian. “Fragmented Thoughts on Several Keywords about Non-fiction.”ChinaArtNews11 April 2017.]
——:“我有重器堪干城”,《文藝報》2018年12月21日第2版。
[- - -. “I Have Pillars to Defend the State.”LiteratureandArtDaily21 December 2018.]
——: 《大國重器》。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8年。
[- - -.ThePillarsofaGreatPower.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18.]
趙瑜: 《尋找巴金的黛莉》。西安: 陜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Zhao, Yu.InSearchforBajinsDaili. Xi’an: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