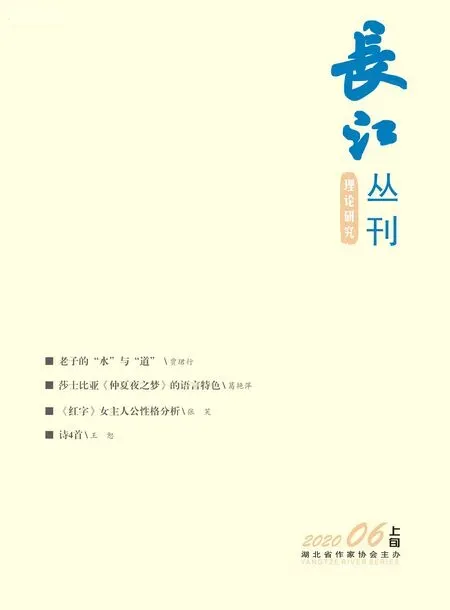應用心理學發展的邏輯起點問題
■王 川/西北大學
一、前言
科學主義心理學會認為人類可以和機器或者動物等同。人類的具體特征也是機器或者動物的具體特征,因此他們認為人類的心理學的主要研究可以在實驗室當中進行具體的控制以及研究。人文主義心理學則指出了人類具備比較獨特的價值,并主張在人類和機器以及動物之間要進行最根本的區分,他們提倡對人類進行相應的不受控制的具體臨床以及野外描述性的相關研究。
二、實證主義對人性的具體“取消”
(1)比較嚴格的實證主義是以相應的理性邏輯以及數學作為靈魂,邏輯以及數學是提取相應的離子現實的一種理想語言。如果可以用相應的邏輯以及數學理想的具體語言充分的描述人的相關本性,那么意味著人們已經達到了一種理性以及理想的生存狀態:人們將不會再出現情緒化,每一步都可以通過相應的具體“計算”來完成。恩格斯曾經認為,未來的某一天,意識以及具體的心理會在物理和化學的運動過程中表達出來。很顯然,恩格斯所說的這些話并沒有得到真正的實現。斯金納對此也曾經表示:“我們最終可能會制造出一種具備模仿這種能力的具體機器,但這一目標也沒有具體的實現。”
(2)經驗方法造成的相關障礙以及掩蓋是一種技術的具體手段。技術一直在發展,正在變得越來越復雜,這迫使我們要越來越關注技術的具體本身,而忽略了與相應的問題以及目標進行直接的對抗。我們必須要以相應的技術作為主要的手段,要把技術作為重中之重,消除主要的問題以及屠宰的對象,比較生動的人文以及生活已經成為了比較枯燥乏味,甚至是不負責任的一些宣傳數據。比如,我們花費大量的時間,大量的精力以及財力進行記憶的相關實驗研究,結果表明:有意義的記憶和無意義的記憶相比,將會更好。除兩個具體的技術術語之外,這樣的具體結論沒有任何的意義,也就是說,可以在常識的基礎之上進行判斷這樣的結論,而不需要進行相關的實驗。還有一些試驗研究會讓我們感覺到被戲弄的感覺:比如,一些具體的測量項目會具體的詢問:“你是傻瓜嗎?”絕大多數人一定會選擇“否”,因此您可以得出一個比較符合“正態分布”的具體結論:大多數人都是比較正常的,而傻瓜卻非常的少[1]。當然,這樣的研究可以說是非常荒謬的,但是我們當前的相關心理學當中充滿了許多這樣的一些經驗結論,并且以“科學”的具體名義將它們寫進了各種各樣的教科書當中,這種濫用結論所帶來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3)現代技術的具體發展已經非常的精細了,它滲透到每一個細胞當中,可以控制細胞的具體生化過程。當然,這也為我們提供了可以探索一些更加微妙的心理過程的具體數據,但是具體的考慮一下,當人類的行為減少到相應的細胞活動時,在這種水平之上還會有“人類”的存在嗎,在細胞的相關水平上,人類的具體活動與相應的動植物之間又有什么具體的區別呢?實際上,現有的相關心理學文獻提供給我們的很大一部分實驗數據都是來自于動物的實驗數據。將這些具體的數據推斷給人類,會非常的容易混淆人與動物之間的具體本質界限。即使試驗的目標是人類,那么大多數人需要被控制在相應的實驗室里,實驗室當中這個被嚴密控制的人能否代表具體的現實生活當中的活潑靈性的人呢?此外,現有的具體心理實驗只能看一些比較簡單的低層次的相關實驗。很多的人類行為都沒辦法用具體的實驗結論來進行解釋,科學心理學一直在避免研究相應的人類存在的具體問題[2]。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因為它選擇的相關自然科學方法不具備足夠的具體能力來研究此類相關的問題;以上可以清楚的表明人性是無法進行具體的證實的,憑相應的數學邏輯以及實驗技術阻礙以及掩蓋了心理學的具體研究意義。使用具體的技術來衡量比較生動的生命,我們只能改變生命的具體活力,使其變得凝固化。
三、現象學對人性的相關“還原”
人文主義的相關心理學是以實證主義心理學的相反立場出現的。作為人類心理學的一種哲學基礎,現象學將技術引起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主要“障礙”視為理性邏輯的一種具體化的手段,因此主張相應“懸而未決”,相應的“實質還原”,以及“回歸”。探索客體具體的“本質自我”,但是這種相關的“還原”主觀性是非常明顯的,這將造成客觀標準的具體廢除,走向相對主義以及具體的神秘主義。現象學方法論上存在的一些矛盾:一方面,人性的具體旗幟被抬高,主觀經驗的相關價值被強調;另一方面,人性被“簡化”為比較簡單的一些直接經驗;有兩個主要的問題值得懷疑:(1)是否存在相應的“直接經驗”;(2)在報告相應的“直接經驗”時是否存在具體的報告者價值的相關滲透。第一個問題就構成了一種悖論:一方面,高揚人性的具體大旗,重點的強調主觀的具體經驗,另一方面,即使觀察者沒有接受比較特殊的相關內省訓練,但是也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具體文化影響,并且觀察活動的本身以及用來描述觀察到的相關“直接經驗”的具體語言是人為的和經過相關修改的[4]。這種“直接經驗”與前者的相互直接經驗直接的相反。因此,通過“直接經驗”首先找到真實的邏輯和“本質的自我”是不可能的,“關于第二個具體的問題,我們必須要承認人不僅是一種事實的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種價值存在。這是認識現象相關心理學的一種基本前提。
四、人性——心理學的邏輯起點
人性是人類具體生存以及終極關懷的一種基礎,這是與相關的心理學直接對立的問題的兩個主要方面。因為心理學源于人類對自我具體問題的一種關注,所以其中兩個問題對于心理學的相關出現顯得特別的重要。一種是人類如何看待包含他們本身在內的具體的客體世界。研究這個問題使相應的心理學家更加的專注于組織以及應用知識的具體方式,而這個問題的具體答案構成了相應的心理學知識體系當中的“中心區域”。第二個是人類如何更加幸福的進行生活。對于這個問題的具體擔憂使心理學家們更好的探索人類的具體不幸以及相關的預防方法。由于答案形成的具體知識體系構成了相關心理學的“邊緣區域”。這兩個問題也可以這樣理解:第一,心理變化的具體程度以及范圍具體是什么?其次,心理知識可以怎樣具體的解釋以及我們如何進行使用這些具體的知識。回答第一個問題的時候可以明確心理學的具體研究內容(“中心區域”),回答第二個問題的時候可以定義心理學的具體目標以及任務(“邊緣區域”)[5]。當我們將心理學定義為相關的“解釋心理現象以及規律是用來更好的指導人們的生活科學時,我們實際上是在具體的回答與人類生存以及終極關懷相對應的兩個具體的問題。因此,人性是心理學當中必須首先要進行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否則心理學本身將無法進行具體的定義[6]。
五、結語
總體而言。心理學是主要研究人的一門重要科學,我們必須要首先具備比較正確的觀點來作為研究工作的主要方針。心理學比較基本的任務就是科學地弄清一個人到底是什么,從而可以獲得對人具體的本質理解,所以,人的具體實質問題對心理學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