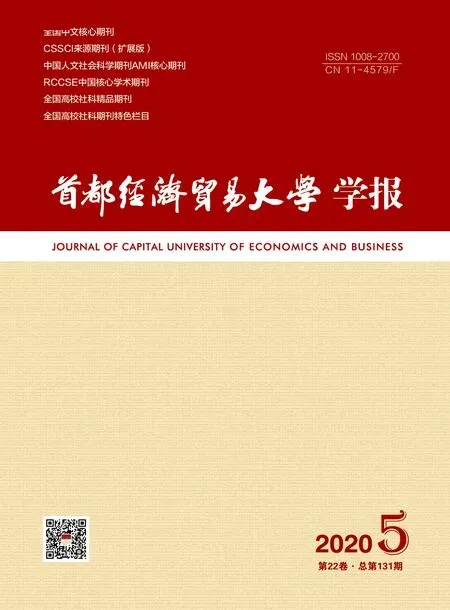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多極核-雙重邊界效應
姚永玲,邵璇璇
(中國人民大學 應用經濟學院,北京 100872)
一、問題提出
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的障礙在于地區之間的巨大差距。這種差距主要反映在三個層面,即省級單元之間、地級及以上城市之間和中心與外圍地區之間。自京津冀一體化作為國家戰略以來,北京和天津及一些大城市之間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差異在逐步縮小,2017年京津冀地級及以上城市群內部的基尼系數與珠三角和擴大規模后的長三角地區均等化水平非常接近;與此相反的是,2014年以來,京津冀地區出現外圍縣與中心城區之間差距上升的趨勢,這成為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巨大障礙。因此,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問題是解決中心與外圍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讓中心充分發揮空間溢出效應,促進周邊地區協調發展[1]。經驗分析表明,空間溢出效應是中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因素[2]。目前大量關于京津冀的研究主要著眼于三地省級層面的地區差距和協同發展;對核心與邊緣地區之間關系及其相互作用重視不足。而協同發展的過程恰恰是打破邊界、促進區域融合的過程;尤其是對經濟發展處于不同階段的三個省市,中心與邊緣地區的協調需要受到更多關注。
從實踐來看,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過程中一個突出的現象是,過于強調省級單元之間的協調發展,忽視了各自內部的地區均衡,從而導致在中心城市進行產業轉移時,存在明顯的政策性“飛地”。其中,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時,將河北和天津作為主要的產業轉移目的地,忽視了北京更有條件的外圍地區。如北京的順義區與天津的北辰區、青田區和河北的保定,同屬于京津冀地區汽車產業的主要生產基地;加之順義的臨空經濟和區位優勢顯著,高端制造業具有較大發展空間;但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并沒有成為產業轉移接受地,反而由于“退二進三”,第二產業受到壓縮。懷柔和昌平科學城由于與雄安新區存在競爭關系,由原來規劃中的“科技創新中心”改為了“科學創新中心”,失去了技術創新功能,降低了優勢空間的使用效率。另外,河北在接受產業轉移時,明確列出承接產業轉移的36個園區大多分布在滄州、保定、石家莊、邯鄲、邢臺、唐山、秦皇島和衡水等地,而最接近北京副中心的北三縣(三河、大廠和香河)卻鮮有明確的與通州產業接軌的產業園區。因此,基于宏觀層面的“飛地”效應脫離開了空間推移規律,表面縮小了地區差距,實際并沒有消除地區之間協同發展的壁壘。
邊界效應是指由于行政邊界的存在引起跨越邊界的同質要素產生量變或質變的現象[3]。當這種效應有利于要素跨區域流動時被稱為中介效應,不利于要素跨區域流動時為屏蔽效應[4-5]。京津冀協同發展就是要在發展差距較大的邊界地區,減少屏蔽效應,強化中介效應。三地的中心城區分別處在不同的城市發展階段,各自的行政級別、規模、結構、功能、資源獲取能力和城市競爭力也不同。在發揮輻射作用時,三個中心相互交叉(即多極核),在兩兩邊界地區同時又分別作用于自身邊界和對方邊界(即雙重邊界)地區。據此,本文認為,京津冀地區三個不同省級單元之間復雜的關系,需要從多極核和雙重邊界角度,在區縣級單元上進一步認識不同類型的邊界效應及其空間作用方式,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提供進一步證據。
二、文獻綜述
邊界效應與區域一體化的關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對邊界效應的認識和測度兩個方面。在認識邊界效應研究方面,安樹偉(2004)認為由于行政區經濟和邊緣化雙重作用下使得省際邊界區發展呈現一種特殊的、具有分割性和邊緣性的經濟現象[6];周黎安和陶婧(2011)認為,中國官員績效考核制度會使得省際間競爭激烈,經濟合作激勵不足,并最終導致了省際邊界區的經濟落后[7];仇方道等(2009)認為,由于政策和邊界阻隔等因素帶來了交易成本過高,從而導致省際邊界區經濟活動的效率低下[8];崔兆財和周向紅(2018)通過對夜間燈光的研究發現,經濟增長在中國省界兩側具有明顯的差異性[9];趙聚軍(2016)認為,京津冀地區雖然具有明顯的大都市區特點,但由于京津兩個大城市均為廣域市制,擁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還沒有達到規模效應外溢的階段,仍然會存在較大的邊界效應[10]。可見,學者們對京津冀地區存在邊界效應已達成共識。但由于不同城市中心凝聚資源的能力和所處發展階段不同,對不同邊界地區作用存在較大差異,針對京津冀地區多核心和多邊界特點還需要在上述研究基礎上,將空間細分并建立非對稱模型,以識別不同核心對不同邊界地區的中介效應或屏蔽效應。
在邊界效應識別和測度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采用一價定律,通過海關貿易和商品數據進行測度[11];或者加入引力模型,通過市場潛力測度邊界效應[12];更進一步則是增加空間權重,以提高對邊界效應測度的準確性[13-14]。但是,這些測度方法過于簡單地將地區看作單中心結構,研究中僅設定一個核心,忽視了一方核心與另一方核心對彼此邊界地區的雙重作用,以及兩個核心對彼此邊界影響的差異。事實上,邊界的存在意味著兩個以上的行政單元相互毗鄰,不同行政單元都有各自的中心和外圍地區,它們的空間關系表現為每個中心既與自身中心有關,也會與另外行政單元的中心有關。從而導致一個中心與多個外圍地區的關系,使得邊界地區對于地區整體既有分割也有連接;同時,由于兩個行政單元的中心和外圍有明顯異質性,這種雙重作用既是相互的、也是不對稱的。這就需要在研究邊界效應時,采用多極核-雙重外圍方法,分別從多個行政單元的中心與雙重外圍關系角度,識別不同行政中心對自身和對方外圍地區的邊界效應。這對于跨越三個省級單元的京津冀地區更為適用。
對京津冀區域的研究發現,一方面京津冀地區的集聚力仍較顯著,由此而引起的“虹吸”現象是導致中心與外圍地區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行政干預在地區經濟中的作用舉足輕重,行政資源的空間配置直接決定著地區經濟發展的空間格局,行政壟斷、財政分權等行政因素往往導致邊界地帶的屏蔽效應[1,15-16];加之邊界地區遠離行政中心,往往容易被忽略而成為發展弱化的地區,尤其是省際邊界區域的經濟發展存在嚴重的滯后性,是區域發展中最容易被邊緣化和遺忘的角落[17]。鄭濤和李達(2017)發現,在京津冀城市群空間格局初現端倪的同時,京津地區與河北省內部各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仍在不斷擴大[18];京津市區與郊區之間的失衡甚至超過京津與河北之間[19]。肖金成(2004)認為,地區間最大差距不是城鄉差距,也不是省際差距,而是省會城市與處于邊緣地位的邊界地區的經濟差距[20]。京津冀地區的行政地位最為突出,因此邊界效應不容忽視。
但是目前的邊界效應相關研究主要將省級單元看成一個整體,沒有進一步劃分省域內部的中心和邊界地區,導致了相關文獻在分析邊界效應時落入到區域協調和合作、地方保護等傳統理論分析框架中,從而難以針對省際邊界區特殊性得出有效的結論[17];根據卡佩羅等(Capello et al.,2018)的研究,邊界壁壘導致的損失在更靠近行政邊界的區域更多[21],這進一步說明,邊界地區是空間異質性最為明顯的地區,這與邊界地區可能同時存在分割與連接作用有關;張學波等(2016)發現,京津冀地區的空間溢出效應具有顯著的地理衰減性[22];尤其是在城市群逐步形成的經濟框架下,中觀尺度的邊界效應研究具有迫切性[3]。因此,對邊界效應的研究需考慮在省域內部更小空間尺度下,分析多極核-雙重邊界之間的相互關系。
本文的多極核-雙重邊界研究框架是,分別將京津冀的三核心對各自的邊界和對方邊界同時作用的結果進行比較。在北京與天津毗鄰地區,同時考慮北京市核心對自身邊界和對天津邊界地區的影響,天津市核心分別對自身邊界和北京邊界地區的影響;在北京與河北毗鄰地區,同時考慮北京市核心對自身邊界和對河北省邊界地區的影響,河北省核心對自身邊界和對北京邊界地區產生的影響;在天津與河北毗鄰地區,同時考慮天津市核心對自身邊界和對河北邊界地區的影響,河北省核心對自身邊界和對天津邊界地區的影響。最后,將三核心分別作用下的雙重邊界效應進行比較,從不同核心的異質性以及不同核心與外圍地區關系的異質性角度,在更小空間尺度上進一步認識不同邊界效應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影響。
三、模型與數據
在測度邊界效應時,通常的方法是在回歸模型中加入虛擬變量,以區分是否屬于邊界地區,通過考察該變量回歸系數的顯著程度,判斷邊界效應的存在。由于該方法不能對回歸樣本進行區分,僅能識別是否存在邊界效應,不能明確具體所指的核心以及所針對的邊界。在地區貿易方面的邊界效應研究中,最初的方法是通過觀測兩個地區之間的實際貿易流量在邊界地區的變化[23],發現邊界效應。基于此,麥家廉(McCallum,1995)基于貿易量數據,采用引力模型計算了美國與加拿大的邊界效應[24];趙永亮和才國偉(2009)采用的是與引力模型類似的市場潛力指數測度邊界效應[25]。在地區市場一體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一價定律方法,從兩個地區之間的價格差異方面衡量地區邊界效應[12,26-27]。由于引力模型僅根據規模推測流量潛力,缺乏理論依據;所需要的貿易流量基于微觀調查,對數據提出了極高要求。在地區經濟增長方面,李郇與徐現祥(2005)基于趨同分析框架,采用經濟增長差異測度邊界效應。由于該方法采用計量回歸發現核心與邊界地區增長趨勢的變化,反映了地區增長的同步性,并能明確識別核心與邊界地區[28],為多數研究者所采納[29-30]。
本文分別以北京中心城區、天津中心城區和石家莊轄區(作為河北中心地區)為三個核心,將與三省市交界的區縣市作為邊界地區,按照發展趨同分析框架,通過在回歸模型中加入距離和邊界的交互項,分析三個省級單元邊界之間相互作用而產生的雙重邊界效應。
(一)趨同分析模型
在地區經濟快速增長初始階段,核心區與邊緣區融合度不高,核心作用以極化效應為主,核心的經濟增長往往要快于邊緣區域增長,邊界起著分割兩個區域的作用,核心區的發展效應無法傳導至邊緣區,反而不斷把邊緣區的資源汲取到核心區,從而產生“虹吸”和“燈下黑”現象,最典型就是環京津貧困帶的出現。隨著核心空間作用由極化效應向擴散效應轉變,邊界的分割作用效果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作為通道的連接作用上升,甚至基于后發優勢可能還會獲得比核心更高的經濟增速。前者成為邊界屏蔽效應,后者為中介效應。
本文以核心區與邊緣區的經濟增長差異變化,采用趨同增長的分析框架,測度這兩種邊界效應。分析框架見圖1。

圖1 多極核情況下核心邊緣關系與邊界效應
據此,本文基于地區差距變化的邊界效應假設如下:
假設1:核心與邊緣區經濟增速差異擴大,產生邊界屏蔽效應。說明當期的中心仍處于經濟聚集階段,對邊緣地區產生了極化效應;這種核心對外圍的極化效應,表現在距離越靠近核心區、屏蔽效應越大,容易在邊界地區產生“空間鴻溝”,不利于地區協同發展。
假設2:核心與外圍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縮小,產生中介效應。在空間上表現為兩種情況:一種是越靠近中心地區,差異縮小越快,說明該中心對外圍地區通過空間溢出發生中介效應,可稱之為“空間溢出中介效應”;另一種是中介效應沒有表現出隨距離變化的空間溢出,而是表現為“飛地”選擇效應,可稱之為“飛地中介效應”。前者反映了空間擴散過程;后者則可能由政策等非空間因素所致,存在空間不確定性。
根據假設,本文建立基于趨同分析框架的回歸模型(也稱巴羅回歸方程),主要通過考察條件β的趨同特征,識別邊界效應。由于β趨同表示不同地區發展速度與其自身初始狀態到穩定狀態的距離,它們大致成正比的空間協調關系;因而通過對模型進行變量代換,可以對不同空間的差異進行縱向和橫向比較。巴羅回歸方程如下:
gi,t=α+βlnyi,0+γXi,0+εi,tgi,t=α+βlnyi,0+γXi,0+εi,t
(1)
式(1)中,gi,t表示的是經濟體i在t時間內的平均經濟增速,yi,0表示經濟體i在初始時期的經濟水平,Xi,0為刻畫經濟體i在t時間內穩定狀態的一組變量(都取對數狀態),在趨同的框架下,β<0。
首先,采用β趨同識別地區經濟增長差異。假設區域1和區域2之間存在邊界效應,則以區域1中心城區為核心,區域2與區域1 相鄰的邊界地區與非邊界地區之間的經濟增長速度存在明顯差異;將區域2的中心城區作為核心區,也可以發現區域1 與區域2相鄰的邊界地區與非邊界地區之間的經濟增長差異。具體公式如下:
g1,t=α+βlny1,0+γX1,0+ε1,tg1,t=α1+βlny1,0+γX1,0+ε1,t
(2)
g2,t=α+βlny2,0+γX2,0+ε2,tg2,t=α2+βlny2,0+γX2,0+ε2,t
(3)
則兩地間的增長率差異可表示為:
Δgt=g1,t-g2,t=(α1-α2)+β(lny1,0-lny2,0)+γ(X1,0-X2,0)+(ε1,t-ε2,t)
(4)
+γ(X1,0-X2,0)+(ε1,t-ε2,t)
將增長率差異進行近似對數標準化,則:
(5)
(6)
(7)

(8)
其次,引入邊界與距離變量。根據距離衰減定律,邊界效應對距離靠近核心邊界處的邊緣區域有更強烈的作用,隨著與邊界距離的增加,邊界效應的影響將逐漸減弱。同時邊界效應的強弱也會使得空間距離的作用產生異質性,二者密切相關;并且在多極核的框架下,與其中一個核心的距離較遠的同時可能與區域內另一極核的距離較近,這將影響對邊界效應的估計。由于核心對邊緣區的作用取決于兩者的作用力,也取決于兩者的空間距離。為了反映距離因素對邊界效應結果產生的影響,本文同時引入距離變量Distance和邊界啞變量Border。
在趨同分析框架下,參照引力模型修正方法,將巴羅回歸模型修正改寫成如下形式:
(9)
再次,加入邊界與距離變量的交互項。本文從多極核心的角度觀察雙重外圍邊界效應。在距離衰減原理的前提下,不同行政歸屬的邊界地區以及距離不同的極化核心對經濟差異的變動都產生不同影響。
在一般巴羅回歸模型基礎上,本文的多極核-雙重外圍地區的邊界效應回歸模型寫為:
(10)

(二)數據
已有京津冀地區一體化研究主要針對省級或地級以上城市。由于邊界地區往往是縣級行政單元,聯合國報告中提到的“環京津貧困帶”實際上指的也是區縣單元。
為了更精確地表示邊界地區的空間特征,本文以區縣級行政單元為空間對象,采用京津冀三地的區縣(市)數據。衡量與省外的關系時,三地的外圍地區分別是:河北與北京接壤的16個市縣和天津與北京接壤的2個區(縣)、北京與天津接壤的兩個區(縣)和河北與天津接壤的15個市區(縣)、北京與河北接壤的7個區縣和天津與河北接壤的7個區縣,天津與河北接壤的10個區縣;衡量省內的中心-外圍關系時,三地的外圍地區分別為:北京市內與主城區交界的6個市轄區、天津市內與主城區交界的3個市轄區、河北省境內與石家莊交界的14個市區(縣)。三地中心地區分別是北京主城區(城六區),天津主城區(城六區),石家莊市轄區。共計183個區縣(1)關于行政區變動的處理:石家莊的藁城區是2014年由石家莊下轄市藁城市撤市設區建立,仍按藁城市計算,計算石家莊市區數據時將其剔除,其他縣市等同。天津濱海新區建立較早,將早年分設的塘沽區、漢沽區、大港區并入計算,北京的東城與崇文、西城與宣武在2010年合并,為方便計算,將此前的也合并。。
各縣(市)數據來源于2004—2018年的《中國縣域統計年鑒(縣市卷)》,部分缺失數據根據相應年份的市(縣)統計年鑒或公報資料填補;北京和天津各區數據來源于《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各地級市市轄區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市轄區。地區人均GDP采用地區生產總值除以地區年末常住人口,并進行平減處理;空間距離在百度地圖上利用Python軟件獲取區縣(市)政府所在地位置進行計算;邊界地區識別利用ArcGIS 10.2軟件選擇相鄰邊界的區縣(市),位于邊界地區的縣級行政單元為1,否則計為0。
四、回歸結果
(一)趨同框架下巴羅回歸的單位根檢驗
為避免出現偽回歸,需要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由于是面板數據,故采用LLC與IPS進行單位根檢驗。Eviews 9.0軟件的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1(ADF與PP檢驗結果也一并給出)。

表1 四種方法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表1顯示所有參數的檢驗結果都拒絕原假設,說明數據平穩,不存在單位根,可以直接進行回歸分析。
(二)模型有效性檢驗
由于核心區對不同邊緣區的作用存在差異,且這種差異會隨時發生變化,故在不同時點模型會有不同截距,因此需要建立時點固定效應模型。在建立模型前需要進行檢驗,以確定模型的有效性(檢驗結果見表2)。
表2 顯示,所有參數都顯著,說明本文選用時點固定效應模型是有效的。

表2 時點固定效應模型的檢驗結果
(三)估計結果
本文分別將北京主城區對北京、天津和河北的邊界地區,天津主城區對北京、天津和河北的邊界地區,以及石家莊市轄區對北京、天津和河北的邊界地區作為多極核心和雙重外圍地區,采用Eviews 9.0軟件對上述模型進行時點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見表3。

表3 多極核-雙重外圍地區的邊界效應估計結果
表3顯示,當以北京為核心時,對河北和天津邊界地區的β<0且在1%的水平顯著,說明北京對這兩個邊界地區產生了中介效應;與此對應的空間距離系數皆不顯著。結果表明,北京市的核心對邊界地區的中介效應,并不受空間距離的影響,符合假設2中的“飛地中介效應”。
以天津為核心時,僅對北京邊界地區的β>0且在1%水平上顯著,天津對北京邊界地區表現的是屏蔽效應;與此同時,對北京邊界地區的γ>0且在1%水平顯著,說明天津核心對與北京鄰近的邊界地區產生屏蔽效應的同時,還受到空間距離的影響,與天津距離越近的北京邊界地區屏蔽效應越明顯。天津市核心對北京邊界效應符合假設1,表明天津主城區與北京邊界地區可能存在“空間鴻溝”。
石家莊作為河北的核心城市,僅對自身邊界地區的β>0且在1%水平上顯著,同時距離因素僅對河北邊界地區的γ<0且在1%水平顯著,說明石家莊對河北邊界地區有顯著的中介效應作用,且距離越近中介效應越大。這個結果符合假設2中的“空間溢出中介效應”,表明石家莊經濟增長對河北邊界地區發展具有空間溢出效果。
對表3中兩個反映邊界效應的重要參數β和φ在三個地區之間的系數重新整理繪制成圖2,以比較三個極核所產生的邊界效應,進一步說明京津冀三中心在一體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圖2 京津冀地區中介和屏蔽效應示意圖
圖2顯示,當以北京作為核心時,對三地的邊界地區一致地表現為β<0和φ>0,北京主城區對所有相鄰邊界地區都產生了明顯的中介效應,尤其對天津中介效應最為顯著,說明北京在京津冀一體化過程中的作用較為明顯,也是京津冀一體化的主要貢獻者。
天津中心城區僅對天津行政范圍內的邊界地區(天津遠郊區)β<0和φ>0,對北京和河北邊界地區則表現為β>0和φ<0;與此同時,天津主城區僅對自身的外圍地區有中介效應,對北京和河北邊界地區都為屏蔽效應,尤其對北京邊界地區的屏蔽效應最為顯著,說明天津是京津冀一體化的受益者。
石家莊作為核心,對河北和北京邊界地區表現為β<0和φ>0,但對北京邊界地區效應不顯著、對河北邊界地區中介效應顯著;石家莊對天津的邊界地區為β>0和φ<0,但不顯著,表明河北在京津冀一體化過程中,主要依靠自身力量。
五、結論與建議
對多極核-雙重邊界效應的分析說明,在多中心結構地區,邊界效應具有異質性和多樣性。同一個邊緣區會受到多個核心區的影響,同一個核心區對不同邊緣區的影響效果不同。京津冀三地在各自發展階段、行政級別、規模、結構、功能等方面差距較大,多核-雙重邊界效應模型在區縣級層面上進一步展示了復雜關系下的核心與邊緣地區相互作用關系。
北京核心對天津和河北邊界地區表現出顯著中介效應,而對自身邊界效應不顯著;與此同時,北京在京津冀一體化過程中表現出了“飛地中介效應”選擇效應。說明北京的中介效應有利于京津冀三個省級單元之間的協同發展,但不利于自身內部的協同。天津核心主要表現為屏蔽效應,且對北京邊界地區的屏蔽效應最為顯著;這種屏蔽效應容易出現的“空間鴻溝”表明,在京津一體化過程中,天津核心地區發展聚集了邊界地區要素,在區縣空間尺度上不利于地區協同發展。河北的核心城市石家莊僅對本省的邊界地區表現為明顯的“空間溢出中介效應”,表明石家莊作為省會城市,其經濟增長確實帶動了外圍地區發展。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除了三個省級單元之間的協同外,北京主城區應該加強對自身郊區的聯系和協同,充分發揮核心對外圍的空間溢出效應;天津需要盡快打破邊界限制,與北京周邊地區共同促進,從京津冀全面協同角度擴大發展空間;河北則需要強化中心城市功能,促進中心城市對整個地區的帶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