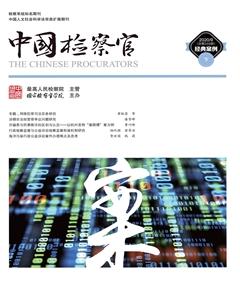非法買賣“套卡”的行為定性
鐘莉
一、基本案情
2019年1月至5月期間,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伙同曾某、楊某某、劉某某等人,多次非法買賣他人銀行卡及信息資料(俗稱“套卡”),牟取非法利益。犯罪嫌疑人楊某某主要負責在網上尋找銀行卡買家、收取錢款以及將買家需求信息轉發曾某等事宜,李某某和曾某主要通過在QQ群、微信群發布兼職消息的方式招募他人辦理銀行卡并予以收購, 劉某某則按照楊某某和曾某的要求將銀行卡及信息資料郵寄給外地買家。經查,本案涉及銀行卡104張,其中已倒賣48套,每套含有銀行卡、U盾、電話卡、身份信息、U盾登陸密碼、取款密碼等物品和信息資料;查獲未及出售的銀行卡56張,其中包含18張單位結算卡并附有開戶資料、取款密碼等信息資料,其余38張銀行卡未發現相關信息資料。上述案件事實有銀行轉賬記錄、信用卡買賣清單、微信聊天記錄、證人證言以及犯罪嫌疑人供述等證據證實。
二、分歧意見
案件辦理過程中,對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等人構成何種犯罪存在較大爭議,主要有以下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當認定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理由是:司法實踐中,類似案件多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定罪處罰。[1]本案中,李某某等人以牟利為目的,低價收購他人信用卡后高價出售,其已出售部分系對他人信用卡的曾經持有,未及出售的部分系對他人信用卡的現實持有,涉及信用卡數量應累計計算,共有104張,已達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數量巨大”的標準,其行為應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等人收購的他人信用卡中,有38張未發現相關信息資料,對該批信用卡僅成立“非法持有”,應當適用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其余66張信用卡因附有相應的信息資料,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等人的倒賣行為同時觸犯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應從一重罪處罰。由于以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數量巨大”的標準為5張以上,明顯低于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50張以上,以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對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更重,故應當適用此罪。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等人收購他人信用卡104張,已達刑法第177條之一規定的“數量巨大”標準,認定其是否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關鍵,在于厘清刑法意義上“信用卡”的含義以及對他人信用卡“非法持有”狀態的認識,具體分析如下:
1.本案銀行卡屬于刑法意義上的“信用卡”。根據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有關信用卡規定的解釋》,刑法中規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業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發行的具有消費支付、信用貸款、轉賬結算、存取現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電子支付卡。需要說明的是,刑法對信用卡持有人的身份并未做限制性規定,可以是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具有信用卡申領資格的主體,關鍵在于涉案“信用卡”是否系金融機構發行且具備上述功能。本案中,李某某等人非法買賣的自然人銀行卡以及單位結算卡均具有消費支付、轉賬結算、存取現金等功能,屬于刑法意義上的“信用卡”。
2.收買他人信用卡可以認定為“非法持有”。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中的“非法持有”,是指行為人所持有的信用卡既不屬于本人又無法說明其合法來源。根據中國人民銀行1999年發布的《銀行卡管理辦法》第28條的規定,銀行卡及其賬戶只限經發卡銀行批準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轉借。由于出售行為的危害性比出租、轉借行為更大,據此可以推定,該《辦法》當然也禁止持卡人將本人銀行卡出售他人,即出售行為本身不合法,這就決定了因收買而持有他人銀行卡的行為是違法行為,應當認定為“非法持有”。
3.“曾經持有”可認定為“非法持有”。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曾經持有”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比較常見,通常情況下,犯罪嫌疑人在到案之前,已將通過盜竊、收買、欺騙等非法手段獲取的他人信用卡轉賣他人或者轉移他處,在抓捕的過程中難以做到人贓俱獲,以致不存在“現實持有”的狀態。但若確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曾實施了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的行為,則應當認定為“非法持有”。本案中,雖然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等人被抓獲之前,已將收購他人信用卡當中的48張通過郵寄的方式轉賣給了網絡買家,但有信用卡買賣清單、證人證言、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等證據證實其曾經具有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的行為,故對該批信用卡可以認定為“非法持有”。
4.“非法持有”不應限于身體上的直接接觸。刑法意義上的“非法持有”應當根據行為人對特定物品享有的實際控制權做判斷,而不應局限于行為人對該物品有身體上的直接接觸。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楊某某主要負責尋找網絡買家、將買家的需求信息以及相應的錢款轉發曾某,在整個買賣信用卡的過程中,楊某某對涉案信用卡并沒有身體上的直接接觸,但應當認定為“非法持有”。理由有:一是犯罪嫌疑人李某某與楊某某等人基于共同的犯意,事前有預謀;二是犯罪嫌疑人楊某某按照分工,事中有提供信用卡買賣信息的行為并在交易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三是犯罪嫌疑人楊某某事后參與了非法獲利分成。因此,犯罪嫌疑人楊某某等人的行為應認定為共同犯罪,楊某某對涉案信用卡享有實際控制權,應當認定為“非法持有”。
(二)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構成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
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是指竊取、收買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情節嚴重的行為。司法實踐中,非法獲取或者非法提供的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大多流向犯罪集團用于偽造信用卡,但難以查明行為人非法獲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的目的是用于偽造信用卡或者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資料的行為人與偽造信用卡者之間有共同犯罪的故意,而竊取、收買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的行為確實對金融秩序安全具有很大的破壞性,故《刑法修正案(五)》增設了本罪。[2]
本罪侵犯的對象是持卡人的信用卡信息資料,且應當屬于信用卡的核心信息,非核心信息不能構成本罪。一般而言,信用卡核心信息主要以下特征:一是直接決定信用卡的消費、取現、透支等功能的正常使用;二是信息的泄露會直接、緊迫的影響持卡人利益;三是該信息具有絕對的隱秘性和排他性。[3]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0年發布的《銀行卡磁條信息格式和使用規范》,信用卡信息主要包括:主賬號、發卡機構標識號碼、個人賬戶標識、檢驗位以及個人標識代碼(密碼),這些信息無疑屬于信用卡核心信息,掌握這些信用卡信息資料,是信用卡正常使用的前提。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等人倒賣的他人信用卡賬戶名、卡號、U盾登錄名、U盾登錄密碼、U盾支付密碼、取款密碼等信息屬于刑法意義上的信用卡核心信息資料并無爭議。本罪系選擇性罪名,犯罪嫌疑人既有收買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的行為,又有出售(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的行為,且涉及信用卡66張,已達刑法第177條之一規定的“數量巨大”標準,其行為已構成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以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對犯罪嫌疑人定罪處罰,需核對相關信用卡信息資料在竊取、收買、非法提供時的真實性,對賬戶名、取款密碼等關鍵信息與信用卡不相匹配的,不能計入涉案信用卡數量。
(三)本案同時觸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與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應從一重罪處罰
一是犯罪嫌疑人的行為系一行為同時觸犯多個罪名,應當從一重罪處罰。關于犯罪嫌疑人倒賣他人信用卡的行為,有觀點認為應當分解為收買、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及信息資料的行為和出售(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及信息資料的行為,由于收買和非法持有行為只是手段,向他人“非法提供”牟利才是目的,故兩個行為之間具有牽連關系,對兩個行為的刑法評價有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應從一重罪處罰。[4]筆者認為,應當將整個倒賣過程視為一個行為,其中收買、非法持有、出售等行為只是倒賣行為的一部分,即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等人在實施倒賣行為的過程中,既有收買、非法持有、出售他人信用卡的事實,又有收買、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的事實,系一行為同時觸犯多個罪名,應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處罰。就本案而言,是否將倒賣行為視為一個行為并非問題的關鍵,因為不論是牽連犯,還是競合犯,其最終處理結果都應遵循從一重罪的處罰原則。本案中,買賣的66張信用卡附有相關信息資料,不論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還是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均以達到“數量巨大”的標準,依照刑法第177條之一第1款的規定,應當在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法定刑幅度內定罪處罰。但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的規定,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數量巨大”的標準為50張以上,而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涉及信用卡“數量巨大”的標準為5張以上,后者“數量巨大”的標準明顯低于前者,故認定為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量刑應當更重,應當適用此罪。
二是認定為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更符合立法本意。以“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認定犯罪嫌疑人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其立法原意是犯罪嫌疑人“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的目的難以查清,且犯罪嫌疑人無法說明信用卡來源的合法性,但該行為又嚴重妨害國家對信用卡的管理,存在冒用持卡人名義使用信用卡或者將信用卡及其信息資料非法提供給他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可能性,導致信用卡管理秩序和持卡人合法權益存在受到侵害的現實危險性,出于防止這種危險性的實現以及打擊犯罪的需要,在立法上采取的一種現實的、簡易的處理手段。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收買他人信用卡及其信息資料行為的目的業已查清,即向他人高價出售謀取不法利益。同時,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并不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的名義進行交易,需要掌握與該信用卡配套的賬戶名、登錄密碼、取款密碼等信息資料,才能保證他人冒用持卡人名義進行正常交易,故收買、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行為的危害性相較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行為更為直接、緊迫且嚴重,以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追究李某某等人的刑事責任更符合立法精神, 也更有利于打擊和震懾犯罪分子,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注釋:
[1] 截止2020年3月20日,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查到,自2008年以來,案由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判決書有5100份,而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罪的判決書僅39份,大部分買賣信用卡及信息資料的案件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對被告人定罪處罰。
[2]參見張軍主編:《刑法[分則]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607頁。
[3]參見俞小海:《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司法適用》,《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2013年第5期。
[4]參見盧勤忠:《信用卡信息安全的刑法保護——以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資料罪為例的分析》,《中州學刊》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