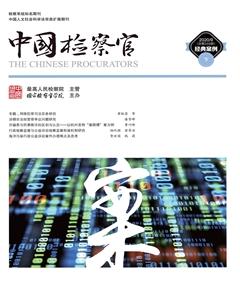銀行職員利用職務便利進行欺詐行為之定性
楊蘭
摘 要:在銀行職員偽造存單、運用過期存單或偽造公章在存單上蓋章等,再利用職務便利對客戶進行詐騙這一類型的案件中,由于存在著民事關系與刑事行為的重疊交叉,對于案件性質的認定存在一定的困難。認定財產損失由誰承擔是此類案件定性的關鍵點。根據整體財產說的基本規則,在轉移交付前后財產沒有減少,原則上就排除財產損失的成立;而詐騙行為的實施則使被害人的財產消極減少或受損。因此,銀行職員利用職務便利對客戶進行欺詐,侵占的是單位財產,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職務侵占罪,而不成立詐騙罪。銀行需要對客戶的損失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關鍵詞:詐騙罪 職務侵占罪 職務便利 整體財產說
【基本案情及判決結果】
原告劉磊于2013年5月31日在被告山東鄒平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子支行鎮中分理處存款人民幣2000萬元,經辦人是段振峰(被告處原支行行長)、張寅(被告處原銀行職員),二人因涉嫌偽造金融票證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追究刑事責任。段振峰、張寅等人采用非陽光操作的犯罪方式將被告賬上沒有實際存款的無效存單交付原告劉磊,騙取原告款項。因段振峰、張寅的行為構成犯罪使得原告的存款至今無法兌現,并且原告的款項沒有經過刑事處理。原告劉磊認為被告山東鄒平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子支行鎮中分理處應當承擔該筆存款的賠付責任,故提起訴訟,要求被告賠付2000萬元的存款及利息。被告辯稱原告所主張的資金涉及犯罪,涉案資金已經通過法院作出的刑事判決書認定和處理,被告作為單位不應當承擔刑事犯罪人因為犯罪而產生的責任,銀行沒有占有涉案資金,原告主張的資金應當按照刑事追贓、退賠程序予以處理,本案刑事追贓、退賠程序尚未完畢,不應當通過民事程序處理。再者,原告資金沒有交付給被告,原告所主張的存單存款關系不真實。
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認為,本案糾紛的實質是犯罪分子誘騙原告在被告處開設存款賬戶并存入款項而引發,這使得涉案儲蓄存款合同在簽訂及履行過程中均存在犯罪分子的欺騙手段。盡管存款無效系犯罪行為所致,但原告是在被告的營業場所、營業時間,按照被告工作人員指示辦理轉存款業務,收款人劉哲的名字和賬號并非原告劉磊提供和填寫,而是被告工作人員張寅利用職務便利,在柜臺里將原告的錢轉到用款人創能石化公司楊玉峰控制的劉哲賬號,被告的職員張寅把偽造的被告印章的假存單從柜臺窗口交給原告劉磊,原告劉磊在存單到期后支取遭拒時才被告知存單系偽造,原告劉磊遭受的資金損失主要原因系被告對其支行行長和職員監管不到位致其工作人員違規操作騙取了原告對銀行的信任,被告作為從事金融業務的專業人士,應對其工作人員的行為負擔大部分責任。
本案判決如下:被告山東鄒平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子支行鎮中分理處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對原告劉磊的存款本金1556萬元及利息(自2015年6月至付清之日止利息,按年利率3.3%計算)承擔80%的賠償責任;被告山東鄒平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子支行對被告山東鄒平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子支行鎮中分理處的財產不足以清償上述債務的部分承擔補充賠償責任。
【爭議焦點】
本案的關鍵點就在于,銀行職員利用“假存單”騙取客戶的存款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構成什么罪。如果銀行職員的行為構成詐騙罪,那么受害人應當通過刑事退贓、退賠程序對存款進行追償;如果認定銀行職員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而是構成職務侵占罪,那么就應當由銀行來承擔對客戶的賠付責任。
【裁判理由及法理評析】
銀行職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對存款人進行欺詐,最終將該筆存款據為己有的行為僅構成職務侵占罪而不構成詐騙罪。對于該類案件,需要進行兩個方面的判斷,一方面是如何認定該筆存款的占有,另一方面是財產損失最終由誰來承擔。
(一)財產占有之認定
客戶的存款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現金形式,一種是在同一個銀行內部進行轉賬的形式。筆者將就兩種形式分別進行論述。
銀行職員與銀行之間屬于民法上的雇主與雇員的關系,雇員在職權范圍內履行職務的行為所產生的法律后果應當由雇主來承擔。銀行通過招募員工、培訓員工的方式,使其能夠獨立地對外承擔業務,相當于將自己的一部分權利讓渡給了銀行職員,因此,客戶通過銀行職員業務范圍內進行的存款行為,就相當于銀行本身的行為。銀行雖然已經明令禁止職員使用假存單,但是,該規則無法對客戶產生效力,客戶無法隨時掌握銀行內部的具體操作流程的。銀行有義務保證其員工都按照操作細則進行業務辦理,如若職員違規操作,或者鉆“漏洞”,由此產生的風險應該由銀行承擔,而不能將風險轉嫁到客戶身上,客戶對此不存在民法上的主觀過錯,就應當認定銀行與客戶之間簽訂的儲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如果存款是以現金的形式交付,雖然該筆存款是由客戶交給柜員,其中不曾經過他人之手,但是,由柜員實際上控制的存款就是歸屬于柜員占有的嗎?答案是否定的。實際控制不等于民法意義上的占有,該筆存款在離開銀行之前,應當是由銀行占有的。有學者認為,刑法上的占有與民法上的占有是不同的,刑法中的占有更加強調事實上的占有,而此案中,由于銀行職員對于客戶的存款的占有具有強大的事實上的占有,就應當認為該筆存款在客戶交給銀行職員時,就是由職員占有而非銀行占有。但是,正如筆者前文所述,由于職員辦理業務的法律后果是由銀行來承擔的,因此,客戶是與銀行簽訂了有效的合同。既然合同有效,當客戶將存款交給銀行職員的時候,雖然是由柜員實際控制該筆存款,但只是輔助占有,銀行對其職員在工作中收到的每一份儲蓄現金都有占有意思,這種占有意思不必具體到現金來自于誰、數額是多少等細節。[1]所以,基于民法上的雇主雇員關系以及客戶與銀行之間簽訂的合同關系,該筆存款實際上是由銀行占有的。即使承認刑法意義上的占有與民法意義上的占有有所不同,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忽視規范上的占有。規范因素的作用主要是用來補強和支持事實因素。一個加之于財物上的占有狀態,通常由事實上的控制力以及規范層面上對控制的認可共同組成,兩者之間互相補強。[2]因此,在事實上的支配力不夠強大時,若規范上的控制力足夠強大,在一般人的認知中可以認定物品的歸屬,那么久足以彌補事實上控制力的不足。本案中,按照規范層面上來說,都會默認該筆存款處于銀行的支配之下,因為銀行可以在銀行職員離開銀行之前,隨時取回該筆存款,因此,該筆存款在刑法意義上也是處于銀行的占有之下的。并且,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存款是處于銀行和職員的共同的事實占有的狀態下。這時,對于事實占有的強弱不會決定存款的占有歸屬,而是應當根據規范進行判斷,顯然銀行在規范上占有更強,由此判斷該筆存款應當是由銀行占有的。
如果該筆存款是以銀行內部的轉賬形式進行的,那么,該筆存款一直都處于銀行的控制之中自不必言,雖然,客戶轉入的賬戶并非自己的賬戶,而是銀行職員提供的他人的賬戶,但是,該筆存款由本行的一個賬戶轉移到另一個賬戶上,銀行對于該筆存款的控制狀態并沒有發生改變,因而,銀行一直處于對該筆存款的占有狀態中的事實應當是沒有異議的。
(二)財產損失之認定
關于本案的財產損失的認定,筆者認為,本案中只有銀行遭受財產損失,客戶是沒有財產損失的。本文采取的是整體財產說的觀點。
對于詐騙罪中財產損失的認定,學界有幾種不同的學說。日本刑法學界采用的“形式的個別財產說”與“實質的個別財產說”,德國刑法學界的通說“整體財產說”。“財產損失”在詐騙罪中的定位與認定對于詐騙罪的成立與否有著重大的影響,因此,對“財產損失”予以正確定位至關重要。“形式的個別財產說”認為,通過欺騙使對方陷入錯誤認識,對方繼而交付財物的行為就成立詐騙罪。因交付而轉移的個別的物或利益的喪失本身,就是詐騙罪中的法益侵害,這樣,詐騙罪被認為是針對個別財產的犯罪。[3]形式的個別財產說不關注行為人是否給予對待給付,即使受騙人獲得了相對應的給付也不能成為犯罪阻卻事由,因為這種對待給付只是詐欺行為的一種手段而已。在可以認為如果被告知真相對方就不會交付財物的場合,即使提供了與財物價值相當或超過它的代價,也不妨礙詐欺罪成立。[4]形式的個別財產說對于法益的保護范圍有明顯擴張趨勢,因而基本已被排除適用。“實質的個別財產說”認為,詐騙罪畢竟是侵犯財產的犯罪,保護的應當是財產的所有權及其本權,詐騙罪的認定不能只考慮財產的交付,還應當著眼于受騙人的實際財產損失以及財產作為交換手段、目的達到手段的意義。“整體財產說”認為,詐騙罪的成立以被害人整體財產減少為必要。[5]整體財產說不僅要考慮客觀經濟的實際損失,還應考慮財物的交易目的是否實現。整體財產說的基本規則是,僅當客觀經濟和主觀交易目的都沒有損失時,才能當然排除財產損失的成立。實質的個別財產說與整體財產說存在以下兩方面區別:首先,德國刑法明文規定詐騙罪是針對整體財產的犯罪,因而會比較整體財產在轉移交付前后的得失。沒有減少,原則上就排除財產損失的成立,但如果在交易目的實現與否的判斷中,確定交易目的失敗或落空,就成立財產損失;而實質的個別財產說肯定財產損失的成立原則是財產的移轉,以被害人的錯誤與財產沒有實質關聯作為例外。兩者對于財產損失理論架構的基礎理解不同,判斷路徑也就存在不同。其次,在數額認定方面,實質的個別財產說是基于詐騙罪是針對個別財產犯罪的理論出發的,其會將被騙人轉移或交付的所有財產當作財產損失的數額,并不會考慮行為人是否有給予對待給付等情形;而整體財產說則會考慮行為人是否提供了相應的對價給付或提供了部分的給付,從而將給付的部分予以扣除。筆者經過比較認為,整體財產說的觀點更為合理,因而本文采用整體財產說的觀點。
就本案而言,在運用具體的學說對財產損失進行認定之前,需要先行確定的是,判斷詐騙罪損失的時間點應當是行為人處分財產的時候,而非最終看誰遭受損失來認定,如若這樣,詐騙罪的成立就存在不確定性。本案中,客戶處分財物的時刻是其將存款交給銀行職員的時候。司法實務中,有時會根據最終時刻來認定行為的性質,如果銀行最后賠償了存款人的損失,則由銀行承擔最終損失,行為人構成職務侵占罪;如果銀行拒絕賠償或者最終無力賠償,則由存款人承擔最終損失,行為人構成詐騙罪;如果銀行和存款人都遭受損失,則行為人構成詐騙罪與職務侵占罪數罪。雖然這一判斷方式非常簡便、直接且有效,但是其弊端也是不容忽視的。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其后果的不確定性,要依靠最終銀行是否賠償存款人的存款來進行認定。明明就實施了相同性質的行為,卻因為銀行的賠付與否使得性質發生變化,筆者是無法贊成這一判斷方式的。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在一個固定的時間點來判斷受害人是否遭受財產損失。這一時間點應當是存款人將存款交給銀行職員的時候。接下來,根據整體財產說的理論進行判斷:
首先,從財產的客觀經濟價值來判斷,受騙人沒有遭受損失。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存款人單方面進行了金錢的給予,但是,實際上并不是如此。存款人是否遭受客觀經濟上的財產損失應當根據其與銀行簽訂的合同的權利義務來綜合考量其是否獲得了相應的對待給付。筆者已經在前文對銀行與存款人之間的合同的效力進行了認定,該存儲合同應當是有效合同。既然該合同是有效的,那么在存款人將存款交給銀行的時候,銀行就承擔了返還該存款給客戶的義務,存款人由此獲得了將來從銀行方面收回該存款的債權,因此,雙方的權利義務是相當的,存款人可以說是獲得了相應的對價給付。雖然銀行職員對存單等事項進行了偽造隱瞞,但是并不影響該合同的效力,法律后果至始至終都是由銀行承擔的,至于銀行職員的違規操作,應該由銀行內部進行處分解決,而不能對外產生任何效力。因此,客戶在客觀上不存在財產損失。
其次,從財產的主觀價值來判斷,存款人的交易目的已經達到,所以財產的主觀價值也是沒有遭受損失的。同樣,在合同有效的情況下,存款人的經濟交易目的已經達成。存款人將一定數額的金錢存在銀行里,不論是活期的還是定期的,由于合同有效,銀行必須履行合同義務,在合同內容范圍內不得拒絕向存款人履行義務。因此,存款人的經濟交易目的是一定能夠獲得實現的。
根據上述對于財產占有與財產損失的分析,受騙人沒有遭受損失,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應當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構成詐騙罪。
(三)職務侵占罪的認定
本案中,銀行職員的行為成立職務侵占罪。根據刑法第271條規定,職務侵占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由于該筆存款在交給銀行職員時,已經是歸銀行占有了,因此該筆存款是銀行的財產。既然是銀行的財物,銀行職員利用其職務上擁有可以直接控制該存款的條件,將該筆存款非法占為己有,明顯已經符合職務侵占罪的構成要件,其認定應該不存在困難。雖然本案對于銀行職員的定性為偽造金融票證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但筆者認為,應當以職務侵占罪進行定性,偽造金融票證的行為只是職務侵占的手段行為,以職務侵占罪一罪認定更為合理。
(四)結論
在司法實踐中,銀行職員虛造金融票證,讓銀行客戶誤以為其存款以及存入銀行或購買了銀行理財產品的情況屢有發生。在這類案件中,只要抓住行為的關鍵,即能夠對錢款的占有、合同的效力以及財產損失的承擔做出分析,就能夠明確民事關系與刑事行為的界限,做出合法合理的判斷。
注釋:
[1]參見郭利紗:《從一起銀行職員詐騙案看刑民交叉案件的定性》,《中國案例法評論》2017年第2期。
[2]參見[德]ingebory Puppe:《法學思維小課堂》,蔡圣偉譯,元照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37頁。
[3] 參見[日]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王昭武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頁。
[4]參見[日]大塚仁:《刑法概說各論》,馮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頁。
[5]參見 [日]林干人:《刑法各論》,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年版,第1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