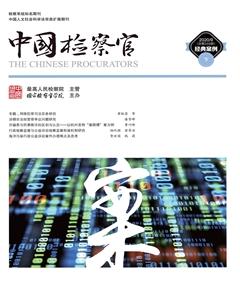論儲蓄存款合同中銀行的附隨義務
梅駿峰
一、基本案情
2014年4月,盧某某經人介紹在衢州市工商銀行某支行辦理所謂高額年息業務。當天,盧某某在該支行辦理了一張工行卡,并轉入該卡人民幣1000000元。之后,詐騙分子祝某某以打印對賬單為由誘騙盧某某提供身份證、銀行卡,在盧某某不知情的情況下填寫一份轉賬匯款單(收款人:祝某某,金額1000000元;客戶簽名:祝某某代)。祝某某將盧某某的身份證及銀行卡、本人的身份證及銀行卡、轉賬匯款單交給該支行柜員,并在該柜員前就坐,辦理轉賬業務。當密碼器提示“請輸入密碼”時,柜員讓祝某某輸入密碼,祝某某轉過頭叫其身后的盧某某過來輸入了密碼。銀行工作人員提交客戶、代理人身份信息聯網核查,核對公民身份號碼與姓名一致、證件是否和代理人為同一人,通過現場審核蓋章后,銀行柜員將系統資料(卡號、金額、簽名、身份證是否聯網核查)提交上級分行授權,授權通過后銀行柜員打印轉賬回單交給祝某某,盧某某銀行賬戶中的資金1000000元即已轉到祝某某的銀行賬戶中。祝某某隨后轉賬給盧某某120000元作為貼息。后祝某某因涉嫌詐騙罪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經查,其在案發前已多次實施類似詐騙行為。祝某某因犯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但其無力向盧某某等受害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盧某某等受害人陸續以儲蓄存款合同糾紛為由提起民事訴訟,試圖追究相關銀行的合同責任。一審法院判決相關銀行賠償盧某某本金損失額度20%的民事責任。盧某某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對一審判決予以維持。這批類案經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再審申請后,陸續進入當事人申請檢察機關民事訴訟監督環節,并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
二、分歧意見
本案在審查過程中出現兩種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銀行在辦理案涉轉賬業務過程中并未違反相關的銀行業操作規范以及銀行儲蓄存款格式合同,無需承擔賠償責任。經檢索查詢,關于銀行轉賬匯款業務辦理的相關規定主要如下:《中國銀監會關于進一步加強銀行卡服務和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銀監發[2009]17號)規定,對借記卡存款、取款、掛失申請等業務,各銀行業金融機構應開放代辦業務;5萬元以上(含)取款、掛失申請,代理人提供雙方身份證即可辦理;《中國工商銀行個人境內匯款業務管理辦法》規定,匯款人以現金方式申請辦理個人人民幣匯款,以轉賬方式申請辦理大額個人人民幣匯款(金額在5萬元以上),以及辦理個人外幣匯款,須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證件。轉賬匯款如為他人代辦理,還須同時出示代理人有效身份證件。柜員應審核身份證件真實有效并摘錄相關信息;《中國工商銀行借記卡章程》規定,申請借記卡必須設定密碼。持卡人使用借記卡辦理消費結算、取款、轉賬匯款等業務須憑密碼進行(芯片卡電子現金交易除外)。凡使用密碼等電子信息辦理的各類交易所產生的電子信息記錄均為該項交易的有效憑據;《關于金融業務簽單服務管理辦法(2010版)》規定,經辦人員在審核憑證內容填寫完整、準確、無誤且客戶已簽名確認后,方可為客戶辦理相關業務。通過上述銀行業相關規定可知,以轉賬方式申請辦理大額個人人民幣匯款,可以委托他人辦理,代理人必須出示本人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證件、銀行卡、匯款憑據,代理人使用密碼的交易,銀行也視為客戶本人所為。就本案而言,盧某某受高息誘惑,將身份證、銀行卡交給犯罪分子祝某某,且未核對真實信息即聽從他人安排輸入密碼,造成其銀行卡內的存款被騙。而銀行工作人員在辦理案涉轉賬業務過程中已遵守銀行業相關規定,對相關人員的身份證件、銀行卡、匯款憑據等進行了審核,不存在違反法定義務或合同約定義務的情形,因此銀行無需對盧某某的財產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銀行在辦理案涉轉賬業務過程中存在一定過錯,應承擔相應民事責任。盡管銀行業操作規范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但是銀行作為專業的金融服務機構,其工作人員在辦理轉賬業務的過程中,發現代理人祝某某實際未掌握密碼,而是由客戶盧某某(或密碼輸入方)在場輸入的情況下,應當了解并詢問客戶詳情、審核代理人填寫的匯款憑證是否本人真實意思、告知密碼持有人輸入密碼的用途、及時提醒客戶注意義務。本案中,相關銀行工作人員并未履行上述通知、提醒義務。故銀行在辦理案涉轉賬業務過程中確有瑕疵,對盧某某賬戶內的存款被騙存在一定過錯,應承擔相應責任。
三、評析意見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儲蓄存款合同中銀行附隨義務的認定思路
檢索相關法律法規、銀行業操作規范以及銀行儲蓄存款格式合同,很難找出銀行在辦理此類業務時的不妥之處。銀行業畢竟是在千錘百煉中不斷糾錯、精密武裝免責條款的成熟行業。但在這批案件中,相關銀行的問題在于,其工作人員在操作代理大額轉賬業務時,發現代理人不知道密碼,而是由儲戶本人或者其他人輸入密碼的,并未通知、提醒儲戶或者輸入密碼者相關轉賬信息。這對于專業金融從業人員來說是不應該的。類似的詐騙行為其實也經常被媒體報道出來,而國內很多銀行的工作人員及時對儲戶通知、提醒,挫敗了很多類似騙局。事實上,履行通知、提醒義務對于銀行而言并非苛刻的負擔,但卻能有效揭穿類似騙局,堵住漏洞。與儲戶相比,商業銀行作為資金管理的專業性機構具有更強的風險防范能力和技術保障能力以確保儲蓄存款的安全。改進服務和保障資金安全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銀行的基本要求。而儲戶的風險防范意識、資金控制和保障能力都有所不足,明顯處于弱勢地位。在類似情形下,要求商業銀行履行通知、提醒義務是具有合理性的。正因如此,相關銀行在操作代理大額轉賬業務時確實存在過錯。
根據傳統合同法理論,合同當事人履行義務的范圍僅以合同約定為限。但隨著交易的不斷進行,人們逐漸認識到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因一方當事人未盡其應盡的照顧、通知、保護、保密、協力、忠實等非合同約定義務而致使另一方當事人受到損害,若這些損失僅因合同未約定而失去對過錯方的約束,則有違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1]誠實信用原則可以解決合同相對性理論所無法解決的債務人義務擴大問題。附隨義務以誠實信用原則為基礎,將道德上照顧、通知、保護、保密、協力、忠實等具體要求轉化為法律上的義務,使道德教化與法律規定有機結合,從而保護和平衡合同各方當事人的利益。
就本案而言,相關銀行作為儲蓄存款合同的一方當事人,雖然沒有違反銀行操作規范以及儲蓄存款格式合同,但違反了民法上的帝王條款即誠實信用原則。合同法第60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民法典第509條第3款的規定保留了這些內容。上述法律規定是基于誠實信用原則而衍生出對合同附隨義務的具體規定。這意味著,合同當事人不僅要全面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還要基于誠實信用原則而履行合同的附隨義務。附隨義務是指當事人依誠實信用原則,為保護契約當事人人身、財產安全所應負擔的通知、協助、保護、保密、忠實等義務,旨在衡平合同當事人之間以及當事人與社會間的利益關系,以實現實質正義。[2]合同附隨義務的概念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國民法判例與學說,原本是基于探討締約過失責任而提出的。[3]隨著合同附隨義務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化,它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特征:第一,合同附隨義務可存在于締約階段、履約階段和履約后階段,并不局限于締約階段,因此在時間上具有全程性;第二,合同附隨義務在地位上附從于主給付義務,并不能離開主給付義務而獨立存在,但其與從給付義務亦不相同,違反從給付義務的話當事人可以獨立訴請履行,而違反附隨義務的話當事人卻不能獨立訴請履行,只能請求賠償損失;第三,合同附隨義務是法定的強制性義務,“附隨”并不代表其不重要,其基于誠實信用原則而依法被確立,效力上具有強制性,并不能被當事人約定排除;第四,大多數合同的主給付義務和從給付義務在合同成立時即已確立,但合同附隨義務則明顯具有不確定性,其會隨著合同關系的不斷推進而變化,也會隨著當事人主體的不同而有所區別,還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在這批民事申請監督類案中,盧某某等儲戶輕信他人關于相關銀行存在不規范、不公開的高貼息存款業務的謊言,未向銀行工作人員深入了解核實情況即輕易地將銀行卡和身份證交給祝某某,并按照其要求輸入密碼,未能認真核對相關信息,其對于自身銀行存款被騙存在重大過錯,應當承擔主要責任。而這批案件所涉銀行作為專業金融服務機構在辦理大額代理轉賬業務時,發現代理人實際并未掌握密碼而客戶本人(或密碼輸入方)在場輸入的情形,應當及時通知、提醒客戶本人(或密碼輸入方)注意該大額代理轉賬業務的相關信息,切實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履行儲蓄存款合同的附隨義務。但其并未履行通知、提醒義務,故對盧某某等儲戶的銀行儲蓄存款損失應當承擔一定比例的責任。值得一提的是,因該民事責任是基于違反合同附隨義務所產生的,故屬于合同責任范疇,而非侵權責任。
(二)類案不同判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這批民事申請監督類案其實共分成三類。前文所闡述的是第一類,法院判決相關銀行承擔儲戶本金損失額度20%的民事責任。第二類是部分儲戶其實知道祝某某在代理轉賬業務,并自愿輸入了密碼,他們相信資金需要投入其他用途,但還是安全的。在這類案件中,由于儲戶對轉賬信息是知情的,銀行未通知、提醒轉賬信息與儲戶受損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故法院未支持儲戶對銀行的索賠請求。第三類情形與第一類情形相似,唯一的區別在于相關銀行裝配了“柜外清”,這種裝置可以在銀行營業場所對交易信息進行語音播報和文字公示,但效果受現場環境影響,播報和公示信息未必能讓每個在場儲戶完整接收。在第三類情形下,法院認為安裝了“柜外清”的銀行盡到了部分通知、提醒義務,但由于這些儲戶實際上并未接收到轉賬信息,所以判決案涉銀行承擔10%的民事責任。總體而言,根據銀行是否完全履行了儲蓄存款合同的附隨義務,以及銀行的行為與儲戶所受損失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等因素來對銀行所應承擔的賠償責任予以認定,是妥當的。正因如此,衢州市檢察機關民事檢察部門在審查后對這批民事申請監督案件均作不支持監督申請決定處理,并對原審判決的說理內容予以適度充實和完善。
(三)案件辦理后的社會效果
這批案件的辦理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一方面,這批案件辦理后,衢州當地的相關銀行深受觸動,紛紛開始對鏡自照,排查風險隱患和制度漏洞,特別是在辦理類似的代理大額轉賬業務時,要求其工作人員務必履行對在場的儲戶本人或者輸入密碼者的通知、提醒義務,預防類似騙局再現。另一方面,這批案件的辦理推動了相關銀行安裝“柜外清”裝置。“柜外清”能幫助銀行盡到通知、提醒義務,減輕銀行的民事責任,于是很多銀行也開始裝配此類設備。總而言之,衢州當地的相關銀行吸取了這批案件的教訓,當地銀行業因此越來越規范,類似騙局很難再現,體現了民事司法對社會活動的正確指引功能。
注釋:
[1]參見李敏:《合同法中的附隨義務探討》,《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
[2]參見宋建立:《儲蓄存款合同中的附隨義務及責任》,《人民司法》2009年第3期。
[3]參見李偉:《德國新債法中的附隨義務及民事責任》,《比較法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