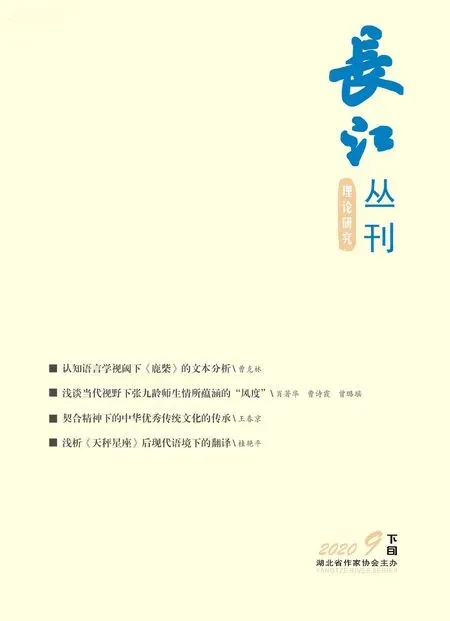認知語言學視閾下《鹿柴》的文本分析
■曹克林/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
一、前言
認知語言學作為一門新型、新興的社會科學,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以認知科學和語言學兩門跨領域專業(yè),宣揚了文本研究中語言的工具性作用。萊考夫(Lakoff)試圖糾正我們兩千多年的錯誤觀念,并認為我們所處的階段是研究的轉折期[1]。以經驗和思維認知為出發(fā)點,力圖透過語言現象來探求外部世界規(guī)律。
詩歌和語言相融相成。文本研究是挖掘詩歌內蘊的手段,就文學批評而言,其廣義范疇包括電影、電視、戲劇等一切有藝術研究價值的文本內容,而狹義范疇是指以英美新批評理論關注和聚焦的文本(text),本文以王維《鹿柴》具體文本為載體,結合美國詩人艾略特·溫伯格在《觀看王維的十九種方式》①提供新穎的視角和解讀空間,通過認知語言學視閾重新審視文本,運用相關理論視角在文本研究中找到新的文學空間和詩意道路。
《鹿柴》(唐)王維
空山不見人,(1)
但聞人語響。(2)
返景入深林,(3)
復照青苔上。(4)
1200年前的唐朝大地,空山、深林、落日以及鋪滿地的青苔,千年煙云化為語言低吟和字符象征,千載春秋自成為時空敘事與詩歌空間。在認知語言學框架下“認知模型體現并尊重其內容,其有意識地運用于概念內容之中,而認知模型結構往往內化于形式分類與成因。”[2]詩歌迷霧現象背后的結構和機制,需要從文本內部的詞匯、符號和意象等來解密。
二、詩歌——認知:經驗之詩
認知語言學是一門內含語言學和哲學理論的學科,從笛卡爾、康德到20世紀邏輯實證主義,語言作為思想的外衣,參與詩歌文本的剖析。從日常經驗到詩歌經驗,既要跨越基本語言交流的范疇,也要借助語言工具對經驗進行認知。喬納森·卡勒在談到抒情詩時強調“詩居于文學經驗的中心,因為它最明確地強調了文學的特殊性,強調了與用以表達個人對世界的經驗感受的普通話語之間的區(qū)別。……詩的特殊性已經改變了這一語言交流范疇。”[3]人是理性的存在,語言的獨立性以符號搭建詩歌與世界的內在聯系,客觀上認識世界最簡單的方式是通過器官完成感知,而主體生活在觀察、認知和闡釋中實現詩歌經驗的構建。
《鹿柴》文本僅有二十字,然而內蘊豐盈。從表征風格而言,“山”與“人”的關系是古典詩歌的常見圖像,根據經驗主義認知理論,第一,詩歌思維不能脫離形體。“鹿柴”之名不是虛指,在溫伯格的日常經驗中,此乃詩人曾居住過的現實空間和地域場所,它類似于伊利諾伊州的Deer Grove(地名),客觀之物絕不是“鹿+柴”的拼湊;第二,詩歌思維不能缺少虛構。中國詩歌的經驗不同于龐德闡釋的意象——借助科學研究式的方法對詩歌生命內部機制和詩歌基因進行試驗、解剖。不言而喻的是對原詩進行切割、組合與改造,確實能給人帶來“陌生化“體驗,而“斜斜刺入”的層次感、“人語響”的運動感、“山不見人”的空間感等營造的虛構空間是中國古典詩歌獨特審美和“余韻”存留的需要。
三、范疇——原型:符號之詩
詩歌從日常過渡到經驗,符號發(fā)揮重要作用,在認知邏輯中,解讀詩歌即是認識世界,完成該過程需要兩個步驟:其一,從低級到高級的進階。即人需要從已有經驗的中建層面,向更高的向度延伸;其二,從具象到抽象的符號。即一般認知的思維邏輯傾向于直接的、形象的和具體的可接觸經驗完成對于客觀物象的描述、闡釋。“但是從有了符號功能之后(言語、象征性游戲、意象,等等),不是現實的感知的情境也可以重視,即有了表象或思維,于是我們就看到有最初的反映抽象作用出現了。”[4]詩歌固有的凝練性和跳躍性,在符號抽象化中完成“加密”,那么,文本闡釋要完成對符號的“解碼”。
語言的產生是世界認知的需要。所謂范疇-原型理論,就是對復雜事物進行分類、歸化與整合,以達到對事物概念化和理論化的高級別認知,《鹿柴》語言之詩與精神之思,符號簡化詩歌并走向詩意,劉若愚在《中國詩藝》里宣揚使用“新批評”技巧來闡釋中國詩歌,并強調詩歌感官的非歷史、非傳記性,這種主體性的弱化在詩歌翻譯的被動語態(tài)中足可見,一花一沙一世界,在詩歌局部性的空山、人語、聲光、苔蘚等客觀“零部件”中,詩人向我們呈現的是可預見世界的整體性,從生態(tài)主義角度而言,意象所呈現的符號、概念體現著天人合一、眾生平等的協(xié)和,正如帕斯在提到《鹿柴》的翻譯時,將其難度歸于語言背后的本質:中國詩歌的無個性、無時間、無主體以及普遍性。
四、隱喻——象征:想象之詩
詩歌的深度離不開隱喻和象征。作為人類認知世界的重要方式——通過一個事物的認識、理解、思考表達來表達另一事物的概念性過程,隱喻逐漸成為語言學的熱門話題,在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等人的研究中,一切新的知識都是建立在原框架的基礎之上,而隱喻作為一種認知方式有助于理解另一種語言范疇[5]。
詩歌因隱喻和象征具有了深度和高度。所謂隱喻就是從源域映射到目標域的一種切換,利用一種已有的、掌握的概念領域說明和闡釋另一種陌生的、新興的概念領域。這種隱喻機制在詩歌闡釋和創(chuàng)作中都普遍存在,前者是由已知概念投射到未知概念的解釋,后者是由陌生概念替代熟悉概念的間離。當然,就認知語言對文本的分析,個體在這種認知模型中無時無刻不受到所處社會、文化、人際等多重空間的影響,存在于個體自由的心理機制的模型,即隱喻的輸入空間和輸出空間的投射。
詩歌的認知過程也是建立在語言和思維的心理機制上的觸發(fā)與整合過程。狄爾泰談到想象賦予歌德詩歌的力量時稱“想象被編制進整個心靈地關聯之中。在日常生活中發(fā)生地任何傳達都本能地重新構成經歷過的事情……在想象地作用中建構起有別于我們的行為世界地第二個世界。夢是所有的詩人中最古老的詩人,在夢中構成中,虛構力本能地表現出來。”[6]從隱喻-象征視角審視《鹿柴》文本,僅就“鹿柴”之名就具有豐富內涵,按照弗萊徹的說法“柴”是“鹿歇息的地方,是鹿的form”[7],而使用form來翻譯“柴”,其背后隱含柏拉圖每個事物都有理念的哲學;程抱一的“返景”,是夕陽的落日之光,是暗影返回到幽深的森林里神秘與神圣;劉若愚譯文的“光”是余勁猶在的晚照,包含“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悵惘,溫伯格的夕光返照包含著自然界光度、光亮、清晰度等自然屬性的因子,也有延伸著啟蒙之光的精神屬性。飛升的綠色之光、運動的生命之光……“山“、“空山”、“荒山”的進階,“樵人”和“牧人”的出場,“返景”之夕和“復照”之光的投射,“青苔”與“青苔”的新認知思維等,文本浸透著認知和解讀的新內容,在轉譯和闡釋中,實現從一種認知空間進入到另一種認知空間的轉換。隱喻成為了顯性存在,透過詩歌特有的朦朧、詩意、隱含寓意,于俯仰、鼻息、忽閃間獲得頓悟。都在隱喻和象征的光影中見詩歌神與魄的猶存。
五、意象——圖式:空間之詩
意象是詩歌的靈魂。在認知語言學框架下從一個認知域到另一個認知域的意象圖式過程,是人與外部世界進行經驗聯動的抽象模型。這種經驗式“橋梁”是心理學家意象性和經驗性的圖式融合,即人的心理機制中的還原能力和信息組織加工的存儲能力的結合,不同于在萊考夫的意象圖式理論強調意象圖式來自經驗,皮亞杰在談到結構與功能時,懷疑心理學家集中力量從個體意義去理解主體,“在建構認知結構的情況下,不言而喻,‘體驗’只起到了很次要的作用。因為這些結構并不存在于一個主體的意識中,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這些主體是從來沒有意識到過這些作為整體結構而存在的結構的。”[8]而如果要從主體活動上說明其構造過程,這個主體專指認識論上的主體,那么主體的“親身經驗”就與人的生理和心理空間就變得不可分割,將意象圖式作為一種哲學理論,指導和推動定義、推理和意義等內容去認知客觀世界。
《鹿柴》熔鑄詩歌的物理空間、心理空間和精神空間三個層次。首先,物理空間是詩歌認識世界的基礎。龐德在“山”與“人”的雙重關系中偏愛“人”,兩條腿上的眼睛即是運動之眼,第三行第五個字“林”乃是雙木合成,是“森林”之意,而“入”和“上”兩個動作行為形象而準確地描繪了詩歌內部的空間關系;其次,心理空間是詩歌聯通世界的途徑。在詩畫合一的圖景闡釋中,山、人、光、聲的排列,深林、返景、復照、青苔的組合,通過個體的認知、體驗建構起符合讀者心理空間的“圖景”,“空山”是詩人的心靈棲息地,建構起不見一人的清寂、孤凄、獨我、忘我的心理空間;“深林”是詩人的修行場所,清風明月藏在衣領、袖子、褲腳乃至鼻息間,從意象圖示而言,這獨處的修行之地,光影沉沉、風輕人靜,詩人此在空間中完成人與世界的對話;最后,精神空間是詩歌闡釋世界的脈動。詩歌的文本分析離不開其背后的社會環(huán)境、文化內蘊以及精神傳達,“青苔”呈現的是精神微光,青苔占據的空間不大、體型不大、身影不大,但它所折射的力量是無窮的,復照于青苔,獨獨是青苔,不是外物,絕非詩人的偏愛,在微柔的青苔上幽微迷人、暗地生發(fā)、生機盎然的獨立之姿、人文之夕、精神之光將賦予青苔闊達的精神境界,在落日之夕潛入深林的剎那,浮動在青苔之上,空山、深林、樵人、牧人,山與人的還原、塑造、圖式,返景和復照的嵌入、飛升、相容。以自然審美和意象圖式筑造的空間,在詩歌文本有缺失、誤讀等闡釋中回歸到詩歌本質。
六、結語
詩歌闡釋不能停留在文本研究,要借助語言和理論工具進行挖掘。語言研究不能只滿足對其結構的描述,而不去探尋現象背后的本質,從規(guī)范到解釋,認知語言受到各種客觀因素的制約,但是,對于詩歌、小說和戲劇等文本研究,可以將嚴謹的、科學的語言學理論納入到原本夾雜個體主觀性和差異性制造的闡釋困境,為詩歌內部和外部研究和闡釋提供新視角和新方法。
以文本為本,遵循認知語言學的科學推理,進行抽絲剝繭的偵破過程,針對詩歌的虛實與情景等內在聯系,語言以“透明的眼睛”去認識理解人與世界、人和語言、語言與本質等多種關系背后的認知邏輯,就文本分析和闡釋,基于鑒賞主體的主觀性易導致差異性,要尊重文本研究的客觀事實,發(fā)掘詩歌文本規(guī)則背后的審美燭照與人文之光。
注釋:
①《鹿柴》文本分析中多處參考艾略特·溫伯格對詩歌翻譯、闡釋的內容,這里統(tǒng)一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