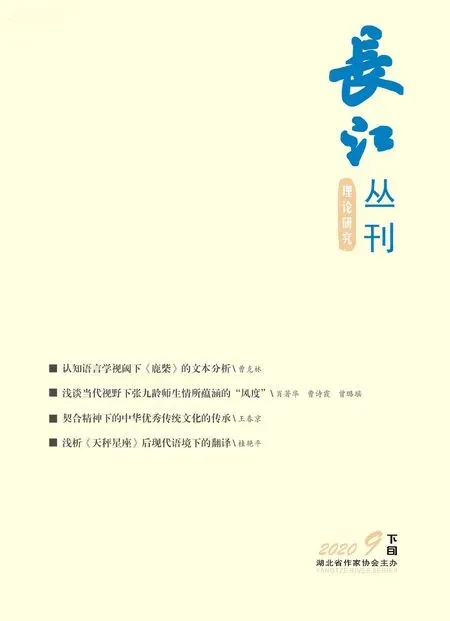淺析《天秤星座》后現代語境下的翻譯
■桂艷平/江西科技學院
Don Delillo(唐·德里羅)是美國當代出名的批判家、后現代主義小說家。《天秤星座》(Libra)于1988年出版,并在出版當年獲得“全美優秀圖書獎”的提名。作品以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害事件為主題,通過典型的后現代主義小說的敘事手法,勾勒出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多重可能性。小說中展現出的不確定性及削平深度的描述體現了后現代主義的明顯特征。小說受到了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影響。后現代主義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產生的現代派的一種文化思潮。它影響了多個學科領域,形成了后現代文學,后現代建筑,后現代繪畫,后現代哲學等,其思想顛覆了諸多固有的創作思想觀念,從而引起了各個領域的變革。受到后現代主義文化的沖擊,翻譯理論及標準問題也被重新審視,從而體現了多元化,多重可能性,開放性等諸多特點。本文以后現代主義小說《天秤星座》的翻譯為例,探討其翻譯中遵循的后現代翻譯標準。
一、解讀《天秤星座》
《天秤星座》以美國第35任總統肯尼迪遇害事件以背景,采用了推理小說及后現代敘事的手法,完美呈現出政治小說的精彩之處。小說通過主人公奧斯瓦爾德的人生經歷展現了美國20世紀50,60年代的社會現實環境。小說通過后現代主義的寫法,充分表現出不確定性及社會歷史的多重可能性。
(一)人物的不確定性
后現代小說中人物的不確定性具體表現為人物的破碎性及變化性。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邊緣化及主體意識消解的人。《天秤星座》的主人公奧斯瓦爾德就是這樣一種人物。他從小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想要改變生活現狀卻無法實現這一目標,甚至一度處于失業狀態,完完全全變成了邊緣化人物。他的思想也表現出其不確定性的特征,他渴望生活在烏托邦式平等的社會卻沒有平等地對待妻子;他追求民主、認為人人平等、希望革新、渴望思想進步,是一位具有左翼思想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卻做著右翼思想的事。小說的不確實性甚至還直接地從主人公的星座中體現,奧斯瓦爾德是天秤星座,其特征就是思想在天秤上不停地搖擺,正面時表現出穩穩當當,公平公正的性格,反面時卻呈現出情緒不穩,魯莽沖動的特征。無論是向左還是向右,他始終呈現出自身主體意識的淡化,不斷掙扎卻還是屬于邊緣人物。
(二)現實的不確定性
加拿大知名文學理論家琳達·哈琴在解讀后現代主義小說思潮時,提出了“歷史編纂元小說”的概念。這種政治或歷史小說公開顯現了在被創作時進行了梳理、選擇及建構的過程,它們將過去想當然地認定是真實的歷史知識置于懷疑的位置,表現出歷史真實的多種可能性。在《天秤星座》中描述了多種歷史真實,一是文本中作者虛構的歷史學家布蘭奇,帶著編纂真實歷史任務的他需要從眾多的歷史資料或文檔中進行梳理,然后篩選,從而編纂出宏達敘事的歷史真實;二是作者作為創作者也在史料的基礎上編排出另一種歷史真實,他展現給讀者一個變化的矛盾的世界,他引領讀者參與其中并進行判斷,讓讀者感受到歷史編纂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并對歷史本身產生更多的認識。
(三)情節的不確定性
情節的不確定性在后現代文學作品中多表現為內容的斷裂式或碎片式。情節描述中不再呈現出連貫性和一致性,給讀者一種雜亂無章的感覺,正是這種混雜無序的描述體現了現實生活的偶然性和不確定性。在《天秤星座》中,作者有意將各種碎片式的文本進行拼貼,以戲謔現實生活中無序的真實。如小說文本第23章中,作者虛構的歷史編纂家布蘭奇在整理材料時,直接把部分磁帶的錄音用文字的形式拼貼在小說的文本中,這種碎片式的拼貼在幾乎在小說的每個章節都有出現。這種不連貫的情節更加給讀者展現出歷史真實的不確定性。
二、《天秤星座》后現代語境下的翻譯
傳統的思維方式認為文字語言是一種自明性及特殊性的符號,語言具有確定性及規律性的特征,因而人們有能力認識及掌握語言。然而,后現代的思維方式否認了語言的這種屬性,認為語言是含混不清、模棱兩可的。在作品翻譯過程中,翻譯者作為一個主體的參與,必然將自身的意識形態,文學素養等糅合在翻譯作品中。傳統認為的文字語言可以通過其自身規律性而產生明晰性和確定性的結果,這一觀點由于翻譯主體的加入而變得不確定。語言意義的不確定性使得傳統翻譯標準中的“忠實”“等值”“對等”受到顛覆,后現代語境下的翻譯朝向開放性、多元性發展。然而,后現代語境下的翻譯也要遵循一些基本標準,如翻譯應符合知識的客觀性、翻譯應符合理解的合理性、翻譯應符合原文的定向性。
(一)翻譯符合知識的客觀性
戴維·米勒在他的《開放的思想和社會》一書中指出客觀的知識或思想是“完全獨立于任何人自以為是的知識,也獨立于任何人的信仰、贊成、維護或行動的意向”。從翻譯角度來看,原文文本本身就涵括了知識的客觀性,這是譯者翻譯的前提基礎。譯者與作者通常是通過文本進行交流,在兩者不同的角度下,知識的客觀性是評判翻譯的一個標準。在《天秤星座》原文本的第2章中,歷史學家布蘭奇一直從事著歷史編纂的工作,原文本對于他的工作進行了如下描述:“He is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his labor and sometimes wonders if he is becoming bodiless”,翻譯的譯文為“他這樣辛辛苦苦地干了十五年,有時甚至懷疑自己是否正在脫離自己的皮囊”。文中的上下文語境是這位歷史學家在長期艱辛地勞作中苦苦地收集,篩選史料,從而編纂出真實的歷史,但是10幾年如一日的工作使他漸感疲倦,因為譯文中的“脫離自己的皮囊”描述地很真切,符合知識的客觀性。
(二)翻譯符合理解的合理性
翻譯文本符合理解的合理性也即是譯本要遵循普遍可接受性。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要清楚地領會作者文字表達的真正意圖,達到理解與闡釋的合理性。小說《天秤星座》的譯本很好地體現了作者想要呈現的美國當時社會的政治意識形態,也彰顯了文本的政治批判意識,推進了文學的翻譯與重寫。文本中歷史學家布蘭奇的歷史撰寫史料與作者對于歷史事件的描述產生了文本間性的效果,他們都是在進行著歷史的寫作,他們也都試圖從大量的歷史文本中構建一種全新的歷史敘事。譯本整體體現了文本間的相互作用與政治文化意識,其翻譯符合理解的合理性。
(三)翻譯符合原文的定向性
翻譯應符合原文的定向性指的是文本對譯者的約束性,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的整體語言風格及表述應符合原文本的格調,原文本的框架約束著譯者翻譯的框架,從而使得譯本具有定向性。這種定向性在《天秤星座》中表現為文本與譯本整體框架的一致性。小說呈現給讀者是雙線框架,一是以地理名字命名的章節,主要描述主人公奧斯瓦爾德的一生;二是以時間日期命名的章節,闡述兩位陰謀者對歷史事件的策劃。譯本在雙線框架中符文原文的定向性。
翻譯標準是一直存在爭議的主題,翻譯既要秉承傳統翻譯標準的精髓,同時又要與時代接軌。在后現代語境下的翻譯要呈現出翻譯的多元性、開放性和自主性,同時,在翻譯過程中,譯本應符合知識的客觀性、理解的合理性和原文的定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