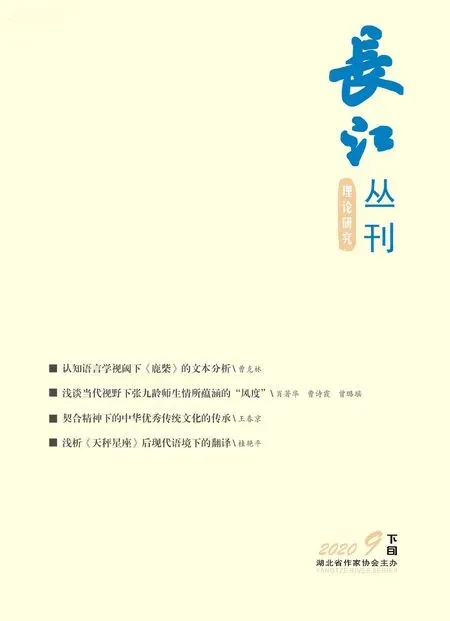當下音樂劇中民族民間音樂的重要性及具體分析
■張 敏/平頂山學院音樂學院
民族民間音樂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承載了我國各民族的文化結晶,對于民族發展有著極為深遠的意義。隨著我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逐漸提升,吸引著西方文化在我國文化市場落地,文化大融合的趨勢下如何保證我國傳統文化的地位不動搖,并在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中提供穩定的助力,值得當前每位國民的思考。以音樂劇為代表的當前我國音樂文化市場中的主流音樂表現形式,應當積極就民族民間音樂的融入采取措施,使其能夠充分發揮出我國傳統文化的優勢,滿足觀眾的精神需求,提升傳統文化的影響力。
一、當下音樂劇中民族民間音樂的重要性
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提升,民眾的生活逐漸從物質追求轉向精神追求,各類文藝表演形式在中國文化市場上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態勢來。音樂劇作為當前國民文藝娛樂活動中的一種重要舞臺表演,其能否有效的融入民族民間音樂,消除西方文化在我國社會主義價值觀體系中不適應的部分,對于國民精神世界的健康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音樂劇中融入民族民間音樂不僅能夠引進優秀的外來文化,豐富民眾的精神的生活,更能強調民族文化中的優秀部分,提升民眾的文化自信,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穩定建設。上層建筑雖由經濟基礎決定,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只有提升民眾的文化素養,培養其良好的文化情操,才能更好的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1]。綜上所述,在我國的音樂劇表演中有機的融入民族民間音樂時,通過去除糟粕,保留精華,統一西方音樂與傳統音樂的優勢,才能促進音樂劇在我國文化市場的可持續發展。音樂劇中民族民間音樂的體現,對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既是傳承,也是創新,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著積極的影響作用。
二、我國音樂劇中民族民間音樂的發展歷程
(一)傳入與初期發展
明末清初,在西方文化打開中國的國門后,音樂劇作為一種全新的舞臺表演形式傳入中國,給當時的中國傳統戲劇表演打開了新的視角。由于中國的傳統戲曲文化與西方音樂劇在表演形式、演唱內容、舞臺裝扮上都有著極大的差別,因此音樂劇并未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引起熱捧。在二十世紀初期,封建社會在西方列強的強勢攻擊下被逐步瓦解,民智得到解放,西方文化的滲入有了良好的社會環境。1927年,中國歷史上第一所高等音樂學府在上海成立,為我國專業的音樂事業發展提供了穩定助力。隨著西方音樂理論在中國社會的廣泛傳播,新潮流下的傳統民族民間音樂發展受創,為了宣揚民主科學的理念,當時的音樂界人士“一刀切”,導致音樂劇的表現形式過于西化。再加之國內局勢動蕩,百姓民不聊生,當時的音樂劇更多的為上層人士服務,因此其民族民間音樂的構成較少,缺乏一定的民族特色。
(二)穩定發展與繁榮
隨著中國取得獨立,結束百年屈辱史,中國國內環境趨于穩定,音樂文化的傳播逐漸滲透到社會各階層。此階段的音樂劇也打破了其階級性,以滿足社會大眾的精神需求為前提進入了穩定發展。在1956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時任國家主席的毛澤東為鼓勵知識分子參與到文藝工作的創作中發表了講話,對于民間藝術的發展奠定了積極的政策環境[2]。在此時期的音樂劇融入了大量的民族民間音樂,其在我國傳統戲曲的基礎上結合了民間說唱等特色音樂,廣泛吸收了各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極強烈的民族特性,誕生了如《紅色娘子軍》《洪湖赤衛隊》等優秀的音樂劇作品,極大的繁榮了我國傳統的民族民間音樂文化,滿足了大眾的精神需求,娛樂了其生產生活。
(三)停滯與復興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國文化事業再次迎來新的春天,此時期的藝術創作者重新開始了新的音樂探索,音樂劇在主流音樂潮流中逐漸擺脫“舶來品”的標簽,以民族民間音樂為重要工具開啟了文化復興之路。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改革開放的潮流下,大量西方音樂劇涌入中國文化市場,如對《吉屋出租》的改變就取得了巨大成功。與此同時,中國音樂劇開始逐漸形成中西結合的特殊風格,以音樂劇為載體注入了民族生命力,出現了《蒼原》等優秀的音樂劇作品。
三、當下音樂劇中民族民間音樂的具體分析
(一)鄉土元素
音樂劇是由樂譜、歌詞、劇本以及舞蹈、舞臺設計等多種元素構成的,戲劇表演是其最基本的體現形式之一,音樂在完整的一場音樂劇的核心,其在舞臺上的所有表演都基本要依托于歌唱才能得以表現。在當前的我國音樂劇表演中,以原創音樂劇中的鄉土因素最為豐富,民族民間音樂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民族民間音樂起源于各地域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土壤,原創的本土音樂劇更能將各族人民的真實生活展現出來,具有較強的民族特性與民族文化研究價值。善于利用鄉土元素,是在當前音樂劇表演中有效應用民族民間音樂展開表演的客觀條件之一[3]。以土家鄉村音樂劇《黃四姐》為例進行探析,這部融匯了恩施地區土家族的代表性民歌、民俗生態的音樂劇,故事以土漢兩族的青年愛情為主線展開,塑造了兩個極具時代感的新貨郎和黃四姐的人物形象。在這部音樂劇中,以民間歌曲《黃四姐》為大框架,融入了大量鄉土元素,向觀眾們展示了一個較為立體的土家生態。劇中出現的“抬工號子”“女兒會”“撒葉兒嗬”等民族民間音樂,極高的還原了真實的民族生活氛圍,提高了觀眾的觀看體驗,通過音樂向觀眾傳送了人間至美的感人情懷,具有較強的民族特性。
(二)戲劇文學
音樂劇作為從西方傳播而來的一種新型舞臺表演形式,在中國文化市場的發展過程中體現出一定的偏差性,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其劇本創作過度依賴西方歷史文化,本土化的改變不多,難以推進中國民族民間音樂在其中的應用。文藝工作者在探索音樂劇的表演過程中,意識到要賦予音樂劇新的民族活力,其劇本創作要基于我國悠久的歷史出發,通過采擷上下五千年歷史中的文學瑰寶,結合當前的社會主義價值觀進行改編,不僅有助于民族民間音樂在其中的靈活應用,更能夠極大的對傳承創新歷史文化做出貢獻。如由中國歌劇舞劇院等傳媒公司共同出品的《昭君出塞》便是改編自歷史上的真實事件,還原了漢朝時期為了安撫匈奴被選作聯姻對象的王昭君的一生。在這部音樂劇中創作者結合新時代的特性對故事內容進行了良性改編,講述了王昭君從被迫出塞到成就國家大義的傳奇一生,帶領觀眾回到了氣勢磅礴的歷史時空,對王昭君的情感形成強烈的共鳴。基于我國本土歷史文化進行劇本創作的音樂劇,使觀眾在觀看時更能有效的代入到故事情境中,對于傳統民族民間音樂的插入也極為有利,是音樂劇中國本土化的積極表現之一。
(三)聲樂演唱
聲樂演唱是音樂劇中最為重要的表演環節,劇本創作、舞美設計都是為了服務于聲樂表演,烘托表演氣氛而生的。在音樂劇中的民族民間音樂表演更具其獨特性,對于表演的歌唱手段有著較高要求,其主要演繹形勢有民族唱法、美聲唱法、通俗唱法、原生態唱法四大種,演唱者需結合實際演繹需要變化唱法,才能完美的融入到舞臺表演中,為觀眾帶來較好的視聽體驗[4]。聲樂表演的優劣直接影響到了觀眾在欣賞過程中的民族認同體驗,對于音樂劇的整體質量有著關鍵的影響力。如在宜都民族音樂劇《清江清,長江長》的表演中,其通過“再鄉土化”的手段,借鑒了歌劇詠嘆調寫法的唱段形式,打破了原生民族民歌結構的封閉性,達到了完美的聲樂表演效果。
四、結語
在當前的我國音樂劇中民族民間音樂的應用越來越普及,其不僅加快了音樂劇本土化的進程,豐富了民眾的精神生活,更對優秀的傳統文化進行了傳承創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給了有力的文化助力。在應用民族民間音樂在音樂劇中時,藝術創作者應當注重鄉土元素的融入,基于本土文化進行戲劇創作,并通過完美的聲樂表演與其他舞臺配合完成音樂劇的演出,從而加強音樂劇的民族特性,促進音樂劇在中國文化市場上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