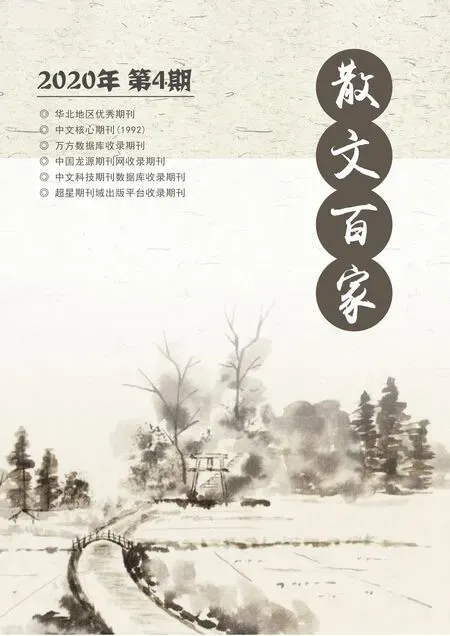淺論中國古典詩歌含蓄美的特性與實現
吳雨欣
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含蓄”是討論中國古典詩歌時需要關注的一個基本特征,也是衡量詩歌質量的重要標準。宋人張戒在其著的《歲寒堂詩話》中就點評白居易等人的樂府詩的問題并非格調、立意不高,而在于失之含蓄。由此可見,“含蓄”作為一個重要的中國詩學概念,對中國古典詩歌的鑒賞與寫作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理解“含蓄”非常重要。
中國古典詩歌對“含蓄”的追求由來已久,詩歌要“主文而譎諫”的要求,早在漢代就被提出。“含蓄”作為一種詩學概念與術語正式出現在了唐代詩僧皎然所著的《詩論》中:“氣多含蓄曰思。”在晚唐司空圖所著的《二十四詩品》中,含蓄更是被單列一品,從此“含蓄”成為一種重要的詩歌風格和詩學的審美范疇。宋代詩論中更頻繁地提及“含蓄”,并更多地將其作為一種文學批評的術語與尺度。及至明清,詩歌創作的高峰已過,學者更多地轉向對中國古典詩歌文本本身的解讀,“含蓄”受到了更大的重視,如清代詩論家葉燮在《原詩》就將“含蓄”稱為是詩的至高至妙之處。
一、含蓄美作為中國古典詩歌審美風格的特性
中國歷代詩論家們從多個側面對“含蓄”進行了解讀,“含蓄”成為了中國古典詩歌從古至今一以貫之的藝術追求與審美傳統。簡言之,“含蓄”就是把無盡的詩歌意蘊,用不直露的表達方式,在短而精悍的文本上呈現,從而實現“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
作為審美風格的“含蓄”具有如下特性。
1.詩意上的不可及性。
含蓄使得詩意延展至可言和不可言的尺度間,因此詩意既有可解的一面又有不可解的一面。可解的一面使詩歌能夠超越時間,令人們在閱讀時能夠產生共通的情感體驗,增強了詩歌普世的感染力。不可解的一面,即詩意上的不可及性,則給予讀者充分的想象自由與理解空間,讀者窮盡思考以體味作者的真意的同時更能融入自個體獨特的理解,在不斷的解讀中加強詩歌的生命力。如李商隱的《錦瑟》,其詩意至今未有定論。
2.抒情上的隱蔽性。
與外國詩歌不同,奔放、熱烈的詩句少有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出現,中國古典詩歌往往借他物隱蔽地抒發己身情感。如清代納蘭性德的《蝶戀花·辛苦最憐天上月》一詞,作者沒有直接表達對妻子深沉的懷念,而是抒寫了明月圓缺、燕子低語等場景,作者澎湃的悼亡懷人之情隱蔽在對他物的描寫中。
3.文本上的高度概括性。
中國古典詩歌要想達到含蓄的審美效果,便不能過于直白,需要擷取最具代表和特征性的事物,經歷高度的藝術概括后才能呈現在讀者面前。詩歌有限的語言空間內從而建構出富有暗示性、闡釋性與象征性的意境。高度概括后的文本呈現出的效果便是詩歌省略了具有交代、陳述、連接作用的成分,形成似斷還續的局面。
二、含蓄美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藝術實現
“含蓄”本質上是一種對詩歌“言”與“意”之間關系的探索和要求。對于創作者而言,要通過多樣化的表現手法與技巧實現“含蓄”之美。
1.情景交融。
中國詩人慣于將個人情志與自然景物融合進行抒寫,以景結情、借景抒情成為詩人常用的實現“含蓄”的手段,情景交融是意境創造的表現特征。如王安石《葛溪驛》一詩,此詩通過月、燈、蟬等意象,營造出一種孤寂、衰殘的氛圍,表現詩人深重的懷鄉之思和對國家現狀的愁苦與無奈。清代紀昀評此詩為:“意境自殊不凡。”作者能構造出不凡意境,正因為情與景完美融合,從而體現了含蓄不盡之妙。
2.比興寄托。
最早出現在《詩經》中的“比”與“興”原本是兩種藝術手法,因為其功用的相似與相關性,兩者常被放在一起談論研究。比、興手法的運用可以幫助詩文擁有可供讀者回味的余意。明代茶陵詩派的代表人物李東陽在《懷麓堂詩話》中明確指出比興具有寓托與含蓄兩個特點。比興手法顯著的含蓄性,使得它為廣大詩家所采用、推崇。
3.靈活用典。
用典也稱用事。用典不僅使語意得到了濃縮,更吸引讀者去探究典故背后的意蘊,給讀者造成豐富的暗示與聯想。如李商隱《淚》一詩,此詩圍繞詩題“淚”,前六句鋪陳用典,分述世間各種悲傷落淚之事,淚與淚之間的比較,可解作送別之淚,更可挖掘出詩人暗藏的自傷身世之意。可見用典使得詩意的表達不再直露,也為詩意的解讀提供了更多樣的可能。
三、結語
不論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還是鑒賞過程,都不可缺少對“含蓄美”的理解把握。通過多樣的技法實現了含蓄美的中國古典詩歌往往擁有悠長的藝術生命,因為含蓄而造成的多樣解讀不斷豐富著詩作的意蘊。“言不盡意”的含蓄美使得中國古典詩歌之于世界詩壇有著其獨特的魅力。在詩歌創作不再只是上層知識分子專利的今天,詩歌的娛樂性大大加強,詩歌創作更加自由,評判標準也更加多元。但含蓄憑借其獨一無二的蘊藉深邃之美,仍然可以成為我們今天詩歌創作與欣賞的審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