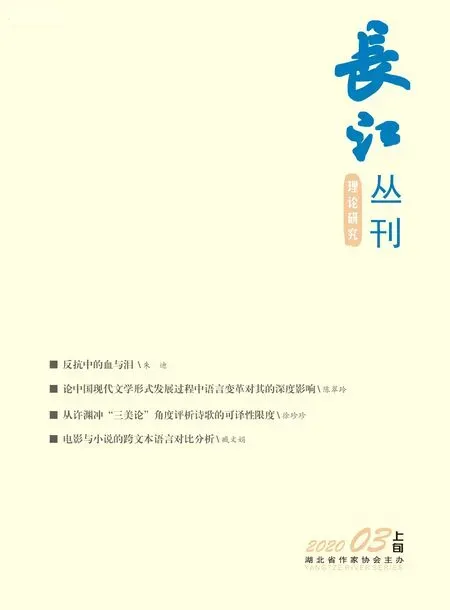曾紀鑫先生答曾紹義教授十問
■陳 羲 周 威
2014 年9 月中旬,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曾紹義教授帶著陳羲、周威兩位研究生采訪了著名作家、《廈門文藝》主編曾紀鑫先生,曾先生就散文創作中的許多重要問題作了詳盡回答,現根據采訪錄音整理成文,并經兩位曾先生過目訂正。
一、你是一個多面手,散文、小說、戲劇都有涉及而且很有影響,但要數文化歷史散文影響最大,其原因是什么?
我的創作比較廣泛,最早出版的是一本小詩集,后來小說、散文、劇本、歌詞、小品包括評論等都涉獵了,但是文化歷史散文的影響更大一點。主要原因我想是找到了一個契合點。一是與時代的契合。我1982 年開始創作,1985 年發表第一篇文章,當時雖然有人知曉,但并不怎么出名,直到1999 年才產生較大影響,我想與余秋雨出版《文化苦旅》后在社會上掀起的“文化散文熱”的時代氛圍有關,我的作品就是在這種時代環境中應運而生,進而產生一定的影響。二是我個人的因素。我是歷史系本科畢業的,中文專科畢業。我上學相當早,閱讀很雜,曾經當過老師,對教育學、心理學等都有些研究;我喜歡政治學、歷史學、宗教、哲學等,在大學時系統地閱讀了胡適和林語堂,當時西方的存在主義流行到中國,所以海格德爾和薩特的原著我都讀過,還有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杜威的實用主義等對我的影響較大。另外,我對中國傳統文化也很喜歡,看文言文沒有任何問題,可不必借助于工具書,比如《老子》《莊子》《論語》《史記》等我看的都是原著。當時讀得并不是很明了,只是喜歡,但我就是帶著這些知識積累開始寫作的,從中找到了一種契合點。與別人相比,我的優勢并不在于生活多坎坷經歷多豐富,卻是積累較多、用功頗多的人。對我的文化歷史散文創作影響最大的要數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這是知識界,包括文學界、歷史界和哲學界都要看的一本書,最早由美國出版。我當初看的時候并沒想到對我的散文創作會有助益,但它沉淀在我心靈深處,后來寫作時立馬浮現在腦海中。這本書選擇一個剖面來對縱深的歷史進行分析,然后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我的文化歷史散文也是這樣縱橫結合,選擇一個橫斷面、一個人物、一個事件,然后將其背后的動機、歷史的淵源、歷史的走向等條分縷析出來。
二、為什么要把你的散文稱為“文化歷史散文”呢?
我的散文一共有九本,加上戲劇論著的那本,我是用文化散文的形式對中國戲劇理論進行一個梳理,并與西方戲劇進行比較,所以也應該看做文化散文,那么我的散文創作其實一共是十本。要分的話,我覺得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普通散文,比如《天地過客》,主要是一些短小的散文、隨筆匯編;二類是文化散文,比如《千秋家國夢》《永遠的驛站》;第三是文化歷史散文,比如《歷史的刀鋒》《千古大變局》等,這些都是以歷史為根基,在歷史的基礎上進行文化闡釋。這三種類型呈不斷遞進態勢。我為什么要把“文化”放在“歷史”的前面呢?因為文化的概念很寬泛,范疇比歷史大,大范疇詞應該放在小范疇詞前面,而我又以歷史這門學科做支撐來寫散文,所以叫文化歷史散文。
三、你認為你的散文中最有價值的東西是什么?思想、情感、技巧還是語言?
這必須要談到對散文題材的認識,我個人不喜歡、不認同所謂“大散文”和“小散文”的區分法,因為散文在古代是很寬泛的,古代散文跟韻文相對,只要是不講究韻律和駢儷的文章都可以稱為散文。我非常贊同古代散文的這種觀點,這是一種隨意而為、形散而神不散的創作境界。另外一點,古人講究文史不分家,文學跟歷史是連在一起的。比如《史記》既是歷史記載,同時又是一部燦爛的文學作品,甚至比一般的文學作品更文學化,它的文學價值難以估量。所以在我看來,散文應追求一種想象、隨意、形散神不散的意境,這也是一種美學觀。我不在乎你寫什么,怎么寫,但最后要看你的散文有沒有美學價值,能不能具有一種超越時空的性質,引起大多數人的共鳴,這樣的散文才是好散文。我個人追求文史哲的相通,這與我自己的閱讀和興趣有關。我寫文化歷史散文,總是以歷史作題材,用哲學來觀照,通過文學的方式來描寫,形成自己的認識與思想,一句話,就是在文學、歷史、哲學這三個學科之間開掘一條通道,將它們連接在一起,這是我的文化歷史散文的最大特點。此外,文化是一個非常大的概念,所以我的散文還融合了多種學科,比如宗教、政治、軍事、經濟、心理學、教育學,等等等等,是多學科的結晶體。
四、如何處理思想與情感、內容與技巧的關系?
要把握平衡,不能成為跛足,太過于思辨了,文章就容易空洞無物;如果全是歷史的堆積,就不過一堆素材而已;如果沒有用生動的語言形象地表達出來,讀者會特別少,所以哪一個方面都不能太過也不能缺少,要在文史哲三者之間找到平衡點,把握一個度。這就要在對大量的素材進行分析的基礎上,一步一步搭建并形成自己觀點和思想,進而引導和帶動讀者接受自己的觀點,不能先入為主。另外,必須用文學的語言形象地表達出來,用優美的情感打動讀者,用啟示性的東西吸引讀者,用所寫人物的人格魅力征服讀者,這樣才能留住讀者、感染讀者。我寫文章特別講究“留白”,不把文章寫滿,給讀者意猶未盡的感覺,留下思想延伸空間,以便讓讀者將自己的人生思考融入其中,和作者一起進行思想創造。整篇文章中,這些東西也不是平均分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須有一種氣韻貫通其中,形成一種力度。如果是疲軟的,拖沓的,就不能給讀者以心靈的震撼和閱讀的愉悅。所以我特別強調作品情感的飽滿、氣韻的貫通、思想的力度,這三方面也對應著文、史、哲。另外,文章講究客觀公正,我的觀點不會明顯地流露出來,也不使用偏激的詞語,如果我贊頌或抨擊一個人,我會把自己的好惡、情緒和觀點融入文章當中,讓讀者看完后自己思考。比如在《千古大變局》中,我做的就是把人物神化、鬼化的外衣剝掉,不用概念化、臉譜化的東西,也不隨便貼標簽,任何人或事都是豐富飽滿的,沒有單一的概念化的好與壞。
五、你寫過多部長篇小說,還寫過劇本,都有好評,你寫小說和劇本對你寫好散文有什么幫助嗎?
我在進行文化歷史散文創作的時候,沒有有意識地去借鑒小說的創作手法,但會不自覺地加以應用。一旦涉及人物的對話、形象的塑造、情節的發展、細節的描寫等,就不知不覺地把小說的表現手法用進去了。特別是細節,因為很多歷史的東西離我們十分遙遠,幾百年甚至幾千年,我們知道的只是一個大概,會顯得十分模糊。但是如果你抓住了一個細節——能夠反映人物性格的細節,于是,這段歷史就會生動起來,人物形象也會鮮明起來。這是借鑒的一個方面。然后呢,小說必須有情節,才會吸引人,引導讀者一步一步往下讀,我在寫文化歷史散文的時候,盡管一些人物比如說袁世凱啊孫中山啊宋教仁啊我們已經知道他們最后是什么樣的結局了,但是你只要看我的文章,仍會不自覺地進入到我所描寫的那種氛圍里面去,他們的事跡,通過跌宕起伏的情節吸引讀者,跟著作者把人物的經歷重現一遍,也就是對這段歷史進行一個回顧,同時也會有更深刻的認識,所以我覺得小說與散文在這些方面都是相通的。除了小說對我的影響,還有劇本,我原來是編劇,戲劇對我的文化歷史散文創作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戲劇講究矛盾沖突,一下子就把要表現的所有東西集中在一起,營造一個戲劇情境,把人物放在情境里,不同性格的人物產生沖突,通過矛盾沖突展現人性,展現這段歷史。我寫的劇本主要是話劇,我認為話劇是所有體裁里最難寫的。為什么這樣說呢?話劇沒有什么敘述與描寫,主要通過對話把所有的東西表現出來,包括人物的行動、情節的推進、形象的塑造、細節的表現等。一般來講,話劇里面連注釋都很少,所以對編劇的要求相當之高,對話必須凝練,每一句話都是有用的,沒有一句廢話。并且戲劇還十分講究一些道具啊美術布景之類的運用,比如說大幕一拉開,觀眾會看到舞臺上的一些道具,墻上掛著一幅畫,或者一個包,這都不是隨便掛的,會起作用的。隨著情節的推進,這個包會背走,畫里面會藏著什么東西,每個道具的布置都有它的用途與意義。由此來看我的文化歷史散文,雖然每篇寫得很長,一兩萬字的篇幅,并不是有意為之,但是我盡可能地不寫一句多話。我截取一段歷史,抓住關鍵性的轉折事件以及最能反映人物命運的事件來寫,盡量要言不煩,但稍微一展開,就那么長了。當然,我是盡量在壓縮,如果洋洋灑灑寫下來的話,一個人物的參考資料有時多達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字,我提煉、濃縮、發酵、轉化之后,最后成為一篇一兩萬字的散文。另外,我對音樂比較愛好,常聽交響樂、搖滾樂、民樂以及流行歌曲;還有美術,早年畫過廣告畫,喜歡閱讀美術理論方面的雜志、書籍,會從中借鑒吸取營養。我一直在文化系統工作,與劇團打交道比較多,所以對表演藝術比較了解,經常參與大型文藝晚會的策劃與撰稿,這些都會不知不覺地運用到我的文化歷史散文創作之中。也就是說,表面看起來相當單一的文化歷史散文,事實上把我很多知識儲備、藝術積累、美學認識都融匯進去了。
六、你認為散文能虛構嗎?
我認為散文是不能虛構的,真實是散文的靈魂。有的人覺得可以虛構,我想大部分人認為散文是不能虛構的,寫的人物、感情這些都應該是真實的。我有一個朋友也是同學,十多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叫《父親》,發表在一家著名雜志上,結局是他的父親去世了。當時我就很奇怪地問他,你父親去世了我怎么不知道?他說父親還健在,而且那篇文章里好多內容都是虛構的。于是我就和他產生了一些分歧,說散文不能這樣寫,《父親》雖然寫得好,藝術質量較高,但你的創作理念我不認同。這是個很特殊的例子。我寫散文是不會去虛構的,我尊重三種真實:一是歷史的真實,二是現實的真實,三是藝術的真實。譬如我寫李鴻章,就用各種史實把人物放到當時的背景及舞臺,還原歷史的真相,讓讀者去分析去判斷,李鴻章到底是不是漢奸賣國賊。一件事實遇到幾種不同的說法,我會進行理性的分析,盡可能地接近并還原真相。像《岳陽樓記》,范仲淹雖然沒有到過洞庭湖,但他在畫作中欣賞過;并詢問來自當地的士兵,了解到的東西、掌握的資料,比那些去過岳陽樓的人更多;同時他融入了自己的家國情懷。于是,范仲淹寫出的《岳陽樓記》并非虛構,而是一種藝術的真實。
七、你寫兩種題材,就是歷史題材和現實題材,寫哪一種比較容易?
對我來說應該都差不多,但著力點不一樣,所花功夫的程度也不一樣。比如寫古代,我一般搜集大量資料,認真閱讀、感悟,只要有條件,會做田野調查。我寫歷史人物,幾乎每一個都要去他們的故鄉及生活、從政甚至游歷的地方,搜集了解相關資料,這個工作開展起來其實比較辛苦。比如寫清代理學名臣李光地,在福建安溪縣感德鎮參加一個筆會后返回廈門,當地派車送我到安溪汽車站,乘便先去參觀李光地故居,然后前往他的墓地。李光地墓位于一座山上,司機繞了一個大圈,終于找到一條山路爬了上去,當時正在修路,新土十分明顯。幾天前下了一場大雨,天剛放晴,路面坑坑洼洼尚有積水。走著走著,右邊泥濘難行,司機方向盤便朝左邊一打。左邊是懸崖,路面的新土被雨水浸泡之后突然往下陷,司機緊急剎車,臉色都嚇白了。我當時也有點懵了,若不是親身經歷,真不知道當時的情形有多么危險,車身傾斜,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設想。于是我們趕緊下車。司機在周邊找來一些石塊、土塊墊在輪胎下,一陣忙碌后再慢慢啟動,終于小心翼翼地回到了堅硬的路面……對此,我在《理學名相李光地》一文中寫道:“也許是歷經喧囂、倦于官場,看淡紅塵的李光地,不愿他人打攪他的清靜與安寧吧?”再如寫抗倭英雄俞大猷,在泉州友人的帶領下前往他的墓地,也很難找,花了大半天時間終于如愿。
文字資料與田野考察相結合,是創作歷史題材的基本要素。寫現代題材的話,文字資料可能比較匱乏,但我們是親歷者,對人與事有著切身的體會,便以親身感受為主,文字資料為輔。歷史題材、現實題材,側重點不同,但著眼點都一樣。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研究歷史、重寫歷史需以當下的視角進行透視與反思,其實也是為了現實與未來。創作題材沒有優劣之分,文學體裁也是如此,不是說寫詩歌就完全可以超然物外,小說就可無邊無際地虛構,,散文就可性之所至天馬行空了,體裁也無優劣之分,只要寫得好,藝術價值都一樣。所有的題材和體裁,都不過是載體。但是每一個作者都有他的特長,有人擅長寫小說,有人喜歡寫散文,有人對詩歌情有獨鐘,不僅強求不了,也是學不來的,得根據自身條件、喜好等發揮特長,向讀者展示最為“拿手”的一面。那么我呢,各種都會寫一點,就像您說的是個多面手,但我現在的“戰線”有所收縮,主要寫長篇小說、文化歷史散文和戲劇。
同時,搞創作非得有激情不可,沒有激情的推動,是寫不下去更寫不出好作品來的。但是創作久了,往往會產生寫作的疲勞感。《千古大變局》寫完之后,我一個月不想看書,兩個月不想寫任何東西,有一種吃膩了食物的“惡心感”。遇到這種情況,我就自我調節,變換一下寫作頻道,激發創作活力。比如我寫完散文之后,會換著寫一下小說,就有了新鮮感,于是激情又來了。因此,我的創作,就是通過不斷更換題材與體裁,產生新鮮、熱情與活力。我的每一部作品,構思時間會很長,幾年甚至十多年,反復琢磨。而一旦構思成熟,創作起來,往往一氣呵成,平均每天可寫一萬字左右。
八、文化歷史散文要寫出來極容易變得枯燥,成為史料堆積。你是如何看待散文美的?
對散文方面的美學追求,我做了一個梳理,可歸納為八點:
第一個首先是語言。語言是最重要的,語言不優美,語言不過關,其他免談。
第二個是細節。因為散文往往會忽略細節,但細節最能反映事物的本質,細節最為鮮活,這也是小說方法的一種嫁接。
第三點就是獨特性。我的散文,要有獨特的屬于我的“曾氏風格”才行。
第四點是激情與理性、歷史與現實、主觀與客觀的結合與融匯。寫作的時候要有激情,但不能讓激情泛濫,泛濫之后就會沒有尺度,從而失去理性,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寫歷史,必須用現實的視角加以觀照,剛才我已經說過。再一個就是主觀與客觀的關系,題材是客觀的,“我”是主觀的,創作必然會打上“我”的主觀烙印。
第五點就是寫散文的留白。留下一定的空間,讓讀者參與其中,一同感悟,一起創造,可以把某些本質性的東西延伸傳遞下去。所謂“留白”,那個白不是無,而是一個空間,有縱深感,同時留白也是尊重讀者,促使他們開動腦筋認真思考。
第六點,講求思想性。我們的散文常常沒有思想性,但是我認為必須要有,一篇文章沒有思想就立不起來。有思想,你的文章才會有內涵,才會深邃。并且思想要有邏輯性,哪怕隨意跳躍時,要有那種內在的西方的邏各斯。
第七是意境。要把讀者帶入你營造的境界里面,有了意境,文章才有文化味道。
第八點,要追求雅俗共賞。散文不是學術論文,既要通俗易懂,又要高雅上檔次,下里巴人與陽春白雪兼而有之。
九、你是如何把荊楚文化融匯到閩南文化之中去的?
答:2003 年我剛來廈門時,廈門日報社記者年月對我進行了一次采訪,談到近海文化決定廈門性格。一晃十多年過去,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所謂的荊楚文化、閩南文化,是從區域文化的角度進行分類,強調地域的獨特性,這都是理論方面的。只有深入到每一地域文化的內里,對這種文化有一種切膚之感后,才能知道不同區域間的文化差異有多大。當然,完全融入其中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基本融入。此前,我身上攜帶的是荊楚文化、中原文化的因子,來廈門后,這個城市不排外,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很快就習慣了,融入到這座城市之中了。廈門城市的歷史,決定了它的包容性。廈門的發展,第一次是鄭成功時期,鄭成功將廈門作為“反清復明”的大本營,建立政治軍事機構,大力著手廈門的經貿開發與建設;第二次是鴉片戰爭之后成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西方文明大量涌入;第三次發展,是當代的改革開放,廈門成為經濟特區。歷經這三次大的文明融合之后,廈門容納百川,因此我一點也不感到隔膜。但是內里的細微區別還是非常明顯的,區域文化的特色,常在一些代表人物身上體現出來。比如荊楚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屈原,他忠心報國,具有浪漫主義傾向。人們常說“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我對九頭鳥的理解,就是多元化,九個頭互相協調,形成一種契約和協商機制,我覺得這是最早的民主因子;同時也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現,想想看,剁掉一個頭,還有八個頭活著呢!閩南文化是多元文化的融合,閩南人大多不是本地人,最早從河南遷來。閩南文化是移民所帶來的中原文化,與本土閩越文化和外來西方文化交融的產物。廈門屬于閩南文化圈,海洋文化的影響格外明顯,但又不是真正的海洋文化,而是靠海、臨海、瀕海,我把它稱為“近海文化”。我認為中國是沒有海洋文化的。其實,我是不可能百分之百融入閩南文化之中的。比如閩南話,剛來時學了幾個月就學不下去了,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會說閩南話,而且只聽得懂一點點。再如廈門人的性格,溫溫的,綿綿的,不急不躁,這與湖北人也不一樣。還有,廈門人從來不會邀請你到他家去做客。我分析這種原因,他們當時移民過來,一無所有,每占據一塊地盤,都會有非常殘酷的斗爭。你一個外來人,是否前來窺探我的領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家園意識,拒斥外人,不讓你踏入我的地盤。這些,都是我慢慢感受、體會出來的,這就是文化的差異。我寫閩南歷史人物,第一個是李贄,泉州人,致仕后在湖北紅安、麻城隱居過,他是傳統文化的一個異數,我把它稱為“另類思想家”。人們常說“落葉歸根”,可他就是不愿老死故里!再一個,他六十多歲才出版第一部作品《初潭集》,以后一發而不可收,七十多歲了還表現出旺盛的創作激情與極強的生命活力,同時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叛逆性,這種叛逆,你可以看作率性,也可以視作胡鬧。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年人,怎么總是忌諱回家呢?以前我不明白,到廈門后就理解了。他的故鄉泉州是朱熹的首宦之地,尊孔復古的理學氣息十分濃厚,而李贄是反對拿孔子作標簽的,回來之后會受到各種束縛,于是他索性不回。他身上的叛逆性也是淵源有自,閩南人多為移民后裔,作為弱者,他們不斷逃亡,不斷南遷,但心底永不服氣,骨子里有著一種反叛的精神,喜歡打拼,免不了下意識地胡鬧幾下。而且自我邊緣化,不斷放逐自己,一直往南走,渡海臺灣,闖蕩南洋,乃至向全球各地發展……作為一個外來人,我會不斷地比較,有些東西一比較,差異性就出來了,這種差異性就是個性與獨特性,對創作會大有裨益。而日常生活之中,有些東西你改變不了,又要與它長期相處,有時就不得不去遷就它、適應它,我想這就是所謂的“融合”吧!
十、你今后的創作有哪些打算?
答:正要寫的是長篇歷史人物傳記《大明雄風· 俞大猷傳》,然后是關于現當代歷史的創作,以關鍵性人物為載體,描述、剖析、反思中國政治、文化、宗教、軍事、經濟的方方面面,已經寫了古代的《歷史的刀鋒》、近代的《千古大變局》,那么再寫一部現當代的,就可構成中國史系列三部曲。可能的話,我還想寫一部關于世界歷史、文化的描述與反思性作品,探討人類文明的發展與演變。然后就是太平天國,這些年一直在實地探訪相關遺跡,搜集閱讀這方面的資料,構思一旦成熟,就會以文化歷史散文的形式好好寫一寫。衡量一個國家、民族最高文學水準的是長篇小說,因此,我還想好好寫一部長篇小說,能夠立得起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最后的落腳點,我將超越這些具體的題材,探討與人類命運、星球宇宙相關的內容,寫一些哲學性、本質性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