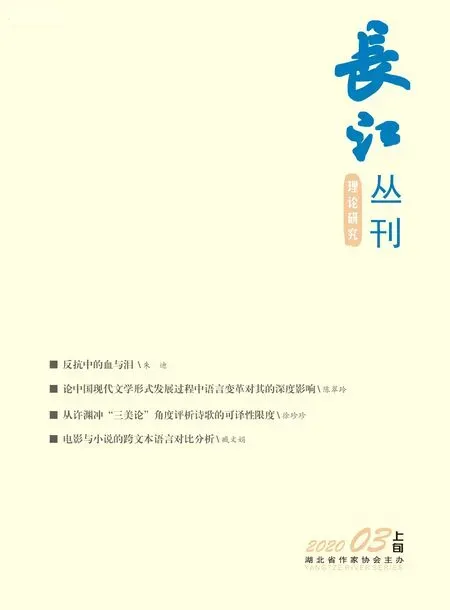網絡語境下城鄉公共文化服務一體化的法治路徑
■宋 凡 宋 凱/.湖南工商大學;.石堰河中學
一、網絡語境下公共文化服務城鄉二元結構失衡態勢嚴峻
城鄉差距不可避免,只能縮小。這種不均衡現象產生根源具有社會性、歷史性與自然性。有學者提出新中國成立后,社會發展模式有著濃郁的強國家主義色彩,城鄉二元結構成為這一政治哲學與發展模式的衍生品。從歷史維度來看,任何朝代都會設立首都,不同地區發展程度不同,同一地區也會出現農村與城市,城鄉差距問題從古至今一直都存在,僅在程度有所不同。因此,將城鄉二元結構歸于社會發展模式的衍生品并不準確,但不可否認的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發展模式確實加大了城鄉發展的差距。
改革開放初期,文化建設受制于經濟發展,尤其在投資、政策導向與現代化建設布局等方面略顯不足,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發展一直處于邊緣化狀態。進入21 世紀以來,我國互聯網發展迅猛,由工業社會迅速轉型為信息社會,根據2018 年7 月公布的第42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來看,我國網民規模為8.02 億,農村網民規模為2.11 億,占整體網民的26.3%,城鎮網民規模為5.91 億,占比達73.7%。另外,經過20 多年的城鎮化建設我國城鎮化率已達58.5%①,根據《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 年至2030 年)》的預期規劃,到2030 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70%,而我國目前約有六億農村人口,即使到2030 年仍有四億多農村人口。不可否認,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鎮是一種大的趨勢,但是這樣數據分布也反映了另一個問題,即農村網絡普及性不夠。這種現象的原因顯而易見,農村人口結構分布主要是老人和留守兒童,一方面囿于經濟狀況,另一方面在接觸學習新事物能力上也遠不如青壯年,自然會導致網絡規模少于城鎮網民。
相較于傳統公共文化服務,網絡中的文化服務產品更具有優越性。首先,網絡中的文化服務相較于傳統公共文化服務更具有經濟性。據調查,甘肅省蘭州市大量居民月文化產品消費低于30 元,89.4%的居民參加文化活動不積極。在網絡中僅需要花費極少量的錢甚至不用花錢就可以獲取有大量圖書、報刊、音樂、藝術作品等文化產品,而傳統的紙質書籍價格一般都在幾十至幾百元不等,在選擇公共文化服務時,因此,在居民本來就不愿積極參加文化活動的情況下,在獲取公共文化的產品時經濟性自然是首要考慮的問題,基于經濟利益最大化,自然會選擇網絡中的文化服務。其次,網絡中的文化服務更具有便利性。網絡中文化服務便利性主要體現在獲取、攜帶、運輸傳送等方面,在對某一方面的文化感興趣時,在互聯網上進行搜索即可獲取大量信息,通過篩選之后便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資料,極大地提高了閱讀效率與閱讀質量,并且電子數據攜帶、運輸、傳送便捷。第三,網絡中的文化服務更具有時效性。所謂文化服務的時效性是指在網絡中獲取的文化服務產品都是最新的,不會因為出版、印刷或者其他繁瑣的程序導致獲取到的信息與社會發展不對稱等問題。
二、基于網絡時代下城鄉公共文化服務二元結構失衡嚴重問題的反思
(一)治理網絡中公共文化服務的制度依據層次有待完善
我國對于傳統的公共文化服務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設相對比較完善。近年來,我國相繼出臺了《電影產業促進法》、《公共圖書館法》、《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等多部專門調整公共文化的法律,打破了傳統的公共文化治理依靠部門規章或者“紅頭文件”的局面,表明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治理開始逐漸步入法治軌道。另外,在城鄉二元失衡問題上,也開始予以重視,《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進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的指導意見》(2015 年)、《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2017 年)以及2018 年發布的《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計劃(2018—2022 年)》中第七篇第二十四章都明確規定了對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相應的制度,②表明傳統公共文化服務法律制度的“四梁八棟”已初步建立,相應的規章制度也開始逐漸完善。
(二)相關部門在網絡時代中的公共文化服務中定位不準
網絡給公共文化服務帶來了巨大的改變,網絡中的公共文化服務在服務理念、服務內容、服務方式等各方面與傳統服務方式都不同。在服務理念上,傳統模式下公共文化服務提供側重點在于管理與服務,也就是說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時候公民很難拒絕,圖書館、體育館、文化館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由相關部門投資并實行,而在網絡時代,大量的電子圖書數據庫取代了傳統圖書,公民在選擇閱讀問題上可以依靠相關部門提供的圖書館的資料,也可以在網上找相關資源,在服務內容上,數字化公共文化服務于傳統的公共文化服務差異巨大,數字化公共文化服務最大的特點是虛擬,也就是無法接觸到實體,而文化權本身便是精神層面的權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網絡中的公共文化服務更契合文化權的本質屬性。在服務方式上,網絡中的公共文化服務最大的特點就是迅捷,獲取和攜帶都優于傳統公共文化。因此不能將傳統的主導服務模式照搬應用到網絡語境下的公共文化服務管理之中,而對網絡中的公共文化服務實行強管理制的模式。
(三)網絡時代下農村公民的公共文化服務權利保障不足
我國對于基本救濟采取雙軌制,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抽象審查和司法機關以訴訟的形式進行保障,但是這種救濟機制很難切實保障基本權利,抽象審查主要針對法律法規以及地方性法規會不會存在違憲或者上下位階沖突問題,而制度規定能否落到實處很難進行監管。司法救濟作為權利救濟的最后一道屏障,對于公民的文化權利也無法保障,公民不能直接依據憲法請求國家履行保障文化權的義務,出現了文化權利被侵犯的情形,司法救濟的缺位極易導致權利意識的淡化。另外,公民自身維權意識不強進一步惡化了公共文化服務法治的環境土壤,在經濟相對不發達的農村對于文化權利意識就更為淡薄,特別是留守兒童與孤寡老人,文化權作為基本的權利他們應該享有,但實際上大多農村的居民對于文化權是沒有很清晰的概念的。
三、網絡語境下城鄉公共文化服務一體化的法治路徑選擇
(一)完善網絡中的公共文化服務法律保障體系
當前網絡中公共文化服務保障的需要依照法律進行制定相應政策法規,保證在文化治理上既有宏觀的法律制度,又有具體的政策法規。全面依法治國強調在各個領域依照法律規定進行治理,對于網絡中的公共文化服務保障制度依據更多的散見于政策法規,這政策法規靈活性高,能夠在出現問題時及時止損,但是依照政策法規治理公共文化服務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法律是站在全局視野下展開治理,而政策法規主要針對公共文化服務中出現的某一個或者某一類現象進行規制,容易出現掛一漏萬的現象,會產生很多空白地帶的規制不能,并且政策法規的權威性不足、穩定性不夠必須有相應法律作為依托。
(二)相關部門在網絡語境下的公共文化服務角色的再定位
一方面,網絡時代并不是以傳統提供物質化公共服務為主,許多企業和社會組織在網絡資源上具有很大的優勢和發展空間,在網絡語境下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過程中,作為主導者應當鼓勵個人、企業、社會組織參與,并未其創造條件,過于強勢干涉反而會阻礙這些社會組織以及企業的發展,不利于多元化公共文化服務提供發展。
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務響應權利屬于文化權,本質上是精神層面的權利,對于精神層面的權利應當予以更多的選擇空間,介入公共文化服務的提供過程中本身便具有強權色彩,在公共文化 產品的供給問題上,長官意志長期占主導地位,導致公共文化服務的政策制定,資金、人員的投入,相關項目的監督均缺乏公眾廣泛且有效的參與,進而出現公共文化產品供給與民眾需求脫節的現象。
(三)加大農村網絡中的公共文化服務權利保障力度
對于農村網絡中的公共文化服務權利保障力度加強應當從相關部門和公民自己兩方面著手。一方面,相關部門保障層面需要進一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應當確保是有效的供應,公共文化服務權利的行使必須要有相應的基礎設施,并且這些基礎設施能夠滿足農村公民對公共文化的需求欲望,農村公民希望相關部門提供文化培訓活動、體育與才藝比賽、放電影等基礎設施活動,但這些基礎設施的資金、人才投入都低于對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網點、文化大院、農家書屋等方面。相關部門不能依據其自己的目的判斷公民文化需要什么,應當深入調研,在明確農村公民的現實需求的基礎上加強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確保網絡語境下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與農村公民的現實需求不存在脫節的情況。
另一方面,農村公民應當明確自己在網絡中也有公共文化服務的權利,并且能夠主張權利。這就需要培養農村公民在網絡社會中公共文化服務的權利意識,權利根據性質課分為積極權利與消極權利,文化權從性質上來界定應當屬于精神自由領域的權利,屬于消極權利。消極權利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容易被遺忘,在網絡興起的時代,公民忙著體驗網絡帶給自己生活的改變,而忽略了自己在網絡中擁有公共文化服務方面的權利,特別是在權利意識淡薄且網絡不發達的農村,對于網絡中的公共文化服務權利遺忘更加嚴重。因此,需要培養農村公民在網絡中的公共文化服務權利意識就顯得十分必要,在具體操作中可以通過相關部門宣傳、社會組織宣傳以及網絡、廣播等形式強調公共文化服務的權利,進而喚醒農村公民在網絡時代的這種權利意識。
注釋:
①第42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R].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2018.
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R].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