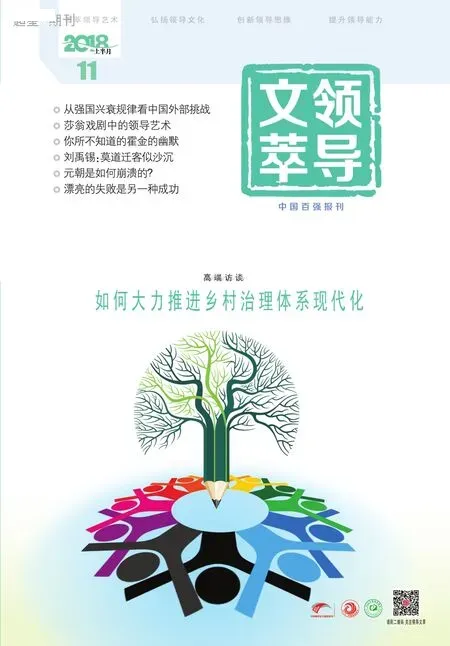田文鏡:從賑災(zāi)救民到匿災(zāi)誤民
林乾
在雍正皇帝的眼中,田文鏡是“巡撫第一人”。雍正甚至提出,如果地方的封疆大吏,都像田文鏡和鄂爾泰那樣,則天下“允稱大治矣”。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田文鏡是執(zhí)行雍正一系列革除積弊政策最徹底的人。但說起田文鏡的仕途經(jīng)歷,堪稱“出奇”。而最令人唏噓的是,他得到雍正重用,是因揭發(fā)山西匿災(zāi)不報,而他最后失信于雍正和河南地方百姓的,竟然也是匿災(zāi)不報。
(一)
田文鏡是漢軍旗人,康熙元年出生,22歲正式走上仕途,經(jīng)過40年為官,在康熙朝做的最高官位,還是一個從四品的中層官員。升遷的路,慢得“出奇”。
如果沒有什么“意外”,到雍正即位時,年過花甲的田文鏡,已經(jīng)準(zhǔn)備收拾行囊,告老還鄉(xiāng)了。但他的仕途生涯卻因一次再平常不過的差事而完全改變。
按照慣例,新君即位要告祭山陵。田文鏡前往告祭的是西岳華山。正是這一次告祭,給他的仕途帶來“四級跳”。因為他向雍正講真話,揭露山西匿災(zāi)不報,而且還征比錢糧。
雍正元年,是啟用雍正年號的第一年。北方出現(xiàn)了少有的旱災(zāi)。雍正對此非常關(guān)注。自康熙后期,清朝就有“雨雪糧價”的奏報制度,而對災(zāi)害的奏報制度要更早。山西巡撫德音接二連三奏報山西雨雪充足。他在正月奏報說,山西普降大雪一尺多厚,百姓都說:許多年沒有見過這樣的大雪,全省麥子必獲豐收。
如果放在平時,地方官報喜不報憂,也習(xí)以為常。但這是雍正改元的第一年,更何況,這是人命關(guān)天的事。
田文鏡告祭華山回京,已是四月十四日的事情了。雍正向他詢問沿途經(jīng)過地方的情形。田文鏡一直搖頭,回奏說:山西平定州、壽陽縣、徐溝縣、祁縣等處,雨澤歉少,民間生計維艱,汾州府屬地方,得雨亦未沾足。而地方官現(xiàn)在仍然在征比錢糧。所謂征比錢糧,是采取強(qiáng)制手段,把沒有繳納錢糧的納糧戶,關(guān)押在衙門里,由吏胥逼迫繳足錢糧后才放人。此舉最易引起民變。
雍正感到事態(tài)嚴(yán)重,立即召集總理事務(wù)王大臣,采取斷然措施,予以賑濟(jì)。他說:巡撫以撫綏地方、愛養(yǎng)百姓為職。今山西并未奏請賑濟(jì)緩征,反行催科,小民何以存濟(jì)?這都是因為巡撫德音去年曾奏報得雨,現(xiàn)在想掩飾以前所奏。當(dāng)即命田文鏡會同巡撫德音,率領(lǐng)地方官員速行賑濟(jì)。
田文鏡到了省城太原,巡撫德音卻以主持考試為由,拒不見田文鏡。因此山西賑災(zāi)事實上由田文鏡主持。他立即行文給平定州等四州縣,讓他們趕造花名冊,登記賑災(zāi)人戶。經(jīng)過一個月的緊張工作,四個州縣共有大小男婦13萬人得到賑濟(jì),發(fā)放賑濟(jì)糧一萬石有余,賑濟(jì)銀一萬多兩。
田文鏡的擔(dān)當(dāng)有為和精細(xì)高效,得到了雍正的極大肯定。雍正隨即把德音解職,山西巡撫由內(nèi)閣學(xué)士諾敏補(bǔ)授;布政使森圖革退。
通過山西賑災(zāi),雍正開始考慮對田文鏡這位敢講真話、能做實事的從四品官員委以重任。雍正最初的考慮是在朝中提拔。但山西的災(zāi)情遠(yuǎn)遠(yuǎn)超出最初的估計,也不是最初的四個州縣,而是蔓延到全省大部分地區(qū)。這樣,諾敏在四個州縣沒有賑災(zāi)完成前,就向雍正奏請,把田文鏡留在山西,繼續(xù)賑災(zāi)。雍正卻有另一層考慮,即由田文鏡接任山西布政使。他在諾敏的密奏上朱批:田文鏡到后,朕將擢用于京城顯要之缺。田文鏡人若何?心地品行若何?當(dāng)雍正接到諾敏有關(guān)田文鏡“人勤勉,辦事亦可”的肯定后,立即命田文鏡署理山西布政使,并對諾敏說:田文鏡將本年山西之事奏后,朕方知拯救了五六十萬生靈,想必山西百姓必很感激他。
至此,田文鏡到山西賑災(zāi)4個月后,由從四品的侍讀學(xué)士一躍而成為二品的省級大員。賑災(zāi)完成后,田文鏡正式出任河南布政使。9個月后,出任河南巡撫,成為開府一方的封疆大吏。對于田文鏡的急速升遷,《清史稿》解讀說:雍正嘉其直言無隱,令往山西賑平定等諸州縣,即命署山西布政使。文鏡故有吏才,清厘積牘,剔除宿弊,吏治為一新。自是遂受世宗眷遇。
(二)
田文鏡仕途發(fā)跡,是因為直言山西匿災(zāi)不報。然而可悲的是,田文鏡晚年逐漸昏聵,喪失了官德與操守,沒有善始善終,他失信于雍正與河南百姓的,竟然也是匿災(zāi)不報。而且,田文鏡匿災(zāi)時間很長,涉及范圍很廣,成為他一生為官難以洗脫的污點。
田文鏡擔(dān)任河南巡撫后,雍正就不時給他敲警鐘,提醒他,“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當(dāng)日圣祖時曾有諭:‘督撫初用,各各多有好的,日久年多就變了。此圣祖經(jīng)歷之確論。人能不改變、不忘初志就好了。朕亦以此自勉。”
雍正八年,河南災(zāi)情嚴(yán)重,雍正從其他渠道獲知災(zāi)情,并已下令免征受災(zāi)州縣的錢糧。但田文鏡不但拒絕賑災(zāi),而且嚴(yán)征錢糧,到九月已經(jīng)征齊,致使百姓背井離鄉(xiāng),出省乞討。雍正帝為此質(zhì)問田文鏡:山東災(zāi)民流亡他省,尚屬意料之中。麻城等地也有河南省饑民就食,此系何故,朕殊不解。河南從前未聞荒歉如此之甚,為什么拋棄鄉(xiāng)井、紛紛到鄰省乞討?他還不厭其煩地說:豐收歉收,都是常有的事,豈能保證年年風(fēng)調(diào)雨順?“若令屬員隱飾捏成,不但不能免物論,亦無趣無恥事也。”田文鏡回奏說他“汗流浹背,悚惶惕懼”。但還是報雨雪充足,豐收大有。
檔案顯示,田文鏡以河南山東總督身份,于雍正九年四五月密奏,河南“二麥豐登,家給人足”,十月又報豐收后,瑞雪紛飛,二麥皆已下種,長勢茂盛。又報山東豐收,雨雪充足。密奏還有“此皆圣天子挽回造化,天人感應(yīng),捷于影響”。
但田文鏡匿災(zāi)不報,致使河南、山東百姓流離失所的做法,已激起公憤,參奏他的密折一個接一個。雍正最初考慮田文鏡畢竟是有功之臣,說他多年來把河南治理得非常好,豈能因為一件疏忽,就否定他一直以來的善績。仍給田文鏡以自我糾正的機(jī)會。
到了雍正九年二月,災(zāi)情蔓延,越來越嚴(yán)重,許多州縣出現(xiàn)搶劫富戶、社會失序的情況;賣兒賣女者,更是比比皆是。田文鏡下令嚴(yán)禁買賣。雍正得知后,非常憤怒,認(rèn)為在災(zāi)荒之年,匿災(zāi)不報的行為無異于把人往死亡里推。
山東的災(zāi)情也不比河南好。有人奏報說,山東去年水災(zāi),收成僅三四分,而地方官竟然以收成七八分捏報無災(zāi);又迎合上司之意,將饑民戶口駁減;遇外來乞討的人,一概驅(qū)逐,而本地饑民又?jǐn)r阻不許他往。
河南的災(zāi)情遠(yuǎn)比雍正元年的山西嚴(yán)重。赴河南賑災(zāi)的欽差大臣王國棟奏報說:目擊饑民或挖掘草根,或采摘野菜,情殊堪憫。受災(zāi)達(dá)三十余州縣。自三月初七日起賑濟(jì),每月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給發(fā)兩月,接至麥?zhǔn)铡佑脗}谷多達(dá)五十余萬石。如此平均折算,賑濟(jì)災(zāi)民達(dá)到250萬口。雍正十年十一月,田文鏡因久病未痊,解任調(diào)理。不久病逝。謚“端肅”。
(三)
田文鏡是雍正朝“模范三督撫”中最早受到雍正重用的大臣,但他晚年匿災(zāi)不報,不但成為其50年為官生涯的最大污點,也是乾隆帝用以警示官員的典型人物。
乾隆即位后,明詔罪其匿災(zāi)不報,其中有“幸伊早死,得全首領(lǐng)”的話。他痛心地說:河南地方,自田文鏡為巡撫總督以來,苛刻搜求,以嚴(yán)厲相尚,而屬員又復(fù)承其意指,剝削成風(fēng),豫民重受其困,即如前年匿災(zāi)不報,百姓流離失所。他為此發(fā)布《督撫實心愛民諭》,提出“為治之道,莫切于愛民。督撫能知愛民之為稱職,始不負(fù)朕委任之心。”就河南一省論之,田文鏡匿報災(zāi)荒于前,王士俊浮報墾田于后,小民其何以堪。各省督撫大吏,必須以實心行實政,董率屬僚,以為民勸,方能奠定惇大成裕之治。
(摘自《學(xué)習(xí)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