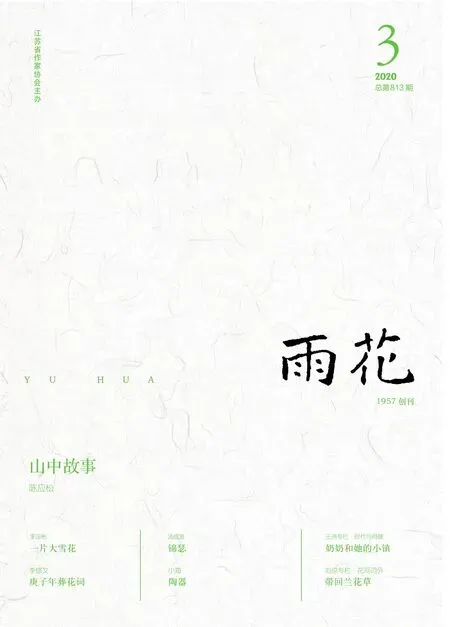奶奶和她的小鎮
王 堯
奶奶坐著花轎從女廟巷到兩千米之外的爺爺家。我不知道奶奶當年是什么發型,在我的印象中,奶奶的頭發從來都一絲不茍,梳著一個髻。奶奶出嫁一定是大排場,隨她去爺爺家的還有一個丫鬟。我后來在電影和電視里看到這樣的場景,就想到我奶奶。大陸演員扮演大戶人家的祖母無論神形常常不及臺灣的一些演員,這可能與家庭背景有關。我在鎮上讀高中時,走過無數遍奶奶坐花轎的這條路,偶爾也有奶奶同輩的人喊住我說:你是聞二小姐的孫子?我是聞二小姐的孫子。在爺爺家那條巷子,有人會指著我說:這是二少爺的孫子。我爺爺排行老二。
我讀初中時,奶奶的媽媽,我爸爸的外婆,我的婆太太還健在。我偶爾跟奶奶去鎮上看她,她會從袖子里掏出一毛錢,讓我肚子餓了去買燒餅。我一直記得婆太太的眼神,沒有奶奶的眼神那樣自信,她的臉上留下了從繁華到衰敗的痕跡。蒼老的婆太太活到近九十歲,在我有限的接觸中,我從未聽她說過聞家當年的境況。她不叫我的名字,見到我會說崢鴻的兒子來了。崢鴻是我爸爸的名字。如果我的舅爹、舅奶奶在家,我進門以后,依次恭敬地稱婆太太、舅爹、舅奶奶。舅爹和舅奶奶都是老師,舅爹教中學語文,舅奶奶教小學算數。舅爹是我在青少年時期見到的讀書最多的人。舅爹知道我喜歡讀書,但我們兩人無法交流。舅爹背《古文觀止》,我讀小說,偷偷看了《野火春風斗古城》《三家巷》和《紅旗譜》等。我在客廳站著,舅爹、舅奶奶和我的談話像老師給學生上課一樣。
在婆太太家的大客廳里,我特別緊張,周遭所有的物件都散發著我在《苦菜花》《家》中讀到的那些大戶人家的氣息。后來知道成語“如芒在背”,我就想到我在婆太太家客廳的感覺。其實,我非常尊敬我的舅爹和舅奶奶。我隨奶奶出門后,奶奶會說:他們就是講斯文。奶奶和她弟弟長得很像,關系可能一般,我從來沒有看到他們姐弟親近過。舅爹在一個大隊小學教書時,我們家修房子,爸爸寫了一封信讓我去舅爹那里借錢。舅爹留我吃午餐,扁豆燒肉。飯后舅爹寫了一封信讓我帶回,沒有提錢的事。我在路上急切打開信封,信里有“入不敷出”四個字。我一直記得舅爹的午餐,在那樣的日子里,舅爹留我吃午餐而且有紅燒肉,已經是深情厚誼了。多少年后,我路過那個村莊,想起秋天的那個中午,舅爹從危樓的樓梯送我下來的情景。我奶奶去世時,舅爹沒有送我奶奶,他當時也重病在身,但我一直無法理解他為什么沒有能夠撐著病體和他的姐姐做最后的告別。
婆太太家的這條巷子,原來叫女廟巷,后改稱井巷,但奶奶習慣叫它女廟巷。一口古井居中,巷子兩側是粉墻黛瓦。井巷的房子似乎都特別高大寬敞,可以想象當年這條巷子的富貴景象。奶奶就是在巷子里裹腳又放腳的,這位“聞記棉線店”的二小姐,把往昔繁華的生活和她在女廟里聽來的故事都梳進她的發髻里。即使在最潦倒的日子里,奶奶在鄉下依舊保持著鎮上大家閨秀的風采。我奶奶在她晚年經常向我講述的我們那個大家族的故事,早已離我和我的兩個弟弟遠去,我們像聽別人家的故事一樣。在村上我家不大不小的天井里,總是放著兩只荷花缸。奶奶說從前鎮上老屋天井里的兩只荷花缸比現在的大多了,我爸爸的印象中也是這樣,祖輩給我最詩性的記憶就是缸里的荷葉。
在奶奶的敘述中,我陸續知道聞家的歷史和一些規矩:在鎮上和縣城有幾家棉線店;三個舅爹都是讀書人;中秋節的月餅從大到小放在盤子里;奶奶和她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姨奶奶,有空時就去書場聽書(姨奶奶跟我說她很少去,奶奶去得多);家里人不到齊了,不好開飯;吃飯不能有聲音,筷子只能伸到菜盤子靠近自己的這一邊;吃好了要對長輩說慢慢吃,不能起身就走,起身時要說“您坐穩了”;早上起來要向長輩請安;做生意要老少無欺;親友往來不能嫌貧愛富。這些歷史和規矩后來都滲透在我家的日常生活中,我有一段時間比較習慣繁文縟節,與我們家族的傳統有關。
爺爺家所在的兩千米之外的那條巷子依水而建,很像我們熟悉的周莊,爺爺的家在這條巷子里,有好幾進房子,比奶奶的娘家還要闊綽。爺爺的規矩和奶奶娘家是一樣的,那是鎮上大戶人家通行的禮數。數百年來,這些規矩成為小鎮文明的面貌之一。我的曾祖父也是經商的,開油店。我喊曾祖父老爹。我爸爸說,附近的幾個鎮吃的都是老爹家的食油。我媽媽見過老爹,在我出生的第二年,老人家去世了。我一直沒有問我的爸爸媽媽,老爹有沒有見過我。我看到老爹的照片,一臉的嚴肅甚至刻板。但所有熟悉曾祖父的人都說到他的寬厚仁愛,曾祖父從來都答應顧客賒賬,一直到他破產都沒有收回欠債。我對祖屋的最初印象非常陰冷,曾祖父去世后沒有安葬,靈柩停放在家里。我從記事開始,就很怕去鎮上的祖屋,進去后就要到停放祖父靈柩的屋子里磕頭。頭磕好了,再向曾祖母請安,我喊曾祖母“老太”。我看不出老太是爺爺的后媽,爺爺奶奶對她行禮如儀。那時糧食特別緊,新米出來后,我爸爸媽媽總是到鎮上給老太送新米。
我直到讀初一后才知道,我所見到的老太是我老爹的填房。那一年春節,我的幾位姑奶奶都到我們家了,在她們的言談中,我聽到她們對老太的一些非議。我想沒有女兒會這樣議論媽媽,這才知道老太的身份。當時我覺得自己很愚蠢,從爺爺和幾個姑奶奶的年齡,我應該能夠算出他們和老太的關系。是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對老太的尊敬,讓我失去了判斷力。我的兩個姑奶奶,和我的奶奶一樣,頭發一絲不茍,衣服整整齊齊。我覺得大姑奶奶特別像我的老爹,不茍言笑。二姑奶奶則端莊中帶著微笑,露出潔白的牙齒。二姑奶奶家的圣堂村離我們十里路,我不常去。有次到圣堂,二姑奶奶看到我了,拉我去她家,用鐵鍋做雞蛋餅,她用稻草燒火,慢慢把蛋餅烤脆。二姑奶奶說,你要好好念書,王家就靠你了。我的大爺一家在解放前就去了泰州,和我們這邊幾乎不往來。這邊的兩個姑奶奶幾乎把我看成是中興家族的希望。兩年后的1975年,我初中升高中,突然要通過考試升學,考點就在圣堂村。中午在二姑奶奶家吃飯,我的表伯問我上午作文是什么題目,我告訴這位小學校長:讀書務農,無上光榮。
婆太太家和老爹家的產業在國共內戰期間破產。我的爺爺奶奶帶著我爸爸和兩個姑姑到了鄉下,兩個姑奶奶則在相鄰的一個村子里。他們都成了難民。從鎮上到鄉下,那幾年一定是異常煎熬。我的大姑姑過繼給了我的姨奶奶,她留在鎮上,二姑姑出嫁回到鎮上。小姑姑在鄉下長大,成了和大寨大隊鐵姑娘一樣的農村青年。我們的家族中真正被鄉村改變的就是小姑姑一人,最終小姑姑也嫁到了鎮上。這好像是命定的秩序,她們都回到了曾經的繁華夢中。但今非昔比,無論如何家道衰落了。她們都帶著舊的記憶開始新的生活。或許是因為我的爺爺有專長,到鄉村不久,他就被政府安排到另一個鄉的糧管所,發揮他的專長了。我的奶奶差不多是三分之一時間在爺爺那里,三分之一時間在村上,還有三分之一時間則是到鎮上和我的幾個姑姑一起住。我會在假期中到爺爺那里住幾天,爺爺非常嚴格,管理糧食倉庫就像管理自己家的一樣。糧倉里有成堆成堆的北方的山芋干,即使不煮熟也可以吃。爺爺看到我盯著山芋干的眼神,便說:你一塊也不能拿。我回去時,奶奶總是送我到很遠很遠的路口,我走了很遠回頭時,奶奶還站在那里。我易于傷感,或許就是在這樣的場景中養成的。有一次,奶奶很生氣,說她送我時,我頭也不回就走了。我想了想,我是回頭向奶奶致意的,但回頭的次數可能比以前少了。我在長大,我消失在行走的人群中,奶奶的眼睛也老花了,她可能看不出我的背影了。
我一直對奶奶經常去姑姑家很不開心,特別是農忙時,家里需要有個人燒飯什么的。但奶奶總是長時間住在鎮上。現在想起來,我可能缺少對奶奶的理解,她不是住在姑姑家,她是回到她的過去。奶奶到鄉下幾十年,但她總是生活在女廟巷里。我凝神看著奶奶一絲不茍地梳髻,她一板一眼的動作,仿佛是一種程式,她對往昔生活的記憶化為對現時生活的規范。少年的我常常納悶,這么多年過去了,奶奶仍舊是當年的聞二小姐。每次回到鎮上,我便進入奶奶規范的生活秩序之中,無論是在老街還是在井巷,我遇到的人都是我的長輩。直到有一天,奶奶熟悉的一個尼姑從鄉下跑到女廟巷沉井身亡,這個和奶奶年齡相仿的尼姑的死讓這口明末的水井廢棄了。我這才找到了不去井巷的理由,我從小就怕鬼,很久以前,我就慶幸我們這個家族在解放前夕的衰落,那個舊式家庭尚未完全消失的輪廓讓我后來理解了為什么有那么多的富家子弟會投奔解放區。
我們村上的宣傳隊演出京劇《智取威虎山》時,正值百年未遇的大水,田里所有的麥子都淹沒了,麥穗再也沒有抬起頭。插秧以后,宣傳隊開始排練,我爸爸被挑選扮演楊子榮。爸爸覺得自己不合適,很多年沒有演戲了,但宣傳隊長說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人了。楊子榮打虎上山那場戲需要穿皮毛大衣,我們村上沒有一家人有這樣的衣服。還是奶奶想起,老爹以前有的,可能在六爺爺那里(我爺爺同父異母的弟弟)。誰去問六爺爺借?奶奶主動說她和我一起去。聽說是演樣板戲用,六爺爺很爽快地答應,從箱子里找出來了。出門時,奶奶說,我去女廟巷,你去不去?我說不去。奶奶一個人獨自去了。
我抱著皮大衣坐在大會堂門前的臺階上,大衣有一股樟腦丸的味道,我把它貼在臉上,已經嗅不到老爹的氣息,但陽光照耀下的皮毛大衣還是呈現了往昔家族的小康氣象。中午過后的陽光終于有些暖意,但水泥臺階依然冰涼。我走下臺階,蕩回石板街。我穿起了老爹的皮毛大衣,再脫下。這個街上沒有人認識我,那幾個和奶奶打招呼的老人,當年或許也就是在我這個年紀看到我老爹穿著這件皮毛大衣從這條街上走過。他們早就沒有理由想我老爹了。即使是我這個曾孫,也正在逐漸失去對祖先的記憶。我記不清我第一次走進時堰鎮祖居的時間,在我模糊的記憶中,它留給我的感覺如同我走進生產隊場頭下的地道,潮濕、陰冷,讓人透不過氣來。我無法想象我的曾祖父就在這里有滋有味地過著他的油店老板生活。在我祖居的隔壁,就是著名地理學家許先生的故居,那棟房子現在已經成了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了我的母校中學掛牌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它也一樣的潮濕和陰冷。我猜想,那位比我祖父還高出一輩的許先生,他最終成為一名水利學家,或許與他想告別這里的潮濕和陰冷有關。
奶奶去女廟做什么?她在回村莊的路上說,她去給那個投井的尼姑燒紙了。奶奶不僅是去悼念她少女時的朋友,可能也是憑吊自己的過去。奶奶走路很慢,她的身上馱著她的女廟巷和這個小鎮。在村上居住的日子里,我們兄弟仨每天早晨起來的第一件事是按照多年的規訓到奶奶的房間喊奶奶早。爺爺退休后,我們早上起來喊爺爺早、奶奶早。奶奶有一只箱子,我從沒有見她打開過。有一天,我偶然看到她打開了,就很好奇地湊上去,奶奶已經來不及蓋上了。箱子里有上海三四十年代的香煙廣告,廣告上一個妙齡女郎優雅地抽著香煙。那是我第一次遇見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好像還有胭脂什么的。我很好奇,封建的奶奶怎么會藏有這些東西。
很長一段時間,我總覺得奶奶把舊社會的東西帶到了鄉下,后來我逐漸意識到,奶奶其實也在延續一種和鄉村生活格格不入的文明或者是一種生活秩序。奶奶一輩子都生活在她的舊時代,她從來沒有走出那個小鎮。我感覺到的那種差異,其實是一個時代殘存的瘢痕。對我這樣的一個鄉村少年來說,小鎮就是我的文明背景,那里有著和在鄉村不一樣的生活,盡管只有十幾里的距離。其實也不只是我,我的長輩們大致也是這樣的,小鎮就是一個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和商業中心。城市或者都市離我們太遠,那些地方給我的感覺是一個人在麥田里揀麥穗時,突然有飛機從上空掠過,轉眼即逝。而小鎮不同,小鎮就像你的一個遠房親戚,它雖然和你可能只是點頭之交,但不管怎么說,你能夠從心里的譜系中找到自己與它的關系。在我們這些孩子長大的過程中,小鎮刺激了我們所有的欲望,包括繁華、權力、身份,和女人。做文學的人,做社會學的人,常常說到城鄉沖突,其實疏忽了在城鄉之間還有另外一個地帶,小鎮。但恰恰也是這樣的小鎮,甚至連彈丸之地一詞都不足形容的小鎮,充其量只能說是一粒麥子那樣大的小鎮,卻可以徹底摧毀你的內心,讓你在十里之外面對它時,產生自卑和恥辱感。我們那個村,距離小鎮差不多只有十里,但這十里路如同天塹,是兩個世界的分界線。鎮上的人到村上去說是“下鄉”,村上的人到鎮上去,人家說你“上來了”。我現在回去,倘若開車,只要十幾分鐘就可以到達小鎮了,但在當年,這條路在心里卻是千里迢迢、望不見盡頭的。
我在奶奶的小鎮讀完了高中,也把石板街留在我的記憶中。即便在另外一條石板街上走過,我也會想到鎮上的那條石板街。我不知道是我自己還是石板街,如同幽靈一般。2004年的冬天,我在蘇州甪直老街游逛時告訴同伴,我仿佛行走在老家那條石板街上。我在來蘇州讀書前就知道,我們那個鎮上的許多人家是從蘇州閶門流落到那兒的。
奶奶是在鎮上病危的,她堅決不肯回到村上壽終正寢。我從蘇州趕回,到了老屋,奶奶已經處于彌留之際。我拉著她的手,我從她的嘴唇里聽出她在喊我的名字,然后,她閉上了眼睛。這是1985年10月的一個傍晚,奶奶在鎮上去世了。在鎮上安葬好奶奶,我回到了村上。我在村前的那個水碼頭駐足良久,很多年后我開始寫作一部至今未完成的小說,小說開頭是: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底下。當年,爺爺奶奶帶著他們的兒女坐船從鎮上到鄉下,就是從這碼頭上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