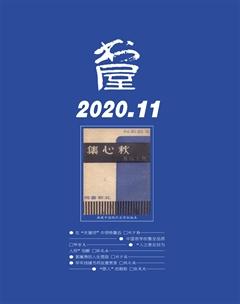鄭樵的治學之道
楊阿敏
鄭樵自述其生平著書千卷,《宋史》本傳稱其“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然其著作多不存。福建《興化縣志》云,“先生之書凡五十八部,五百九十余卷”,所知已不全。而《四庫全書總目》雖稱其生平銳于著述,而記其著述才“已成者凡四十一種,未成者八種”,其所知愈少,或是疏于考證。1923年顧頡剛先生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二號上發表了長文《鄭樵著述考》,首次系統考辨鄭樵著述情況。后吳懷祺先生在前人基礎上撰成《鄭樵著述表》,據其統計,鄭氏合計著述九十八種,注明篇數、卷數的為五十種共六百三十卷四百五十六篇,尚有三十五種未注明卷數。據此可見,鄭樵所言千卷非虛。以“天地間一窮民”而著述如此豐厚,其治學之道必有可觀者。
未有不讀書而能著書者,鄭樵“生長山野,幼不學犁鋤,慨然有讀書志,胸中便以古人自期”。讀其書,慕其為人:“每于史冊,見一傳而高風凜凜者,必讀之再三,通即掩卷長思,躋仰其為人,抃搏氣概以從之游,若驟若馳,及之而后已。”此亦讀書一大用。今人讀書多不思追慕其人,見賢思齊,只以為難以企及,遂無此念,甘心平庸。如此讀書,雖多亦有何用?書自書,我自我,何曾半點相涉。鄭樵“家貧無文籍,聞人家有書,直造其門求讀,不問其容否,讀已則罷,去住曾不吝情”,可見其讀書之心是何等迫切。此等行為,書生大多難以辦到,不得不顧及世俗之眼光。想鄭樵當日多少應受過些白眼,吃過些閉門羹吧。在今日,有公共圖書館可供借閱,又有幾人有此讀書之心呢。
其一生志向所在,不過“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志向不可謂不高。為實現這一理想,鄭樵秉持“在日月之下而不敢辜負寸陰”的精神艱苦著書。雖在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即使廚無煙火,依舊誦記不絕。積日積月,一簣不虧。搜盡東南遺書、古今圖譜,乃至上代之鼎彝,四海之銘碣。遺編缺簡、竹頭木屑無所不求,只為“見盡天下之圖書,識盡先儒之閫奧”。
鄭樵將書籍所言分為可以己意而求的人情事理(這其中即包括宋儒的窮理盡性之說)與不學問則無由識的實學,這其中則主要為鄭樵大力提倡的天文、地理、車輿、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學。他認為:“人情事理可即己意而求,董遇所謂讀百遍理自見也。乃若天文、地理、車輿、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名,不學問,雖讀千回萬復,亦無由識也。”而當時的學者只知操窮理盡性之說,以虛無為宗,置實學不問。
此處鄭樵提及的三國時董遇的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早已人盡皆知,有一極有意味之細節與此相關,卻可能不大為人所注意。據《三國志·魏書·鐘繇華歆王朗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曰:“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余。或問三余之意,遇言:‘冬者歲之余,夜者日之余,陰雨者時之余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董遇教人讀書自悟,從學者深以為苦,畢竟不如聽老師講授來得容易,所以其后跟隨他學習的人越來越少,他的學問也就無人傳承了,可見以“讀書百遍而義自見”教人是有風險和代價的。而鄭樵描述自己寒窗苦讀之情景,絲毫不見讀書之苦,只覺其樂在其中,不知疲倦:“寒月一窗,殘燈一席,諷誦達旦,而喉舌不罷勞;才不讀,便覺舌本倔強。或掩卷推燈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屬,口不誦,而心通。人或呼之再三,莫覺。”口誦心識,曾無半刻虛度,其精神恐不減董遇之“讀書百遍”與“三余”。
對于那種只知籠統而言名物制度,實則不知所云的做法,鄭樵深致不滿:“遇天文則曰此星名;遇地理則曰此地名、此山名、此水名;遇草木則曰此草名、此木名;遇蟲魚則曰此蟲名、此魚名;遇鳥獸則曰此鳥名、此獸名。更不言是何狀星、何地、何山、何水、何草、何木、何蟲、何魚、何鳥、何獸也。”這只不過是偷懶取巧的做法,“縱有言者,亦不過引《爾雅》以為據耳,其實未曾識也”。
對此,鄭樵以身作則,親自實踐,力求在實踐中求真知。歷世《天文志》徒有其書,無載象之義,故而學者但識星名,不可以仰觀星象。為求得天文知識,鄭樵根據《步天歌》觀測天象,一一目驗:“一日得《步天歌》而誦之,時素秋無月,清天如水,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數夜,一天星斗盡在胸中矣。”前代《天文志》多言吉兇災祥,鄭樵皆削去不采:“夫災旱易推之數也,慎、灶至精之術也,而或中或否,后世之愚瞽若之何而談吉兇!知昭子之言,則知陰陽消長之道可以理推,不可以象求也。知子產之言,則知言而中者亦不可聽,況于不中者乎。臣之所作《天文書》,正欲學者識垂象以授民時之意,而杜絕其妖妄之源焉。”鄭樵從事實出發,認識到占候之說或中或否,即便所占得中亦不可聽,何況是不中者。認識天象,是為獲取服務于民眾生產生活所需的歷法氣象知識,而非妄推天人感應之道。
此種理性求實的精神還體現于《災祥略》中:“今作《災祥略》,專以記實跡,削去五行相應之說,所以絕其妖。”鄭樵將這種“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兇而曲為之配”的做法稱為“欺天之學”。在鄭樵看來,“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柰何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一一質之以為禍福之應,其愚甚矣”!而“惟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者,可以為通論”,這一說法不獨對我們認識自然界有所助益,就為人處世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
又如鳥獸草木之學,與《詩經》密切相關,是理解《詩經》的一大關鍵。夫子論學《詩》之用時即有“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之說,不識鳥獸草木之名亦難以準確閱讀《詩經》。鄭樵在《通志·昆蟲草木略·序》中曾舉數例:“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雁鶩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鷕鷕,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鳧雁,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蘋,不識鹿則安知食蘋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蔞蒿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關、‘呦呦之興乎?若曰‘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者,謂瓜苦引蔓于籬落間而有敦然之系焉。若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者,謂桑葉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
因“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而農圃人又不識《詩經》等經典文獻之旨意,二者無由參照考核,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為彌補這一缺憾,鄭樵“結茅夾漈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他將文獻記載與田野考察結合起來,所得庶幾不誤。
通過鄭樵對名物制度之實學的考察,可見其強調學問之道,貴乎親見親聞。《通志·金石略·序》云:“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以后學跂慕古人之心,使得親見其面而聞其言,何患不與之俱化乎。所以仲尼之徒三千皆為賢哲,而后世曠世不聞若人之一二者,何哉?良由不得親見聞于仲尼耳。蓋閑習禮度,不若式瞻容儀;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今之方冊所傳者,已經數千萬傳之后,其去親承之道遠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為略,庶幾式瞻之道猶存焉。且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此道后學安得而舍諸!”鄭樵認為,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親見其面親聞其言,其影響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自然與之俱化。去古人已遠,無由親承。較之書冊經多次傳抄轉手,金石保留了更多的原始信息和面貌,從中可見古人之風神與時代之精神。
鄭樵在《上宰相書》中介紹尚未成書的《通志》說:“其書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書為一書。惟虛言之書不在所用。雖曰繼馬遷之作,凡例殊途,經緯異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特別強調了其獨創之處。在《年譜序》中,鄭樵有一個創造性的誤讀。序云:“太史公之表,紀年不過六甲,而省其五十四,紀事不過十余言,而為事之目,所謂綱舉而目張也……《史記》于六十甲子之統而提其六,近代作編年者盡用六十,已為繁矣。而復有甚焉,乃用歲陽歲陰之名,甲曰閼逢,乙曰旃蒙,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此皆陰陽之命,而不可以紀甲……著書者貴乎意明而語約,以六甲視六十甲,則衍八百言;以六甲視六十歲名,則衍二百五十二言。以古較今,其繁簡如此。今之所譜,但記六甲。”鄭樵以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的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為太史公故意如此紀年,六十甲子只書其六,其余省略不書,語約而意明。
其實這只是一個美麗的誤讀,清儒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十二諸侯年表》考證說:“《史記》諸年表皆不記干支。注干支出于徐廣。《六國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廣曰壬辰,是也。《十二諸侯年表》共和元年亦當有‘徐廣曰庚申字,今刊本乃于最上添一格書干支,而刪去徐廣注,讀者遂疑為史公本文,曾不檢照后二篇,亦太疏矣。考徐注之例,唯于每王之元年記干支。此表每十年輒書‘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不特非史公正文,并非徐氏之例,其為后人羼入鑿鑿可據。且史公以太陰紀年,故命太初之元為閼逢攝提格,依此上推共和必不值庚申,則庚申為徐注又何疑焉?”
干支紀年并非太史公原文,乃后人添加,刊本又于最上添一格書干支,而刪去徐廣注,遂使讀者誤認為史書本文。鄭樵據此還算了一筆賬:“以六甲視六十甲,則衍八百言;以六甲視六十歲名,則衍二百五十二言。”既然繁簡相差如此之大,為何不以簡馭繁,因此《年譜》中就欣然使用六甲紀年。從實際效果來看,以六甲紀年也不妨礙紀年的準確性,在作者還減少了書寫量,這一創造性誤讀倒也不無價值。只是其間空余不書的部分,就尚需讀者稍加推求了。
在《通志·六書序》中,鄭樵提出由小學入經學的治學方法,為清儒之先聲。其論曰:“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圣人之道惟藉六經,六經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清初大儒顧炎武在《答李子德書》中說:“故愚以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二者雖有文字與音韻之別,但由小學入經學的路徑是一樣的。其后戴震《古經解鉤沉序》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圣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錢大昕《左氏傳古注輯存序》亦云:“夫窮經者必通訓詁,訓詁明而后知義理之趣。后儒不知訓詁,欲以向壁虛造之說求義理所在,夫是以支離而失其宗。”強調由語言文字之學而通經文,由經文而明道,這是清代學術界的共識,也是清儒治學之途徑。鄭樵遠在數百年前性理之學日熾的時代思潮中能孤明先發,確為卓識。
著述能否傳世是作者心中永恒的焦慮。鄭樵作為一介布衣,其著作既無子弟可傳,又無名山石室可藏,這種憂慮就更加突出,他在《上宰相書》中表達了希望自己的著述能投納秘書省的想法:“樵暮齡余齒,形單影只,鉛槧之業甫就,汗簡之功已成。既無子弟可傳,又無名山石室可藏,每誦白樂天‘恐君百歲后,滅泯人不聞。賴中藏秘書,百代無湮淪之句,未嘗不嗚咽流涕。會茲天理,不負夙心,仰荷鈞慈,果得就秘書省投納。蓬山高迥,自隔塵埃;蕓草芬香,永離蠹朽。百代之下,復何憂焉!”這篇文章大約作于宋高宗紹興十七年(1147),鄭樵四十四歲。當時他已“山林三十年,著書千卷”。但這時《通志》尚未修成,在這封書信中鄭樵給出了一個成書時間:“若無病不死,筆札不乏,遠則五年,近則三載,可以成書。”實際完成此書遠不止這幾年,此書實匯聚了鄭樵一生著述之精華。鄭樵五十九歲那年,高宗命以《通志》繳進,而鄭樵以命下之日卒。所幸這部巨著全帙得以流傳至今,也不負其一生艱苦著述之心血。百代之下,復何憂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