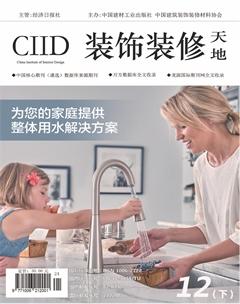對建筑工程造價控制的動態管理分析
張紅琴
摘 要:工程造價的動態管理與控制是建筑工程中的重要內容,提高工程造價動態管理與控制的科學性,對建筑工程的施工質量起到促進作用。從建筑工程造價動態管理與控制的重要意義、建筑工程造價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動態管理與控制的主要措施闡述建筑工程造價的動態管理與控制。
關鍵詞:建筑工程造價;控制;動態管理;研究
1 引言
建筑行業在現代社會的不斷快速發展,不僅能夠為現代人的日常生活帶來非常多的便利條件,而且還能夠滿足現代人對現代建筑物提出的個性化需求。但是現階段,建筑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建筑企業要想在市場中占據有利位置,提高其綜合競爭力,就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經濟效益。如果單純從建筑工程造價的角度出發對現代建筑行業的發展情況進行分析,那么不難看出,建筑工程造價當中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導致建筑行業的經濟效益受到影響。因此,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利用動態管理模式對工程造價進行有效控制。
2 建筑工程造價控制的動態管理的重要意義
工程造價對建筑工程資金的預算,建筑工程在施工過程中,對建筑造價實施動態管理符合現代工程造價的實際應用過程,在建筑施工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必須及時處理,在預算與實際原材料的價錢等都必須進行及時的調整,這就是工程造價實施動態管理。工程造價實施動態管理,必須科學合理的進行預算,提升其應用的過程,對質量與造價形成統一的應用過程,保障工程的安全施工。工程造價動態管理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對保障工程質量,需要對建筑造價進行動態造價進行有效協調,提升工程質量,對其經濟效益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3 建筑工程造價控制的動態管理過程中現存問題分析
3.1 各個環節嚴重脫節
建筑行業的工程造價控制效果,不僅能夠對其未來發展產生影響,而且還會對其經濟效益產生影響。因此,在針對工程造價進行管理時,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直接通過全過程管理的方式,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由于建筑工程本身的涉及范圍就比較廣,而在這些方面都會涉及到工程造價問題。但是從現階段的造價控制效果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各個環節之間嚴重脫節,不僅會對工程造價的實施效果產生影響,而且嚴重的情況下,還會威脅到建筑工程的施工質量。各個環節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相互之間并沒有建立有針對性的溝通和互動機制,導致各個環節無法實現有效的協調。一旦某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那么將會導致整個施工過程出現問題,甚至還會引發斷層現象。
3.2 審批控制存在問題
建筑工程一般都具有比較大的規模,所以需要耗費的時間也比較長。因此,在日常管理過程中,會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內容。即使是同一個工程項目,在不同環節的施工操作過程中,會涉及到的內容、施工流程等都會存在明顯的差異性,而這些環節當中也會出現各種不同類型的問題。針對這一現象,在建筑工程項目施工過程中,要盡可能對每一個環節進行嚴格有效的審批控制。但是從現階段的實際情況可以看出,建筑工程的各個環節大多數都是獨立存在,審批控制不僅沒有得到重視,而且其整體管理能力也比較弱。
4 動態管理與控制的主要措施
4.1 認識到動態管理與控制的重要性
工程造價的動態管理是符合現代建筑行業的需要,在我國現在建筑行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現階段仍存在部分建筑工程企業不能全面、準確的認識建筑工程造價管理的重要性,并在落實建筑工程造價管理的過程中,盲目的根據管理經驗或習慣進行。這直接導致我國建筑工程造價動態管理與控制的科學性和合理性難以保證。在此背景下,要真正發揮建筑工程造價管理與控制在激勵市場競爭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升建筑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應通過擴大宣傳等手段,使建筑工程相關主體的管理者認識到造價動態管理與控制的重要性。并在日常管理、決策的過程中積極建設工程造價管理隊伍與機構,保證工程造價動態管理與控制的科學性、專業性和合理性。工程造價的動態管理是一項動態過程,必須科學進行有效的管理,體現工程造價動態管理的重要性。
4.2 加強對動態工程造價管理的重視
建筑行業在發展過程中,一直會受到一些傳統建筑工程粗放型管理理念的影響,導致現代建筑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仍然缺乏對工程造價管理的重視程度。部分建筑企業并沒有意識到動態管理的重要性,還有部分建筑企業對動態管理控制理念的認識和了解并不是很深刻。即使部分建筑企業在建筑工程造價相關措施實施過程中,將動態管理模式應用其中,但是也無法發揮出實質性的應用效果。因此,針對這一問題,建筑企業要先樹立對動態管理控制理念的正確認識,從提高自我認知水平的角度出發,加強管理人員以及工作人員對動態管理的認識和了解。與此同時,要將動態管理的作用和價值充分發揮出來,實現對工程造價的有效控制。只有在工程造價當中,將動態管理控制的作用和價值充分發揮出來,才能夠逐漸影響到更多的工作人員,不僅強化這些工作人員的動態管理意識,而且還能夠實現動態管理控制措施的有效落實。
4.3 建立完善的制度
工程造價動態管理是建筑工程中的重要環節,但工程造價動態管理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根據實際應用的制度進行科學有效的管理,必須認真執行其規章制度,讓工程造價在建筑工程施工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制度的實施,這對建筑工程的施工質量都起到重要作用。
4.4 施工階段的動態管理
在建筑工程造價工作中,施工階段的造價控制是核心內容,也是確保工程如期交付的前提,施工階段的造價管理對于工程決算也有直接影響,關乎著整個項目的成本預算。有些單位在施工過程中對于原材料的價格不夠重視,當出現市場價格變動時不能及時做出調整,而是完全以招標書或者是施工合同上的價格為主。要確保預算管理在施工階段的應用質量,要弄清楚施工階段涉及的各項內容,協調好各部門的關系,在合同執行、制定環節,要確保管理、監督各個部門的工作能夠得到有效落實,選擇綜合素質過硬的施工隊伍,將施工環節的損失降低至最小化。
4.5 建筑工程造價動態管理控制要點分析
在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物價一直都是以一種動態化的狀態存在,這樣就會導致人工費用、材料、設備等費用相互之間存在嚴重的偏差現象。在建筑施工過程中,人工差額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能夠直接影響工程造價的實施效果。所以,針對這一現象,建筑企業需要結合市場物價的實際變化情況,針對工作人員的薪資進行實時有效的調整和優化。通過基本工資、津貼補助等各種不同類型的福利待遇方式,應和物價不斷的變化,同時還能夠實現對人工差額的動態管理控制。
6 結語
我國的經濟水平正在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不斷提升,而建筑工程行業在這樣的背景當中也迎來更多的機遇,對建筑工程造價應用動態管理模式,能夠把控好建筑工程的質量、安全、進度,對于建筑企業的管理水平、綜合效益也有重要影響。就當前來看,動態管理模式的應用還處于初級階段,其中還存在一些問題,作為造價設計人員,要對動態管理模式有深刻的認知,提高自身的綜合水平,充分發揮出動態管理模式的應用質量。
參考文獻:
[1] 陳友根.建筑工程造價的動態管理和有效性管理[J].居舍,2018(2):138.
[2] 王中琴.建筑工程造價的動態管理與控制探討[J].工程技術研究,2017(12):136~137+140.
[3] 繆麗琴.淺析建筑工程造價的動態管理與成本優化控制[J].江西建材,2015(16):267~268.
[4]劉荷花.建筑工程造價的動態管理與控制[J].江西建材,2015(3):258~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