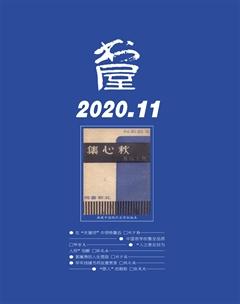梅娘“佚文”發(fā)現(xiàn)記
肖伊緋
2020年,是東北女作家梅娘(1920—2013)百年誕辰。梅娘本名孫嘉瑞,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東北地區(qū)重要作家,也是抗戰(zhàn)期間淪陷區(qū)重要作家之一。
梅娘出生于海參崴,在吉林省長春市長大。1936年出版《小姐集》。后赴日本求學(xué)。1940年代曾出版《第二代》和《魚》、《蚌》、《蟹》水族三部曲,在華北淪陷區(qū)文壇脫穎而出,為同時(shí)代女作家中佼佼者。晚年寫作以散文創(chuàng)作為主,出版有《梅娘小說散文集》、《梅娘近作及書簡》等。
后世讀者大都以為,梅娘的文學(xué)作品應(yīng)當(dāng)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qū)發(fā)表與傳播,不太可能在南方地區(qū)報(bào)刊上發(fā)表。約在十年前,那一場“南玲北梅”的爭論之中,認(rèn)為梅娘不可能在南方文壇有所影響,更不可能與“南玲”(即張愛玲)相提并論者不在少數(shù)。持此種意見者,秉持著一種看似符合常理的經(jīng)驗(yàn)之談,殊不知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歷史之復(fù)雜,遠(yuǎn)遠(yuǎn)超出后世讀者的想象,也并不一定符合所謂“常規(guī)”的推理經(jīng)驗(yàn)。且說七十余年之前,1944年新年伊始,已經(jīng)早成為“孤島”的上海,一本叫《文潮》的文藝月刊創(chuàng)刊。雜志主編是馬博良,發(fā)行者署名文潮社,社長鄭兆年。翻開這本三十二開大小的雜志,就會發(fā)現(xiàn)上海本地作者為其寫稿者少之又少,反而是一些北方作者頻頻有新作刊出。據(jù)說,由于傳聞馬博良的父親與敵偽有關(guān)系,所以上海作者很少為這本雜志寫稿,因此雜志社方面不得不舍近求遠(yuǎn),開始了“北文南刊”的運(yùn)營模式。
可想而知,慘淡經(jīng)營之下,這本《文潮》月刊不太可能支撐多久。據(jù)考,該雜志只印行了七期即告中止。1944年10月,馬博良重整旗鼓,又辦了一本《文潮副刊》的小冊子,仍是三十二開大小。但每期只有十六個(gè)頁碼,刊物作者還是以北方作者為主。《文潮副刊》可能是雙周刊,因?yàn)楫?dāng)年十月創(chuàng)刊,當(dāng)月即出了兩期。這一雙周刊應(yīng)當(dāng)也沒有支撐多久,究竟印行了多少期,至今沒有十分可靠的論證。據(jù)李相銀所著《上海淪陷時(shí)期文學(xué)期刊研究》,該刊共出四期;但因筆者未見實(shí)物,尚無法斷定。總之,正因?yàn)椤捌涿膊粨P(yáng)”、“其壽不長”,對《文潮副刊》鮮有深入了解者。
筆者偶得《文潮副刊》第二期一冊(1944年10月21日出版),初次觀感實(shí)在是觸手極薄、簡陋異常。但仔細(xì)一看篇目,這本只有巴掌大的小冊子,還真是“小中見大”,內(nèi)容頗有看點(diǎn)。首先,封面文章即是沈從文的《湘西的蠱婆》。此文最早刊于1944年4月初版的沈從文所著《湘西》一書中,但半年后摘錄發(fā)表于《文潮副刊》之上,文字上又略有修訂。如果該文確系沈從文授權(quán)發(fā)表,那么《湘西的蠱婆》一文就此也算有了另一個(gè)版本,即所謂“文潮版”,值得研究者關(guān)注。
此外,在“掌篇小說輯”欄目中,榜列頭名的文章《茄子底下》,乃當(dāng)時(shí)北方淪陷區(qū)著名女作家梅娘的作品,應(yīng)屬首次發(fā)表,或?yàn)椤柏摹保辽賹儆谀戏降貐^(qū)發(fā)表梅娘作品的鮮見之例。
為分享文獻(xiàn),共同研討計(jì),筆者不揣陋簡,酌加整理,轉(zhuǎn)錄原文如下:
茄子底下
梅娘
聽見賣菜的人在街上喊,我拿了菜籃子走出來。那是一個(gè)常來我門口賣菜的老頭,有六十歲的樣子,頭發(fā)已經(jīng)全白了,據(jù)說是三個(gè)兒子都娶了媳婦,有五六個(gè)孫子。原來是很好的日子,因?yàn)槟暝缕D難,老了反想不得不出來抓飯碗吃。他菜賣的比較便宜,分量也很公道,這條胡同里的人差不多都照應(yīng)他。他人雖然老,聲音卻還相當(dāng)宏亮,喊起來的時(shí)候,就是住在最里層院子的我,也能聽得很清楚。
我走到門口的時(shí)候,恰好有一輛載重車急馳而過,為了躲避那飛揚(yáng)起來的塵土,我沒拉開門。但是開了門上的投信口往外瞧了瞧。
真巧,老頭的菜車子就停在我門前,他正倚著菜車站著,手里仿佛拿了一樣?xùn)|西。我聽見他低低聲說:
“多少尺?”
“十六尺。”一個(gè)女人的聲音。
“價(jià)錢呢!”他問。
“還照上回那樣就行。”女人說。
顯然他們是在做著一件交易了,我斷定那不是一件正當(dāng)?shù)馁I賣,他們的聲音鬼祟得很。
“幫我一把,我把它放在茄子底下。”他停了停說。
“臟了。”女人說。
“您把它包好,不礙的,我這還有紙。”他說。
在一陣紙響之后,我聽見移動茄子的聲音,我驟然拉開我底門。
和老頭一塊站著的是潘宅做飯的李姐,李姐的身后站著潘宅看小孩的王姐,他們?nèi)硕几┥碓诓塑嚿希犚娢业拈T一響,立時(shí)驚駭?shù)鼗剡^頭來。
李姐立刻回身去遮著茄子筐,說:“這老頭子,沒好心,把好茄子都藏在底下,壞的放在上頭,真沒見過,好的反倒怕賣。”說著,把高高地堆在一邊的茄子推平了。
王姐和老頭笑著招呼著我。兩人都笑得非常勉強(qiáng)。我也笑著答應(yīng)他們。
他們是合伙偷了誰的布嗎!可怕的家賊,可怕的表面上很忠厚的窩主。
“今天的火辣椒太好,您留點(diǎn)吧!真新鮮。”老頭從一只筐子里撿出兩個(gè)碧綠的大辣椒,舉到我眼前來。
“是不錯(cuò)!您買點(diǎn)吧!”那兩個(gè)人也附和著說,搭訕著走開去,李姐提著的籃子里擺著茄子和辣椒。
“不!”我瞧著老頭的臉,“我不要,我要買兩個(gè)茄子。”
“茄子不大好,要不,你來點(diǎn)棍扁豆。”他熱心地?cái)r著我,深恐我買了壞菜。
“我自個(gè)看看。”我說,一只手去拿茄子。
“我給您拿吧!我給您拿,我知道那有好的。”他慌忙地來拿茄子。我忍不住地摸了起來。
“李姐說是底下的好,我來找一找。”我說。不管他拿不拿,真的用手向筐底下摸去。
“您看!您看!您挑不著好的,瞧這個(gè)多好,多好,我哪能騙您呢?”他高高地舉起一個(gè)大茄子,焦灼地說。
瞧見他急了,我縮回手來,接過他拿著的茄子來,真是不幸得很,那茄子長了一個(gè)大疤。
“你瞧,這是你挑的好茄子。”我指著那個(gè)粗糙的疤痕。
“我眼花了,太太,您別生氣,我真沒看見,我再給您挑挑。給您挑好的。”他捶了自己的頭一下,低下頭去找茄子。
“不是你眼花,是心慌了吧!”我笑著說。
“您,您,您這是什么話?我,我,我哪能心壞呢。”他突然結(jié)巴起來,更加不敢抬起他的臉來了。
“我沒說你心壞,我說你心慌。”
“我心慌什么呢?您,您……”他又拿出一個(gè)茄子來,這次倒真是個(gè)好茄子。又圓又嫩又輕。
“您什么呀!”我追問著,“你怎么連話也說不清楚了,這樣顛三倒四的。你今天有虧心事吧!”
“您!”他看著我的臉,“您說這年月,跑一天也賺不上一個(gè)人,家里怎辦——”他的臉陰暗下來,沒像往常抱怨生活太難時(shí)候那樣嘆息,而像要哭出來似的。
“您好心腸得好報(bào),您招招手多照應(yīng)我吧!奔一口吃,奔一口吃,指著賣這點(diǎn)兒錢哪行,我又不會像別人那樣多要價(jià)少給菜。”他知道我是看見他們玩的把戲了,這樣祈求著我。
我原沒有揭開他們的秘密的意思,那只是使我吃了一驚而已,我早就知道北京的老媽子會偷,我倒沒想到賣菜的會是窩主。
我想到我的女傭人,她也是她們的同伙吧!雖然她看上去很老實(shí)。可是老頭也是看上去很老實(shí)的人嗎?
我去看老頭,老頭正用希冀的眼睛瞧著我,我突然發(fā)覺他不但老而且非常疲慵瘦弱,他的臉露著可憐的菜色,那樣一張刻滿了皺紋的疲倦的臉。
“抓一口吃!”他重復(fù)在我耳邊說,“抓一口吃!難得很,抓……”。
我輕輕地笑了,我知道饑餓的滋味,假如我也有一個(gè)另外生財(cái)?shù)臋C(jī)會,恰恰可以補(bǔ)足這長年的不滿的肚子的時(shí)候,我也許會去偷的吧!
“你快拿菜吧!我要點(diǎn)棍扁豆,我沒看見什么,你放心吧!”我靜靜地說。
上述這篇一千六百余字的短文,可稱作“小小說”或“微型小說”。梅娘以白描式的筆法,將一位菜農(nóng)因生計(jì)所迫的種種窘狀生動勾勒出來。雖然菜農(nóng)與女傭有竊取主人財(cái)物的嫌疑,但文中以寬容的眼光待之,并有自白:“我知道饑餓的滋味,假如我也有一個(gè)另外生財(cái)?shù)臋C(jī)會,恰恰可以補(bǔ)足這長年的不滿的肚子的時(shí)候,我也許會去偷的吧!”這樣的推己及人的細(xì)膩真切之筆法,寫出了生活困苦的淪陷區(qū)的民生實(shí)情,也道出了人性本來的同情。
這篇“小小說”之后,還有對作者梅娘的“介紹詞”,稱“梅娘女士為時(shí)下華北最著名之女作家,其作品以情感豐富、技巧細(xì)膩見長,作品有《魚》、《小姐集》、《第二代》等等,均為一般人所愛讀”。確實(shí),僅以上述這篇“小小說”的內(nèi)容與筆法來看,這樣的“介紹詞”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