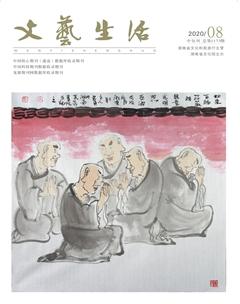從海派文學看上海的都市文化
摘要:海派文學作為我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文學流派,是在上海都市文化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具備著得天獨厚的歷史條件,展示了過去一個時代里殖民地下上海的生活百態,描繪了千姿百態的都市文明。從海派作家視角來管窺上海都市文明的面貌,能夠了解上一世紀都市文明的動感和快節奏,本文探討海派文學和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關系,以及上海文化帶給海派作家的影響。
關鍵詞:海派;海派文學;商業文明;海派作家;都市文化
中圖分類號:I71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20)23-0007-01?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3.004
一、引言
早期的海派充滿了商埠的殖民地氣息,西方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了當時的上海,海派文學作為現代商業發展的產物,與商業市場有著密切的聯系。海派產生于近代海禁后,上海在近代被開辟為商埠,這就肇始了近代的“夷場”、“洋場”文化和文學①。之后作為新興的海派文學,它是站在工業文明的基礎上看待中國的現實社會與物質文化,它與傳統的中國文學是有明顯區別的,但它的發展離不開上海的都市文化。
二、上海的商業文明
不同的時代,文學的發展有其不同的特點,繁榮的商品經濟必然會孕育出與之相適應的精神文明。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上海以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使之商業經濟與對外貿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后來西方資本主義的不斷入侵,上海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加快了上海的城市化進程。不到幾十年的時間里,上海一躍成為中國最大的商業化大都市,被稱為“東方的巴黎”。上海引進了西方的娛樂方式、電報、歌舞廳、酒吧等。隨之上海人在消費方式上打破了中國傳統社會大眾的消費習慣,這些行業的崛起見證了上海商業文明的發展。
每種文化的發展都會受到地域文化的影響,海派文學也不例外,上海的商業文明孕育了海派文學的誕生。作為連接外界的橋梁,上海以其獨特的文化承載能力接受來自西方的文化,并把西方的文化與中國本土的文化相融合。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必然會出現新的文化因子,這就是近代上海文化的轉型。這種文化充滿了商業氣息、享樂主義、快速消費等,我們把這種文化叫做海派文化,這種文化在近代的中國,唯上海獨有。也正是這種文化的催生,海派文學才能在近代中國得到快速發展。
三、海派作家筆下的上海書寫
海派文學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出現,海派文學有廣義與狹義之說,廣義上指鴛鴦蝴蝶派、新感覺派和后來的新海派作家組成,狹義上專指新感覺派作家群。海派作家群,以張資平,葉靈鳳、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蘇青、張愛玲等最具代表。他們以上海為創作題材,寫出了充滿性愛的都市文化、跳動的上海、愛與人性的上海等。他們筆下的上海呈現的是一種都市文明視域下城市與人的交織,這種交織或是人性的丑惡,或是欲望的宣泄,或是平民的歌舞,或是平民的文化心理等②。
譬如葉靈鳳是一個色調復雜的海派作家,因發表作品《女媧氏之遺孽》而成名。他前期的作品以感傷和濫情作為起點,打著反禁欲主義的旗幟去破除舊道德,但還是脫離不了對性愛的書寫。作品《浴》寫出了一位少女的自慰,逼真地展現了春情萌動下的性欲要求和情愛憧憬。除葉靈鳳之外,關于寫性愛小說的作家還有曾補,曾虛白和章克標等人。這些海派作家在享受現代物質文明和男女的性愛禁果時,有狂歡、感官刺激的解放,又有精神的分裂和迷惘。他們大膽地揭示人性的秘密、抒寫人性的欲望。在他們眼中上海就是一個充滿性渴望的都市,或許上海正是為他們提供現代情愛的試驗場,這為后起的新感覺派寫“性”提供了借鑒。
新感覺派小說上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的張資平,葉靈鳳等的性愛小說的余續,下起四十年代以張愛玲為代表的滬港市民傳奇,是海派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這時期的海派作家主要有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他們又稱為新感覺派。③他們第一次用現代人的眼光來書寫上海這個現代都市,以上海為創作題材顯示出濃厚的都市氣息。劉吶鷗眼中的上海是充滿“都市現代性”的,作品中對上海的書寫是五光十色的,又是混沌不清的,是黑暗莫測的、充滿活力的,是生命四射的,又是冷漠孤獨的,他的文學創作視角可稱為“都市風景線”。
穆時英被稱為“新感覺派的圣手”,他是真正意義上寫新式洋場的小說家。穆時英創造了心理象征的手法,表現上海都市的繁華,由金錢、性和罪惡所表現了都市的喧囂。他的作品寫街市、夜總會,以復雜的方式為我們呈現他眼中的上海。讓我們看到穆時英在經濟發展下,商業文明帶給人的雙重標準。他的作品《上海的孤步舞》《夜總會里的五個人》,將西方根植于都市文化的現代派文學形神兼備地移入上海這個東方大都會,并尋找現代的都市感覺。新感覺派的小說是海派發展中的重要一環,是它把文學中的“都市”地位提高了。小說中不僅有都市中的人,還有人心目中的都市④。
四十年代以張愛玲為代表的傾聽市聲、傾心都市日常生活,從細微之處體現都市精神的女作家,她筆下的上海,儼然已經成了普通市民的上海。她以普通市民的眼光書寫生活在上海都市文明里的女性,她以《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小說,在當時的上海文壇引起一片嘩然。張愛玲筆下的都市生活,不僅是歌舞廳、咖啡廳,都市還充滿了歌舞升平和浮光掠影。在都市文化下的精神世界,她說都市對于人來說既陌生又熟悉,但陌生大于熟悉,因為城市的一切只是短暫的。
總而言之,海派文學中的上海是動感、碎片化、快節奏的,它充滿了現代享樂主義,物質橫流是消費的顯現,社會生活用金錢來衡量,金錢就是一切。它又是充滿性愛的,燈紅酒綠的酒吧,咖啡廳等娛樂場所,里面充滿了性的宣泄、性的苦悶,人的靈魂已經變成肉體的快感,精神已經被物質所迷惑。若站在物質文明的立場上窺視上海的都市文化,海派作家以全新的視角為我們剖析了商業文明下的上海都市的發展現狀,我們可以通過作家的文學作品去了解上海都市文化的歷史嬗變。
四、上海都市下作家的創作
在文學發展領域里,有兩種文學創作觀念。一種是“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創作,其文學創作觀是純粹的感性思維,作家過分強調文學的審美功能而淡化文學的認知和教育功能,這種文學創作具有自我至上的人本主義色彩;另外一種是“為人生而藝術”的文學創作觀,其文學觀念的作家強調文學的認知和教育功能,淡化文學的審美功能,使得作家充滿了理性思維的人文主義精神。
對于海派文學的作家而言,筆者認為大部分作家是屬于前者的文學創作觀,海派作家的創作不像左翼作家那樣認為文學要為政治服務,或像魯迅一樣文學要反映民生疾苦,反映國民劣根性。而海派作家的文學創作是他們在上海都市生活的間接反映,他們創作的文學作品,可以為了迎合商業利益、市場消費的需要、迎合市民心理的需求進行藝術改造。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是有極大關系的,上海商業經濟的繁榮發展,必將會影響社會意識形態的轉變。與此同時,報刊出版業的發展為文學作品的商業化提供了傳播媒介,作家的文學創作受到商業化的影響,故呈現出商業化的特點。海派作家他們生活在上海商業文明下的都市圈層,他們的文學創作必然與商業文明緊密結合。
五、余論
上海文化富有多元性,都市品格只是其中之一,都市文化又是當時社會的客觀反映。對于海派文學的產生與發展,它是上海商業文明化下的產物,在中國文學史上扮演著一個首當其沖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文化角色。綜觀,無論我們從何視角來看待海派文學中的上海都市文明,其都有獨特的社會價值。
注釋:
①吳蘇陽.海派文學商業化的歷史源頭與現實基礎[J].社會科學輯刊,2009.
②吳福輝.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說[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③④錢理群,儒敏.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作者簡介:廖姜婷,西北民族大學本科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