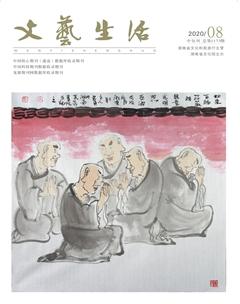試論出土文獻在學術研究中的價值
王文
摘要:出土文獻是文獻研究的重要資料,極具價值。本文通過舉例論證探尋出土文獻對《史記》研究的價值體現,發現出土文獻可以解決研究者存在的一些問題,為《史記》研究提供依據;糾正《史記》中的錯誤;擴充了原有的《史記》文獻資料范圍。
關鍵詞:出土文獻;文獻價值;《史記》;《編年記》
中圖分類號:R2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20)23-0011-01?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3.007
一、前言
在20世紀之前,學者們研究文獻典籍主要是利用傳世文獻之間互相佐證。有力的支撐材料大部分是由出土材料提供的;在文獻研究中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互考證也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學者們利用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①對《史記》②進行研究,研究成果頗多,如陳直的《史記新證》、韓兆琦的《史記箋證》等。
二、出土文獻為《史記》的研究提供的佐證
(一)名稱的來源時間
司馬遷的《史記》原本并不是“史記”,“史記”一詞本為古代歷史類典籍的統稱③。司馬遷的《史記》名稱產生時間也有多達數種說法。
根據《隸釋》④中記載的“秦東門”與《秦始皇本紀》中記載的三十五年秦始皇在東海胸界中立石,建立秦東門的事情相對應。據考證,在“東海廟碑”中記錄的就是司馬遷的“太史公書”,這是到目前為止關于《史記》的名稱的最早的一條文獻。陳直在其著作《太史公書名考》中也有相關記錄。⑤
(二)內容涉及體例
學界有不少學者對司馬遷將陳涉歸為世家而引發爭議。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中,記載了從秦始皇元年(前246年)到漢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星運行位置。在紀年表中,大概在秦二世的時期上記載“張楚”,其后為漢代的紀年。“張楚”在《刑德泄書的干支表》中得到了印證。出土文獻為學界爭論的陳涉收錄在世家的問題提供支撐材料。
三、出土文獻糾正《史記》中的謬誤
在《史記》的研究過程中,出土文獻可勘正《史記》中的錯誤。《編年記》⑥逐年記述了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6年)的事件,它可以勘正《史記》中的相關錯誤記載。
如《編年記》中記載秦于昭王十七年,攻打了垣、枳。而在《秦本紀》中記載秦十五年攻打垣后,將垣還魏,十八年攻垣。《秦本紀》里收錄的是在十六年,左更錯取輟及鄧。
《六國年表》中記載在十八年客卿錯攻擊魏國,《史記》中對攻打枳的時間記載有出入。出土文獻可以使學者確定秦十五年攻打垣后,十七年攻垣、枳,更正了原有的錯誤。
四、出土文獻擴充了《史記》的史料
《論語·八佾》中記載了孔子對于出土文獻的看法,可見,文獻典籍的匱乏讓研究者手足無措。而出土文獻是對傳世文獻的擴充補足。
《編年記》中詳細的記載秦在昭王六年攻打新城后,在八年歸還新城。而《秦本紀》只記載了昭王七年,奪取新城,與《編年記》中記錄的“昭王七年,新城被攻陷”是一致的,但沒記載后續。據白起為左庶長在十三年,帶兵攻打新城的記載可知,秦曾將把新城歸還給韓。《編年記》在這里補充了《史記》中遺落的記載。
五、結語
通過對比例證,可知出土文獻對學術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出土文獻對傳世文獻的佐證、糾正、擴充,可以幫助學者解決相關問題,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同時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古籍。如果我們充分利用出土文獻研究文獻學,定會有更多的新發現。
注釋:
①《古史新證》第一章《總論》中曰:“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②引用的《史記》都為中華書局1982年版。
③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七》:“古者,列國之史,俱稱史記。”
④原文為:“碑陰:闕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東門。闕事在《史記》。”(宋·洪釋《隸釋》中華書局1986)
⑤陳直《太史公書名考》用出土文獻東漢碑刻和傳世文獻相互佐證的“二重證據”。楊明照:“據此,以史記專名《史公書》今可考信者,宜以是碑為稱首。”
⑥《編年記》出自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秦簡牘合集·睡虎地簡牘》。
參考文獻:
[1]陳直.太史公書名考[J].文史哲,1956(06).
[2](清)浦起龍.史通通釋[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蘇安國.出土文獻在史記研究中的文獻學價值[J].渭南師范學院報,2010(06).
[4]?? 陳偉.秦簡牘合集·睡虎地簡牘[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