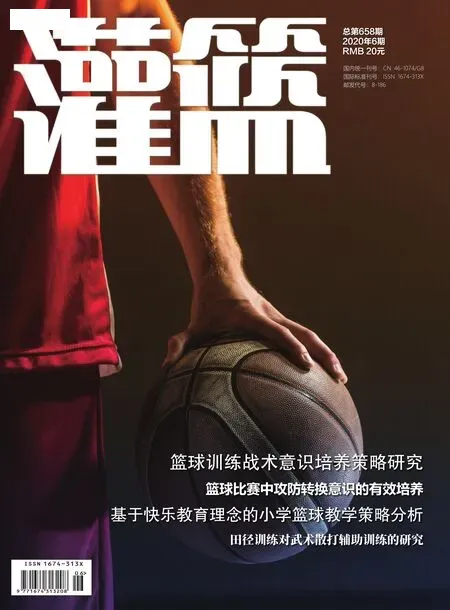菏澤民俗傳統體育文化促進鄉村社會善治研究
榮超 菏澤學院
一、傳統社會治理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機制
非正式制度存在是相對于正式制度來說的,而正式制度具有官方性特點,穩定性相對較強,當然它是從非正式制度隨著時間的變遷,逐漸發展而來的;而非正式制度來自民間,靈活性相對較強,是正式制度的基礎和淵源。“非正式制度通常包括傳統文化、行為準則、倫理道德、風俗習慣和慣例等,是人們在長期社會交往過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會認可的約定俗成、行為規范和行為準則,它構成了社會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1]
在傳統社會中,非正式制度中的運行機制有兩種。第一種就是傳統復制。其主要的特點就在于具有歷史悠久、穩定傳承。比如長老制、家長制、寨老制等,在傳統社會里都是世襲的傳統擁有權力方式、統治方式,言外之意,在傳統社會,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和自給性,社會成員的言談舉止,依據是遵守傳統慣例的準則,社會成員將傳統的遵循、天神和祖先的信奉等當作是權威,這種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道德教化的傳統思想,形成某一時期傳統社會價值觀的核心。比如禮儀禮俗、村規民約等,也有民俗文化、節日儀式,這些內化在人們的內心,反映在言談舉止之中。如云南“跳月節”(彝族阿細人)、云南“新年”(滄源佤族),形成了地方民俗文化的系統,又如:廣西“螞拐節”(河池壯族)、內蒙古“那達慕”(蒙古族)等,傳承至今,這些文化符號的系統,總的來看在發展中創新,在繼承中發揚,無論怎樣,總的趨勢是規制了地方區域風俗習慣、行為準則、道德倫理、價值觀念,逐漸成為有機統一、一脈相承的文化傳統。
第二,鄉村成員之間共同尊崇的輿論共識,這樣共識是潛移默化的。世世代代在一起生活的鄉村社會成員,相互之間是熟悉的,外出機會少,與外界人士接觸的少、難以受到外界的價值觀影響,因而有自身的生存、生活價值觀,成員之間按照慣例互相監督;存在于氏族內部的慣例及規則,由于時間長,約束力大,在成員之間發揮著重要的管控作用,人們為了生活生存嚴格地遵守著秩序,一旦有人破壞秩序,往往受到別人的譏笑、譴責等;面對怙惡不悛的成員,嚴重的話有時候被逐出氏族以外,或者被處死。總之,非正式制度來發揮作用,是傳統社會治理其中的一種方式,有獨具特色的家族制度,或者村規民約、也有道德倫理、風俗習慣等,通過這些來緩和、調節出現在人們之間糾紛和糾紛矛盾,社會治理的生命力得到強化。[2]
二、菏澤民俗體育文化在傳統社會的功能
民俗體育文化是指在特定場合,社會群體成員以此來鞏固自我、共同互動的一種儀式性活動,是在共同交流、溝通、協商的基礎上,彼此通過合作,利用肢體活動進行的一系列程序表演,是區域群體成員獨特的傳統“社會記憶”,有的也被稱為“文化記憶”,因此它具有地域性、周期性和節令慶典性特征。
(一)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增進鄉土社會凝聚力
坐落于山東省的西南部的菏澤市,地處黃河的下游,乃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區域面積以平原為主,地勢較為平坦,土層深厚,毋庸置疑的是以農業生產為主。人們的生活是一種集體群居生活,由于傳統社會的生活環境較為惡劣,以及個體自身的弱小,迫使群居的人們在耕作、狩獵、漁獵中必須加強協作,由此培養了他們思想和行動的一致性。
人們的生活中,也包括娛樂部分,眾多的娛樂方式中,作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俗體育,如舞龍、舞獅、賽龍舟、斗雞、斗羊活動等,這些項目活動是一種非正式關系結構體系,是靠血緣關系、鄉土關系聯絡起來的,傳承與發展是在特定的民俗體育文化場域里,稱為民俗體育儀式。從某個角度看,體現了一種身體行為、一種集體行為、一種組織關系,從體育精神文化的視角審視,是人們的協作與分享行為,是增進地方安全、穩固和團結的重要形式。
(二)培養和激勵文化認同情感,培育民族品質與精神
通常理解認同是人在特定情境下,把個人自身歸屬在某個社會群體。民俗體育文化在培養和激勵文化認同情感、培育民族品質與精神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菏澤包括較多的民俗體育項目,比如舞龍舞獅、馬術、飛刀、車技、爬桿、蹬技、飛人、魔術、走鋼絲等,人們通過有節律的互動實踐獲得情感,從而相互吸引、相互參與動作匹配的儀式活動中;很多項目還具有敲鑼打鼓的節奏,這種一致性表現在儀式上所身體動作之中,集體的心理共鳴被身體動作與節奏的一致性喚醒,使成員不斷在追求活力和激情,長此以往,人們的身心和鄉土社會得以完全融合,表明身體動作和鄉土社會道德秩序有機結合起來,不斷強化族群的價值觀、倫理觀,沉淀民俗體育文化記憶,這種對家族族群真實的認同感來引導自身的行為,人們共同的認識和行為,并最終形成了共同的秩序以及社會,也提高了社會成員的進取心和民族擔當,增強了對民族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從而為鄉土社會治理提供精神支撐。
(三)民俗體育文化的塑造與傳承,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民俗體育文化是社會文化的子系統,所蘊含的理想信念、精神追求、道德規范等體育精神文化,也是社會理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俗體育具有傳統性質的、一種身體性文化的表演活動,為了把鄉土文化和社會記憶再次展現,通常在節假日時間進行。如舞龍舞獅、賽龍舟、斗雞、斗羊、踩高蹺、竹馬、傳統武術、秋千、秧歌等,這些帶有歷史印記的行為和象征物的程序儀軌,展現了鄉土社會歷史的重現,也加深了對祖先、前輩的認識,強化了社會成員的歷史記憶。從另一個角度分析,通過身體文化的展示,也詮釋了農耕人民吃苦耐勞、樂觀向上、純樸穩健的民族特征和精神。這些在激發人們不懈奮斗、凝聚集體智慧和力量、推動社會前進方面,具有強大的動力,進而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四)強化言行舉止的規范性,遵守社會公共秩序
“儀式是人們的各種行為姿勢相對定型化的結果,用以形成和維護某種特定的社會關系”[3]。民俗體育文化也是一定的儀式活動,參與者運用身體語言展現的一系列的動作,譬如斗雞、斗羊、踩高蹺、竹馬、傳統武術、秋千、秧歌項目,通過手勢、舞蹈、歌唱、演奏、角色扮演等身體行為進行展示,表達了人們對民俗體育文化的一種崇敬,同時也讓他們獲得了心理上的慰藉以及精神上的安慰,也是對人類、前輩的行為舉止規范認可。人們的行為根據日常生活言談舉止與儀式場合的不同是存在差異的,為不斷提醒具有正確行為的意識而舉行儀式,每項民俗體育文化儀式活動,都包含一定的程序,許多的身體動作組成組成了這些程序,從而成為儀式上的行為動作和模式,以此重溫過去,感受民俗體育文化的傳統記憶,把自身的價值意義與鄉土社會具有統一性和一致性,約束與規范自身的行為,使之與鄉土社會區域保持社會秩序的同步性和一致性。
三、菏澤民俗傳統體育文化促進現代鄉村社會善治研究
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以及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菏澤部分農村民俗體育項目在人們生活演進的過程中,逐漸脫離了原有的形態,很多項目逐漸相互融合,向著多元化方向發展,逐漸具有多重社會功能和歷史價值。
(一)重塑民俗體育文化,強化鄉土社會中的認同感歸屬感
鄉土社會的善治,目的在于建設魂根同存的發展的鄉土社會。作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民俗體育文化,需要傳承和吸納優秀的民俗體育文化,體現民俗體育文化及內涵精神價值。菏澤在城鎮化社會建設過程中,通過重塑當地民俗體育文化,對傳統文化主題價值、鄉村精神以及鄉村信仰進行恢復與建構,不斷地推動鄉村振興,并形成獨具特色的鄉村傳統文化價值,對鄉村所擁有的獨特傳統文化的魅力進行延續與保存,滿足鄉土社會成員的文化精神生活、風俗習慣等需要,對凝聚人心也具有積極作用。如:武術、舞花棍、甩飛盤、跳皮筋、打雞毛球、拍紙片、蹦蹦球、老鷹抓小雞等。“將相關村落連接成一個社會互動共同體,密切了村落間的聯系,強化了地方的歸屬感和村落間的生活秩序,增強了地方文化及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和凝聚力,成為當地人精神生活世界的基本邏輯”[4]。也利于建設一個具有和諧、文明有歸屬安全感的現代化鄉土社會。
(二)彰顯了人與社會和諧共存的倫理
在市場經濟日益成熟的今天,鄉土社會無疑也充滿了各種競爭,但民眾仍遵循平和的氣度維系鄉村社會的穩定發展。在鄉村社會里,民俗體育是集群性的體育文化社會活動,人與人的體育文化互動交流,無形中形成了一種穩定的人際關系,如民間的舞龍舞獅、劃龍舟等習俗,參與活動的每個人,情感上不由自主地實現了群體認同,不同民眾成員也相應凝聚成一個集體。民俗體育活動中,人們之間的這種頻繁交往,形成了民眾之間友誼的情感基礎,并通過這種民俗行為方式,將鄉土的人情暖意世代傳承,滋潤人們的內心靈魂,這種行為是無須思考的,是一種行為的自覺。同時,由于鄉土社會的族群關系多樣化,并且相互交錯,民俗體育項目活動也常被鄰村之間、異族村落之間相互效仿,也為生存架起了支撐的橋梁,充分詮釋了“求同存異、異中求存”的價值觀。[5]對民眾心中的血緣以及地緣情結進行了固化,讓他們一起來維護所在村落所擁有的地位以及聲望,通過民俗體育方式的交流,形成一種穩定的鄉土共存,維系在一個和諧共存的鄉村環境中。
(三)利于新時代鄉村家園建設,促進民俗體育產業發展
無論在什么時代,各級政府、社會團體、民間組織等,在體育發展方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不過它們分別起的作用側重不同而已,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民俗體育文化活動的發展和傳承,民間組織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些民間組織的成員大多是德高望重的家族長輩組成,代代相傳,其形式有老人協會、傳承協會、武術世家等,他們在組織活動中滲透社會經驗、倫理道德,進一步增強社會體育資源的利用率,促進鄉村社會的合作、協作能力,提升了民間組織的運作效率。不僅為民俗體育文化的傳播提供相對穩定的文化氛圍以及良好的社會環境,而且還能在此基礎上進行民俗體育文化旅游運作機制,形成鄉村獨特的體育傳統文化產業,如武術協會、武術社團、武術俱樂部、武術影視、武術競賽表演、武術服裝、武術器材設備等。在鄉村振興背景下,要進一步加強民俗體育組織建設、體育文化建設,將鄉村社會發展與本村特色民俗體育文化結合起來,為推動鄉村文化發展繁榮貢獻力量,營造“一村一民俗體育文化品牌”的新時代鄉村家園。[6]
(四)運用民俗體育文化活動,加強公民道德建設
道德是公民精神的支持,維系社會發展的底線。在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人們忙于生活、工作,菏澤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人們之間的交流、交往相對減少。好多傳統的民俗文化逐漸流失或者淡化,要維系村民道德修養,建設公民道德,必須有文化的公共平臺與空間,因此重拾、重構民俗體育文化,是對鄉村社會“善治”有效途徑之一,運用其中有益的部分,并與現代體育文化相融合發展,共同推動公民道德建設。如武術、舞龍舞獅、健身氣功、太極推手等民俗體育文化活動,不僅說明了人們對社會活動積極參與的意識,也加深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且還能夠緩和鄰里關系、減少鄰里的糾紛和對抗等,化解城鎮化發展中所帶來不和諧、不文明、不健康的行為,從而構筑鄉村核心價值,形成鄉村的文化認同感。從宏觀上看,民俗體育文化中所體現的道德準則,譬如人們之間能夠互愛互敬、團結協作、互相寬容、和諧相處等道德準則,這些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或者一脈相通的。[7]
四、結論
民俗體育文化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在促進由單向社會管理,向社會管理與治理轉型過程中,也能夠發揮事半功倍的效能,是構建菏澤和諧農村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要發揮菏澤民俗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治理功能,形成當代菏澤鄉村社會治理形態,將區域鄉村治理協調、持續互動起來,把促進社會善治實現作為最終目標,進而達到菏澤鄉村社會更加和諧、健康。
把菏澤民俗體育文化“粘合劑”的作用在鄉村社會治理實施中充分體現,增多了鄉村社會治理途徑,緩解與正式制度、調節社會治理出現的矛盾,村民自治進程得以推動,多元主體、多元文化參與以及民主、互動的善治局面快速形成,這正是當代中國鄉村社會善治的現實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