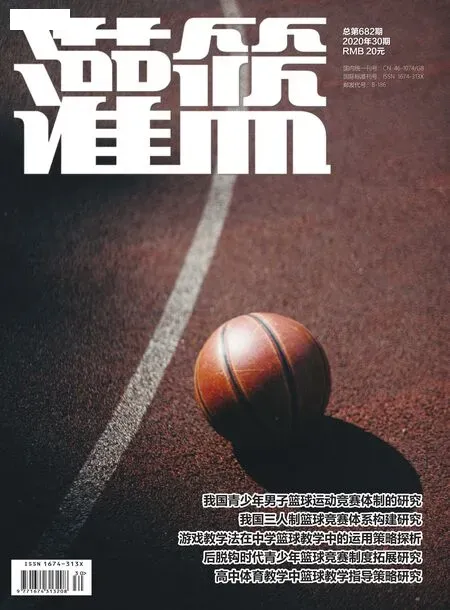在全球化背景下對銅仁龍舟運動發展的再思考
楊博 貴州師范大學
銅仁是聯結我國中東部地區與西南地區的必經之地,因而享有“黔東門戶”之稱。銅仁也因其秀美的山水風貌與獨特的人文風情而自古就有“桃源銅仁”的美譽。自明朝初年始,龍舟運動就在這樣的一片土地上生根發芽、流傳至今并依然深受人們的喜愛,在傳承至今的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龍舟文化。銅仁市也由此成為貴州省重點開展龍舟競賽的城市之一。
在全球化、現代化的時代背景下,銅仁龍舟運動也走向了世界,開展得越來越紅火。在每一年的銅仁龍舟大賽上,都會舉行隆重的開幕儀式,一些知名的歌唱藝術家都會參加演出;同時在賽程中也增加了國際組與女子組這些傳統龍舟賽中所沒有的組別,其專業化和職業化的程度都在不斷地提高,也因為銅仁龍舟賽的競爭的激烈性與觀賞的精彩性,每年銅仁舉辦龍舟大賽時,銅仁市都會出現萬人空巷,人人爭先恐后去現場觀看比賽的現象。然而,作為我國民族傳統體育運動項目的代表之一的“賽龍舟”出現這樣一種現象,是否就有利于該項目的保護與發展呢?
在全球化與現代化不斷普及的今天,開展得紅紅火火的銅仁龍舟運動,在以西方競技體育文化的沖擊下,能夠得到進一步的創新性發展?還是在大浪淘沙的現實中逐步流逝?這些都將是銅仁龍舟運動所必需思考的問題。“新事物”終將取代“舊事物”,沒有一成不變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能夠經得起變化著的時代的淘洗,所以對銅仁龍舟運動進行再思考,并對銅仁龍舟文化進行文化重構是極為有意義和有必要的。
一、銅仁龍舟運動的活動過程
每年的五月初五幾乎成了銅仁當地人民除了大年三十外最為期盼的日子,端午節也成了銅仁當地除了春節外最熱鬧的節日。或許是因為銅仁當地人民太喜愛龍舟,參與現場的意識十分強烈,每年的這一天銅仁市區都會萬人空巷,十萬、二十萬、甚至是三十余萬當地及外來觀眾齊聚銅仁錦江兩畔,觀看這一年一度的龍舟大賽。比賽不會因天氣原因而中斷,這一天不論是烈日炎炎,還是驟降暴雨,比賽都不會停止,現場的觀眾也會停留在原地觀賞比賽,并為比賽吶喊助威,其狂熱與癡迷程度不亞于一場NBA總決賽現場的球迷。
傳統的銅仁龍舟大賽,在正式比賽的前一天,全體參賽隊員連同他們的龍舟都要集中在岸邊,一起舉行隆重的祭龍點睛儀式,該儀式由當地道行最高的法師主持,供奉三牲,誦讀祭文,祈求風調雨順、春華秋實。祭龍儀式完畢后,會請出當地的幾位德高望重的長老或地方官員或外來官員,為參賽龍舟進行點睛儀式。點睛儀式結束后,隆重的游江活動就將開始,賽事的總指揮會乘著快艇在隊伍前方開道,參賽龍舟跟隨其后,每條龍舟上都會插著寫有“風調雨順”“旗開得勝”“五谷豐登”等吉語的一面面旌旗,它們一條接著一條地沿江劃行。
象征著比賽正式開始的發令槍響后,伴隨著鑼聲與鼓聲,原本平靜的江面瞬間波濤起伏,一條條蛟龍翻騰而出,舟行如飛、百舸爭流,隊員們齊心協力、奮勇爭先,場面震撼、壯觀。在勝利的角逐上,銅仁龍舟運動曾經同樣有著別具一格的特色。20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銅仁龍舟賽中,領先的龍舟要從落后龍舟的船頭繞過,才算勝出,這種決勝方式被稱為“團鍋蓋”[1]。最終獲勝的船隊一邊揮舞著獎旗,一邊放著鞭炮,沿著江邊上下游行,同時在船頭還會有一人做倒立表演,以慶祝自己獲得了勝利。這種決勝方式或許是因為要求太高、太過繁瑣,并沒有在現代的龍舟大賽中繼續沿用。
據說,過去銅仁本地的龍舟比賽結束后,有一個非常獨特的民族習俗叫作“蛟龍搶紅”[1],其過程是把豬膀胱揉搓后染成紅色,塞進油紙包裹的禮金,將其吹成直徑約20公分的氣泡,并綁在一只水鴨子身上;然后在水鴨子脖子上輕割一刀,抹上食鹽,最后將鴨子和“氣泡”一起丟進水里,讓各龍舟隊的隊員們下水爭搶。其過程就有些類似于現代競技運動中的水球運動,只是“球”是一只“活球”。受傷的鴨子時起時浮,因傷口的疼痛而游得比平時更快;豬膀胱水泡也因接觸水之后變得奇滑無比,即使有隊員搶到手了,也會不時脫手滑出而又落入他人之手。這對隊員的游泳技術、耐力及“搶球”技巧充滿了挑戰。數百名“蛟龍”在水里翻騰追逐,其場面充滿著濃郁的民族特色,龍舟賽的趣味性和娛樂性也由此而得到了大大的增加,銅仁龍舟運動中的“搶鴨子”習俗也由此一直流傳至今。
二、銅仁龍舟運動的起源及文化特色
(一)銅仁龍舟運動的起源
公元前278年農歷五月初五,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在自己的國家政事混亂,屢為強秦欺凌;自己也因遭貴族排擠誹謗的情況下,被先后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終日悲憤憂郁;最終在楚國郢都被秦軍攻破后,自投于汨羅江。后來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愛國詩人,在每年農歷五月初五這天,人們用包粽子、賽龍舟等活動來紀念他,龍舟文化的起源也就由此而形成。在當時銅仁位于楚國黔中郡腹地,受楚國文化影響極深,所以龍舟文化也自然而然的流傳到了銅仁。然而,銅仁龍舟運動卻是真正開始于明朝初年。經幾百年傳承至今,銅仁龍舟文化不僅積奠了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群眾基礎,而且在流傳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獨具特色的龍舟文化。
(二)銅仁龍舟運動的文化特色
自古以來,龍對中國人來說是祥瑞的象征,是掌管行云布雨的神;對于銅仁人來說,龍同樣是當地最崇敬的神靈。雖然銅仁的賽龍舟同樣與紀念詩人屈原有關,但歷代的銅仁當地居民卻賦予了賽龍舟新的含義,使得賽龍舟的傳說更加的深入人心,源遠流長。
賽龍舟,在銅仁當地俗稱為“扒龍船”,曾作為生活在這里的侗家人的一種祭祀活動,當地農村有句俗語叫“端午不下,犁耙高掛”[2],意思是如果端午不下雨,這一年就會有旱災,一次旱災也就必然會影響到莊稼的生長,而導致人們沒有收成。因此,每年當人們完成了春耕之后,就會開始祭祀神龍,祈求這一年風調雨順。時值端午節,每村每寨殺豬宰羊,沿著銅仁錦江這一條銅仁地區的母親河,開展祭祀活動。這也就形成了銅仁龍舟比賽前,所必需進行的祭龍儀式。
每逢端午,人們便會把擱置了一年的龍船“漆”一遍,并在錦江水面上開始操練起來,到了五月初五端午節的那一天,銅仁各地人民的龍船便會聚集在銅仁城中的銅巖下,等待比賽的開始。在這一天,銅仁各城鄉常常是萬人空巷,紛紛齊聚錦江兩岸觀看這一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比賽。這一原生態民族文化由銅仁兒女一代代傳承著、發揚著,并在全球化、現代化不斷推進、普及的今天,愈發迸發出絢麗的光芒。
三、全球化背景下銅仁龍舟運動的發展現狀
在進入21世紀以來,在全球化與現代化迅速推行的今天,銅仁龍舟運動也做出了許許多多順應時代潮流的改變與發展,其不僅僅成了龍舟賽事中的精品賽事之一,而且成功帶動了銅仁地區的旅游發展,以及地區各行各業的招商引資,幾乎成了銅仁旅游乃至銅仁地區的一張名片。
(一)成為龍舟運動賽事中的精品賽事
自2008年6月,銅仁市承辦了“中國銅仁國際龍舟邀請賽”以來,中國龍舟公開賽、中國傳統龍舟大賽、中華龍舟大賽等多項大型賽龍舟賽事活動都連續在銅仁舉行。龍舟這一地方民俗活動,如今已成了在全國乃至世界都具有相當影響力的體育賽事,其影響力之大、范圍之廣,在當今的民族傳統體育運動中實為罕見,就以2017年銅仁龍舟大賽來說,其參賽隊伍就多達99支,4000余名龍舟健兒在錦江上競逐高低[3]。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參賽隊伍中,有相當部分的女子選手,要知道銅仁以往的龍舟賽事是只有男性才可以參加的,這或許也是銅仁龍舟順應全球化時代與我國改革開放潮流的發展,同時這些女子龍舟隊們也成了銅仁龍舟賽的另一大看點。女子龍舟隊的參賽隊員們穿著五顏六色的民族服裝下到江面上,又是一番別有風趣的景象,巾幗不讓須眉,這些女性參賽隊員們的氣勢與比賽精彩程度一點也不輸給男隊。
(二)成為銅仁的一張旅游名片
“賽龍舟”是一張極具號召力的人文旅游名片,通過“賽龍舟”可以較為全面地向游客展示銅仁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使游客可以親身感受到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和情感交流,從而大大提升游客們的旅游感受。銅仁也借用這一資源優勢,形成了系列旅游精品線,打造銅仁良好的旅游形象,使“銅仁龍舟”為銅仁帶來更好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
(三)經濟效益明顯且發展快速
舉辦龍舟大賽,旨在進一步弘揚民族文化,傳承這一民族體育運動,并在這一過程中搭建對外交流的橋梁,增進了解與合作。銅仁市借助龍舟大賽這一特色活動,展現了銅仁的民族文化特色,加大了對外宣傳的力度,并給參賽選手和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借助“龍舟”這一特色活動,銅仁的旅游業和招商引資等取得了顯著的效果。2008年引進項目41個,實施項目簽約資金13億余元;在2011年成功簽約項目23個,簽約金額達107.43億元;在2012年、2013年招商引資連續超過百億元。[4]
雖然,通過“賽龍舟”成功促進了銅仁市文化旅游產業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從數據上來看,近年來“銅仁龍舟”的經濟效益是在下降的,也表示著銅仁龍舟運動逐漸成了人們眼中“習以為常”的民族傳統體育運動之一,似乎充滿特色的銅仁龍舟運動也逐漸變得“平庸”,所以在全球化不斷推行,日新月異的今天,銅仁龍舟運動實現文化重構,將會是必然趨勢。
四、銅仁龍舟運動文化重構的必然性
文化重構,即文化的重新構建,指對已有文化現象的再加工,再創造,也是人們對已有文化現象的再認知。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重構,是指在與它文化的交往中,通過整合外來的體育文化因子,即加工、融合、創造,使其成為本民族體育文化的一部分,從而建構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過程。[5]
在今天,全球化與現代化早已是無處不在,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全球化與現代化已成為必然。銅仁龍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卷入這一浪潮之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傳統的銅仁龍舟賽前增加了文藝演出,以及在賽中一部分龍舟隊所使用的劃槳動作與以往的民族式劃法不同,而與現代競技運動中的賽艇運動的劃槳動作極其類似。那么在這樣一個趨勢下,銅仁龍舟運動它是否會存在被現代競技運動所取代,致使這一優秀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嚴重影響,逐步走向邊緣化、常態化,甚至消亡的風險。
可以肯定的是,這一風險是絕對存在的。一則,是全球化與現代化的時代潮流,早已傳遍全球,各種各樣的外來文化一一呈現在人們眼前,而人們在外來文化與民族傳統文化的選擇中,似乎對外來文化的接受程度更高。二則,這種民族傳統體育運動逐步脫離自身本來文化,逐步趨于常態的例子已經發生,梁勤超等學者在研究中指出:在政府的推動下,貴州赤水河流域的“獨竹漂”通過現代性轉型,完成了從民間傳承到民運會表演與競賽的華麗轉身,其出場是功利性的工具理性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給其帶來了新生和繁榮,并由此催生了向外推廣普及的發展愿景。但在全國民運會之后,其發展漸歸常態,對外推廣普及的愿望也趨于落空[6]。也許,同屬貴州省的“獨竹漂”運動的例子,不會在銅仁龍舟運動上發生,但這著實是銅仁龍舟運動需要進行文化重構的警鐘。
在另一方面,全球化與現代化,也同樣是銅仁龍舟運動得以進一步發展的契機。銅仁龍舟運動是否可以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浪潮中,在保留自身獨特的民族文化不改變的前提下,借鑒并融入現代化體育文化與其他民族傳統體育運動中的優秀文化呢?在現代競技運動的影響下,銅仁龍舟大賽的競爭性是否會增加,從而使比賽的激烈性和觀賞性增加呢?
這些都是銅仁龍舟運動在當下所必需面臨的問題,將本民族傳統的優秀體育文化擴展到世界舞臺,放眼未來,才能在現代化背景保持生命力與活力,不被全球化與現代化的浪潮掀翻[7]。現下全球化和現代化沖擊已經成為對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及文化的勢不可擋的挑戰,我們要做的不是任由其發展,而是迎難而上,文化重構成為一種必然。
五、全球化背景下銅仁龍舟運動的文化重構
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重構過程中,一般存在三種心態。第一種是對外來文化持全面否定態度的自我中心心態;第二種是對外來文化全面接受的簡單趨同心態;第三種是對外來文化有選擇的接受,使其不斷滋養自身的揚棄心態。被外文化牽著鼻子走,丟失掉自己本來文化的文化重組模式勢必是脆弱的,這種完全模仿型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很容易在外來體育文化面前頹敗,最終完全萎縮。而完全以自我為中心,對外來文化持全面否定態度,孤立保守發展民族傳統體育也同樣會走不久遠。唯有對外來文化進行有選擇性的揚棄,使其優秀的文化部分得以稱為民族傳統體育自身文化的養料,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得到創新性發展,才能使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重構適應外來的體育文化沖擊,使自身的體育文化得到發展和前進。其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國近代體育史上的熱火朝天的“土、洋體育之爭”。
(一)認清自身,做好揚棄,并有選擇的吸收外來文化
銅仁龍舟文化重構的過程必然是長期的,不能以自我為中心,一味否定、排斥外來文化,也不能沒有底線的與其他文化簡單趨同,喪失自己的本來樣貌。所以銅仁龍舟這一文化主體一定要擺正自己的方向,在這一文化重構的過程中既要保持好自身的本味,也要有選擇性的吸收外來的優秀文化,更好地延續與發展。
“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自身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對其文化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且必須在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主體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下對本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進行挖掘、改造和重構,以促進其現代化。[8]“文化自覺”是銅仁龍舟文化重構的基礎,即當本民族的人充分認識本民族龍舟文化的發展時,才能醒悟、反思和創造本民族龍舟文化,才能對本民族的文化進行反省整頓,才能取長補短促進龍舟文化的發展。這一點在當下的銅仁龍舟運動中其實已經有所體現,以往的傳統龍舟比賽中,存在“團鍋蓋”這樣的決勝方式,而現在的銅仁龍舟運動的競爭性和激烈性已經明顯提高,勝負往往只在毫厘之間,所以“團鍋蓋”這一雖然可以體現技藝性和觀賞性的決勝方式也就自然而然的裁汰掉了。
對外來文化有選擇的吸收也是銅仁龍舟運動迫在眉睫的趨勢,因為現下的銅仁龍舟比賽已逐漸成了人們眼中的“平常之物”,雖然對這一民族傳統體育運動喜聞樂見并參與其中的人群同樣不在少數,但如果再不做出創新,銅仁龍舟運動趨于平常的局面將不可避免。所以銅仁龍舟既要接納新的龍舟文化所需要的文化因素,也要吸收現代體育文化元素,給龍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二)與現代體育文化融合,但需要注意運動競爭性和普通大眾的關系
從“傳統”到“揚棄”再到“現代化”“全球化”,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現代體育文化之間的融合是必然的,但是現代體育文化中“更高、更快、更強”的競技體育理念也會影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而這一“優勝劣淘”的進化論理念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中全面推廣,那么其結果就是這些多姿多彩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人文情懷被逐漸消減,最終被淘汰而進入歷史的塵埃。[9]
與“更高、更快、更強”這一理念直接掛鉤的就是現代競技運動的“競爭性”,而在包括龍舟比賽在內的各項賽事中,最能提高比賽“競爭性”的因素,必然是賽事獎金。在前文中提到,以銅仁龍舟為紐帶,銅仁的旅游業與招商引資的增長幾乎都是幾十上百個億,可想而知銅仁龍舟大賽的賽事獎金有多高。同樣的情況在我國其他的龍舟賽事中也同樣存在,如2016年中華龍舟大賽總決賽,職業男子組最終冠軍的獎金設置高達11萬元,其他組別的冠軍為5萬元,總決賽總獎金共計100萬元,2017年中華龍舟大賽萬寧站總獎金80萬元……[10]在高額獎金的利誘下,參賽隊員也將會日趨專業化、職業化。雖然這樣的情形可以使龍舟賽事的競爭性與觀賞性提高,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提上賽事的關注度,但是民族傳統體育運動屬于田野,屬于河流,屬于普通民眾。如果銅仁龍舟的參賽選手大多變成了專業或職業選手,那么普通民眾的參與度也就會自然降低了,久而久之這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特色也就流逝了。
(三)需得認清自身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現代體育文化存在的差距
雖然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多姿多彩、引人注目,但是在當今 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還需實事求是的認識到,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現代體育文化是存在差距的。當今,現代競技體育文化無論從物質層面、精神層面、行為層面、還是制度層面都是更加完備的體育文化,必須承認現代競技體育文化的主體地位,以及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較為落后的事實。當然,承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落后地位并不意味著,就是要對其進行全面的否定,而是要在現代競技體育文化的影響下,進行借鑒,并取長補短,豐富自身。只有這樣,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才能更好地去適應在全球化與現代化時代背景下的發展。對待正處于時代浪潮中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既不應采取簡單的復古式保護,執著于對“原生態”的追求;也不應人為創造出一些“取悅他者”的偽民族體育,忽略傳統文化的主體地位。[10]
六、結語
全球化與現代化已是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尤其是在現代競技體育運動為主體的背景下,給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總的來說,在全球化與現代化迅速普及,且日新月異的今天,銅仁龍舟運動能夠保持現下的參與度和影響力,并在保持自身文化本味幾乎不改變的情況下成為銅仁旅游的一名片,帶動銅仁經濟發展,已經是實屬難得了。但是正如前文所說,一種文化一成不變,只會在歷史的長河中流逝,銅仁龍舟運動要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只有文化重構,在自身文化特色的基礎上對外來文化進行有選擇的吸收,經過不斷重組、整合和融合,才能實現自身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浪潮中生存和發展下去。雖然說,當今的體育大文化是以西方競技體育文化為主的,但是沒有人希望這些寶貴的、極具特色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在西方競技體育文化的擠壓下逐步走向消亡。
正如學者李凌所說,或許只有當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持有群體的文化覺醒進而成為民族傳統體育進行文化重構與文化再生產的內在動力,與加強傳承主體參與的制度化建設成為民族傳統體育進行文化重構與文化再生產的外部推力完全形成合力時,才能有效推動傳統文化資源進行創新性發展,為包括民族傳統體育在內的民族復興與文化繁榮做出貢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