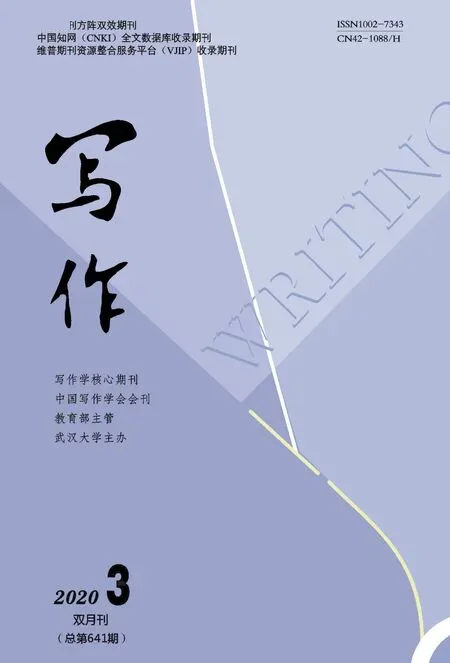文體與風(fēng)格:語言藝術(shù)
——亞里士多德散文寫作理論研究(二)
陳 韜 戴紅賢
如何有效地運用語言是亞里士多德寫作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語言表達(dá)技巧、表達(dá)效果等問題。在他看來,語言的運用能力雖說與個體天賦有一定的關(guān)系,但修辭術(shù)作為一種技藝的學(xué)科,修辭能力可通過教學(xué)而增強,修辭水平可由刻苦練習(xí)而提高。《修辭學(xué)》作為寫作教材,對語言藝術(shù)的分析很具體、細(xì)致,相關(guān)內(nèi)容比較集中地呈現(xiàn)了古希臘時期語言藝術(shù)的面貌,成為西方修辭學(xué)和風(fēng)格理論的重要古典資源,其中不少內(nèi)容至今仍有學(xué)術(shù)活力。
亞里士多德既研究了詩歌語言,也研究了散文語言,這兩種語言藝術(shù)有相通的地方。不過,由于詩歌是模仿藝術(shù),散文是說服藝術(shù),這種文體差異使得二者的語言運用存在諸多不同。本文重點闡釋亞里士多德《修辭學(xué)》所探究的散文語言藝術(shù),兼及《詩學(xué)》的相關(guān)內(nèi)容。亞里士多德所論述的散文語言藝術(shù)被概括為“修辭五藝”①[古羅馬]西塞羅:《論公共演講的理論》,《西塞羅全集·修辭學(xué)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頁。之“文體(style)”②羅念生先生將亞里士多德《修辭學(xué)》相關(guān)部分內(nèi)容翻譯為“風(fēng)格”;顏一先生翻譯為“用語藝術(shù)”;王曉朝翻譯西塞羅的修辭學(xué)時采用了“文體”概念,他又解釋說:“本書在涉及演講詞時譯為文體,在涉及演講時譯為風(fēng)格。”西塞羅則自己解釋說:“文體就是針對構(gòu)思出來的事情采用恰當(dāng)?shù)脑~句”,詳見[古羅馬]西塞羅:《西塞羅全集·修辭學(xué)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5、第3頁。可見這一部分屬于語言運用問題。由于“風(fēng)格”“文體”兩個概念與用語問題有關(guān),但它們還有其他的含義,故本文傾向于使用顏一先生的說法,即語言運用藝術(shù)。。本文擬從用語原則、修辭手法和行文特點這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明晰而適宜:散文用語的原則
亞里士多德在其風(fēng)格理論中開宗明義,指出散文風(fēng)格應(yīng)當(dāng)明晰而適宜。“風(fēng)格的美可以確定為明晰(證明是,一篇演說要是意思不清楚,就不能起到它應(yīng)起的作用),既不能流于平凡,也不能提得太高,而應(yīng)求其適合(詩的風(fēng)格也許不平凡,但不適用于散文)。”①[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91、301、315、83、315-316、87、301、92、301-302頁。明晰而適宜是散文用語的基本原則,同時也是散文和詩歌語言藝術(shù)需要共同遵循的原則,因為亞里士多德在《詩學(xué)》中也強調(diào)“風(fēng)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②[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91、301、315、83、315-316、87、301、92、301-302頁。,并且指出即便是在詩里,有時也會為了需要把風(fēng)格壓低或抬高一些,以使其符合語境③[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91、301、315、83、315-316、87、301、92、301-302頁。。
為落實明晰而適宜的修辭原則,對語言的研究就十分必要。在亞里士多德看來,語言的正確性是風(fēng)格的基礎(chǔ)④[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91、301、315、83、315-316、87、301、92、301-302頁。,而語法是用語正確的保障。古希臘重視語言的準(zhǔn)確性,語法學(xué)說創(chuàng)建甚早。普羅泰戈拉首先采用科學(xué)方法研究希臘語言,分析語法;普羅狄科斯則研究了同義字的區(qū)別和用法。亞里士多德繼承了這些學(xué)說,認(rèn)為語言運用包括語音、連接詞、名詞、動詞、詞形變化、語句⑤[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91、301、315、83、315-316、87、301、92、301-302頁。,又把詞劃分為連接詞、名詞和動詞等類型,初步探究了詞類的語法功能。其中名詞(廣義)包括名詞(狹義)、人稱代詞、指示代詞、疑問代詞(關(guān)系代詞為連接詞)、形容詞、冠詞和不定式動詞,后面六種均可作名詞使用。在詞類研究的基礎(chǔ)上,亞里士多德總結(jié)出實現(xiàn)用語正確的五個方法:(1)善用聯(lián)系詞(起聯(lián)系作用的詞,包括小品詞、前置詞和連接詞);(2)使用本名而不使用屬名,如用具體名詞“狗”,不用抽象名詞“動物”;(3)不用含糊的詞句,除非有意把話說得籠統(tǒng),就像預(yù)言者說含糊的話、政治家說迂回的話那樣;(4)正確區(qū)分名詞的性,把名詞區(qū)分為男性、女性和無生物;(5)正確地說出多數(shù)、少數(shù)(即雙數(shù))和單數(shù)⑥[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91、301、315、83、315-316、87、301、92、301-302頁。。
亞里士多德還把詞語分為普通字和奇字兩大類,并討論其使用規(guī)律。普通字指大家都使用的字,一般為日常語言中的詞匯;奇字包括借用字、隱喻字、裝飾字、新創(chuàng)字、衍體字、縮體字和變體字⑦[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91、301、315、83、315-316、87、301、92、301-302頁。。普通字雖然表意清晰,但它會讓文章風(fēng)格平淡無奇⑧[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91、301、315、83、315-316、87、301、92、301-302頁。;奇字則能使文章顯得不平凡。亞里士多德說:“最能使風(fēng)格既明白清晰而又不流于平淡無奇的字,是衍體字和變體字;它們因為和普通字有所不同而顯得奇異,所以能使風(fēng)格不致流于平凡,同時因為和普通字有相同之處,所以又能使風(fēng)格顯得明白清晰。”⑨[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頁。這里面的衍體字是指母音變長樂的字或音綴增加了的字;而一個字如果其中一部分是保留下來的,另一部分是創(chuàng)新的,這個字就是變體字。詳見本書第88頁。不過,雖然奇字可以使文章遣詞造句不平淡,但他也指出“每一種奇字的使用都要有分寸”,濫用奇字會顯得荒唐⑩[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91、301、315、83、315-316、87、301、92、301-302頁。。因此,寫作藝術(shù)應(yīng)當(dāng)混合使用普通字和奇字,詞語的恰當(dāng)選擇能夠使散文符合明晰而適宜的原則。
對詞語選擇的研究勢必觸及文體問題,散文用語的恰當(dāng)與否和文體關(guān)系密切。盡管同樣遵循明晰而適宜的原則,但在詞語的具體使用上,詩歌和散文仍然存在一些差異。對于詩歌而言,各種奇字可以使詩歌風(fēng)格富于裝飾意味而不流于平凡,詞匯上的變化可以使其風(fēng)格顯得更加莊嚴(yán),異鄉(xiāng)情調(diào)的語言使人感到愉快等等。但是,只有普通字、本義字和隱喻字才適合散文的用語,名詞中的奇字、雙字復(fù)合詞、新造字應(yīng)當(dāng)少用。原因在于,散文屬于公共說理藝術(shù),題材主要來源于現(xiàn)實或歷史,藝術(shù)目的在于說服;而詩歌屬于模仿的藝術(shù),它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這樣才能使觀眾身臨其境,并打動他們,而且詩歌往往取材于神話和英雄傳說,因此,各種奇字可以讓詩的風(fēng)格不平凡,實現(xiàn)詩歌的藝術(shù)功能[11][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91、301、315、83、315-316、87、301、92、301-302頁。。
亞里士多德批評了當(dāng)時演講詞修辭的諸多不當(dāng)現(xiàn)象,認(rèn)為根本原因在于沒有區(qū)分詩歌和散文的文體。例如高爾期亞所說的“‘詩丐似的’奉承者”,阿爾喀達(dá)馬斯所說的“充滿熱情的靈魂和‘火色的’面貌”等,這些雙字復(fù)合詞使演講詞表達(dá)含有詩意,因此不夠妥當(dāng)。呂科佛戎稱薛西斯為“人‘怪’”,阿爾喀達(dá)馬斯說“在他的意志的強烈憤怒上‘磨礪過的’”等,這種奇字使用也模糊了詩與散文的語用差別。各種修飾詞語使用不當(dāng)也是早期演講詞的普遍問題,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散文的修飾詞語使用要節(jié)制。例如,阿爾喀達(dá)馬斯使用修飾語就過度了,他不說“汗”而說“潮濕的汗”,不說“赴伊斯特摩斯競技會”而說“赴伊斯特摩斯的泛希臘集會”,不說“法律”而說“城邦的君王——法律”,等等。亞里士多德說阿爾喀達(dá)馬斯的修飾詞語用得“那樣地密、那樣地長和那樣地顯眼”,累詞贅字引起了含混,破壞了行文的明晰。
在散文內(nèi)部,不同文體的語言使用也有不同要求。政治演說和訴訟演說寫作要適合口頭的朗誦,而典禮演說辭屬于“筆寫的演說辭”,主要供人閱讀,很少用來朗讀①[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9-300頁,注釋9。。因此,在寫作時應(yīng)當(dāng)注意這種口頭表達(dá)和書面表達(dá)的用語差異。亞里士多德指出,筆寫文章的語言表達(dá)最精確;不過,法庭演說的用語也比較精確,尤其是面對單個審判者發(fā)表的演講,用語相對更精確一些;而政治演說的風(fēng)格完全像一幅濃淡色調(diào)的風(fēng)景畫:群眾越多,景色越遠(yuǎn),所以在這種風(fēng)格和圖畫里,過于精確是浪費筆墨,反而效果糟糕②[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374、100、320、302頁。。
亞里士多德反復(fù)強調(diào)散文的明晰適宜原則,其落腳點是在增強說服力上。既然“由演說提供的或然式證明分三種。第一種是由演說者的性格造成的,第二種是由使聽者處于某種心情而造成的,第三種是由演說本身有所證明或似乎有所證明而造成的”③[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頁。這里說的“性格”指演講者的道德品質(zhì),如果聽眾認(rèn)為演講者是好人,就會傾向于相信他的話。,那么明晰而適宜的表達(dá)無非是對這三種證明的追求。在風(fēng)格層面,修辭主要是訴諸前兩種說服手段,即性格和情感。亞里士多德特別強調(diào)散文語言要表現(xiàn)性格,他說:“有證明提出,我們的語言就一邊表現(xiàn)性格,一邊發(fā)揮證明的效力;沒有修辭式推論提出,我們的語言就只表現(xiàn)性格。一個有德行的人必須自己是一個好人,比表現(xiàn)自己是一個說話精明的人更為適宜。”④[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374、100、320、302頁。而詩人“應(yīng)盡量少用自己的身份說話,否則就不是模仿者了。因為劇中的人物各具有自己的性格,沒有一個劇中人物不具有自己的特殊的性格”⑤[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374、100、320、302頁。,這是說服藝術(shù)和模仿藝術(shù)的根本差別使然。至于情感,也是散文寫作需要表達(dá)的,因此應(yīng)該注意語言的情感色彩。例如,只要談到暴行就應(yīng)使用憤怒的語氣;談到大不敬或丑惡的行為就應(yīng)使用厭惡和慎重的語氣;談到可贊頌的事物,就應(yīng)使用欣賞的口吻;談到可憐憫的事物就應(yīng)使用憂傷的口吻⑥[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374、100、320、302頁。。聽眾總是對動感情的演說者表示同樣的感受,在法庭演說中要特別注意通過用語來表達(dá)情感。
總而言之,明晰而適宜是散文修辭的原則,它建立在正確的語言使用基礎(chǔ)之上,受到文體的約束,并通過表現(xiàn)性格與情感實現(xiàn)說服聽者的修辭目的。
二、隱喻和夸張:實現(xiàn)風(fēng)格的修辭手法
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散文的修辭手法比韻文少,所以尤其要重視隱喻。他說:“隱喻字在詩里和散文里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們應(yīng)該在散文里對隱喻字多下苦功,因為散文的手法比韻文少一些。隱喻字最能使風(fēng)格顯得明晰,令人喜愛,并且使風(fēng)格帶上異鄉(xiāng)情調(diào)。”⑦[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374、100、320、302頁。使用隱喻有三個原則:合適;相似;生動。
合適,即在寫作中尋求更合適的字。想恭維人,就從同一類隱喻字中選取比較美好的事物;想挖苦人,則選取比較丑陋事物。例如,乞丐之乞討與祭司之祈禱,在懇請的方式上相類似,在使用隱喻時,可以說乞討者在祈禱,或祈禱者在乞討。隱喻適宜還包括隱喻之美感,應(yīng)當(dāng)從具有聲音之美或意義之美、或能引起視覺或其他感官美感的事物中取來。例如,“玫瑰色手指的曙光女神”的比喻勝于“紫色手指的曙光女神”,最糟糕的說法是“紅色手指的曙光女神”①[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42、309、341、87-88、312、305、319、304、316頁。。
相似。隱喻應(yīng)當(dāng)從有關(guān)系的事物中取來,關(guān)系不能太顯著,然而也不能太遠(yuǎn),因為一個人要有敏銳的眼光才能從相差很遠(yuǎn)的事物中看出它們的相似之點②[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42、309、341、87-88、312、305、319、304、316頁。。因此不要從相差太遠(yuǎn)的事物中取得隱喻字,最好從同類事物中取得隱喻字。如高爾吉亞所說的“淺綠色的、沒有血色的事件”、“你種下了羞恥,收獲了災(zāi)難”,阿爾喀達(dá)馬斯稱哲學(xué)為“法律的堡壘”,稱《奧德賽》為“人類生活的明鏡”,還說“沒有把這種玩偶帶進(jìn)詩里”,這些隱喻關(guān)系扯得太遠(yuǎn),意思含混不清,因此,這類話都沒有說服力③[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42、309、341、87-88、312、305、319、304、316頁。。
生動。措詞要能使事物呈現(xiàn)在眼前,也能受歡迎,因為我們應(yīng)當(dāng)看得更清楚的是正在發(fā)生的事情,而不是將來要發(fā)生的事情。隱喻就是這樣一種措辭。使事物活現(xiàn)在眼前的要訣是借用表示活動的詞,例如“正處在開花的盛年”“希臘人雙腳開動了”;把無生命之物說成有生命之物,例如“那莽撞的石頭又滾下平原”“那支箭飛了回來”“那支箭急于要飛向”“那些長槍栽進(jìn)了土地,依然想吃飽肉”“那槍尖急于要殺人,刺穿了他的胸膛”等等。據(jù)亞里士多德說,荷馬就非常擅長使用這樣的技巧④[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42、309、341、87-88、312、305、319、304、316頁。。
除上述三原則外,亞里士多德還認(rèn)為,類比式隱喻最受人歡迎。他將隱喻分為四種:(1)借屬作種,例如,“我們的船停此”,不用種概念“泊”,而用屬概念“停”;(2)借種作屬,例如,“俄底修斯曾做萬件勇敢的事”,“萬”是“多”的一種,借用代表“多”;(3)借種作種,例如,“用銅刀吸出血來”,借“吸”作“割”,二者都是“取”的方式;(4)類同字的借用,例如,老年之于生命,有如黃昏之于白日,因此可稱黃昏為白日的老年,稱老年為生命的黃昏⑤[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42、309、341、87-88、312、305、319、304、316頁。。第四種即為類比式隱喻,其結(jié)構(gòu)最復(fù)雜,表意豐富又委婉,故最受歡迎。類比式隱喻可以使讀者有所領(lǐng)悟,也就是能為人們提供看待事物的新視角、新方法。亞里士多德說:“語言是表現(xiàn)思想的,能夠使我們把握新的思想的語言,是最為我們所喜歡的語言。陌生的詞匯使我們困惱,不易理解;平常的詞匯又不外老生常談,不能增加新的東西。而隱喻卻可以使我們最好地獲得某些新鮮的東西。當(dāng)詩人用‘枯萎的樹干’來比喻老年,他使用了‘失去了青春’這樣一個兩方面都共有的概念來給我們表達(dá)了一種新的思想,新的事實。詩人的明喻,如果用得好,也可以產(chǎn)生同樣的效果。”⑥譯文見束定芳:《亞里士多德與隱喻研究》,《外語研究》1996年第1期。
亞里士多德也提到了明喻,但他認(rèn)為明喻與隱喻的差別很小;明喻在散文里也有用處,但是應(yīng)當(dāng)少用一些,因為它們帶有詩意⑦[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42、309、341、87-88、312、305、319、304、316頁。。
除了比喻之外,夸張也是一種值得重視的修辭手法。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夸張,是表達(dá)事情比較大或比較小、比較美或比較丑的效果的方法。詩歌可以寫極丑或極美的事物,而散文一般以表達(dá)符合人情事理的實際情況為主,不過,無論是好事還是壞事,都還存在比較好或比較壞的屬性。故文章在證明事情屬實之后,即確定了事情性質(zhì)之后,就應(yīng)該對事情加以夸大或縮小,以打動聽者的情感,激發(fā)他們的憐憫、憤怒、憎恨、羨慕等情緒。論辯散文的這種特殊表達(dá)內(nèi)容,在語言上往往是借助附加詞、指小詞、聯(lián)系詞、重復(fù)、描寫等方法實現(xiàn)的。
附加詞指性質(zhì)名詞,包括性質(zhì)形容詞。附加詞必須與所形容的名詞相適合⑧[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42、309、341、87-88、312、305、319、304、316頁。。附加詞可以著眼于壞的或丑的意義,例如“殺母者”和“他父親的報仇人”;也可以指出事物所沒有的性質(zhì),例如“有一座多風(fēng)的小山”“無琴的曲調(diào)”等等。這種方法可以同時用于事物的好的或壞的方面,視描寫的需要而定⑨[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42、309、341、87-88、312、305、319、304、316頁。。
指小詞使事物顯得沒那么壞,或者沒那么好,例如,小金幣、小斗篷、小嘲弄、小病痛等等⑩[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42、309、341、87-88、312、305、319、304、316頁。。附加詞和指小詞都用來描述和形容事物,使用時要小心謹(jǐn)慎,掌握分寸。
聯(lián)系詞指起聯(lián)系作用的詞,包括小品詞、前置詞和現(xiàn)代語法所說的連接詞[11][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42、309、341、87-88、312、305、319、304、316頁。。亞里士多德很重視聯(lián)系詞的運用。聯(lián)系詞在書面表達(dá)里不能省略,因為省略影響清晰;但它們有時可以在口頭表達(dá)里省略,因為重點突出,有利于聽眾的理解。不過,省略聯(lián)系詞的句子應(yīng)該說得有變化,有差異,例如“我去到那里;我碰見他;我懇求他”,要能顯示出是三件事情,甚至說出三件事情之間的逐步加強的意味①[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350、318、324、84、324、325-327、328頁。。聯(lián)系詞可以把許多事情融合成一件,那么去掉聯(lián)系詞后,就能獲得相反的效果:即把一件事情分成許多件。所以,省略聯(lián)系詞,可以起到夸大事情的表達(dá)效果。
重復(fù)的詞語在書面表達(dá)里應(yīng)當(dāng)省略,因為顯得冗余累贅。不過也有例外,比如在敘述一個人的事跡的時候,可以通過重復(fù)他的名字來進(jìn)行夸大,荷馬的《伊利亞特》就曾使用這種辦法。重復(fù)的詞語在口頭表達(dá)里卻往往不需要省略,還要會利用,不過,在念重復(fù)的詞語時,一定要改變音調(diào),起到強調(diào)的效果,例如,“偷了你們的是他,騙了你們的是他,終于要出賣你們的是他”②[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350、318、324、84、324、325-327、328頁。。
描寫比稱名更有分量。例如,不說“圓”,而說“邊上各點距離中心等長的平面”;不過,稱名比描寫更簡明。表現(xiàn)丑惡或不體面的事物也可以采用此方法。因此,在需要強調(diào)時使用描寫,需要分散受眾的注意力時,采用稱名的方法③[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350、318、324、84、324、325-327、328頁。。
隱喻和夸張經(jīng)常聯(lián)合使用。亞里士多德甚至說受歡迎的夸張語也是隱喻,例如“他的腿彎彎曲曲像芹菜”,不過,夸張語言適合年輕人或發(fā)怒的人,但不適宜老年人,因為前者常用夸張表達(dá)激烈的情感,但老年人應(yīng)該性格平和,性情穩(wěn)重。
除了上述的用語原則和修辭手法外,《修辭學(xué)》還分析了散文特有的行文特點,那就是節(jié)奏和語氣。
三、節(jié)奏與語氣:散文行文的特點
亞里士多德說:“散文的形式不應(yīng)當(dāng)有格律,也不應(yīng)當(dāng)沒有節(jié)奏。”④[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350、318、324、84、324、325-327、328頁。論辯散文的語言藝術(shù)追求說服的力量,但是格律使語言表達(dá)不自然,做作的語言會削弱內(nèi)容的可信度;格律還會分散聽眾的注意力,因為聽眾會期待格律的重復(fù)出現(xiàn),因此,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散文不應(yīng)當(dāng)有格律。但散文應(yīng)該有節(jié)奏,因為沒有節(jié)奏就沒有限制,沒有限制的話語既不討人喜歡,也不好懂。簡言之,亞里士多德試圖在散文所受的行文約束方面取得一個平衡,即不過分受約束(沒有格律,包括節(jié)奏也不應(yīng)太嚴(yán)格),但也不完全自由。
格律由若干音步組成,每個音步內(nèi)長音綴和短音綴的數(shù)目和安排是相同的;節(jié)奏則由限制語言形式的數(shù)目(指音綴和音步的數(shù)目)構(gòu)成。節(jié)奏與散文句子的寫作有關(guān),語句為含義的合成音,語句中的名詞和動詞含有意義,而連接詞則不含意義,這就為節(jié)奏的調(diào)整留下了空間。有兩種方法使語句成為一個整體:一是使它表示一個事物,如人是陸棲兩腳動物;二是用連接詞把許多語句連接起來構(gòu)成篇章⑤[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350、318、324、84、324、325-327、328頁。。
亞里士多德分析了各種節(jié)奏的特點。英雄格是史詩的節(jié)奏,最為莊嚴(yán)但不適合談話;短長格為多數(shù)人的語言節(jié)奏,長短格則是一種輕快的節(jié)奏,這二者比例相同,對于演講來說都過于輕佻;派安格介于兩者之間,最適合演講,因為只有它無法構(gòu)成格律⑥[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350、318、324、84、324、325-327、328頁。,換言之就是最符合散文風(fēng)格。派安格節(jié)奏由一個長音節(jié)和三個短音節(jié)組成,長音節(jié)可以置于句首句末,或其他位置,比較靈活,它也因此不能構(gòu)成格律。亞里士多德主張句子的結(jié)尾應(yīng)當(dāng)用節(jié)奏表明,而不應(yīng)由抄寫人標(biāo)明或用記號標(biāo)明,例如在句首第一個字下面劃橫線表示上一個句子在該字之前結(jié)束⑦[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350、318、324、84、324、325-327、328頁。。
在討論節(jié)奏時,亞里士多德重點強調(diào)了各種句法。他認(rèn)為,散文的句法必須像散漫的酒神頌?zāi)菢哟B起來,用聯(lián)系詞聯(lián)系起來,或者像舊詩人的回舞歌那樣回旋⑧[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350、318、324、84、324、325-327、328頁。。串聯(lián)體是直線式的,各子句之間沒有緊密的聯(lián)系;回旋體是轉(zhuǎn)圈式的,各子句之間有密切聯(lián)系。這樣就形成了串連句和環(huán)形句這兩種句式。串連句指本身沒有結(jié)尾,要等事情說完了才告結(jié)束的句子,它屬于直線式松散的句型;環(huán)形句本身有頭尾,有易于掌握的長度的句子,它屬于圓圈式的緊湊的句型。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串連句由于沒有限制而不討人喜歡,所以他重點闡述了環(huán)形句的寫作。
環(huán)形句可分為復(fù)雜和簡單兩種,前者由幾個子句組成,后者由一個子句構(gòu)成。環(huán)形句不應(yīng)太短,也不宜太長。表現(xiàn)力較強的是對立式環(huán)形句,即不同子句內(nèi)對立的詞相并列,或同一字管住兩個對立詞。例如:“他們讓留在家里的人和跟隨他們的人都嘗到了甜頭,因為他們給后者弄到了比在家中更多的土地,給前者在家中留下了充足的土地。”又如有人在法庭上這樣控告佩托拉俄斯和呂科富隆:“這些人在家中出賣了你們,在這里又想收買你們。”對立式環(huán)形句討人喜歡,易于理解,并具有三段論意味,因為把對立的意思放在一起,可以顯示其中的謬誤,成為一種否定式三段論①[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81、367、368、369、379頁。。
此外,還有平衡句、諧音句等句式。平衡句的兩個子句等長;諧音句的兩個子句的尾音綴彼此相似,相似的尾音綴或者在句頭,或者在句尾。平衡句和諧音句類似中國的對仗句和押韻句,具有形式整齊、語音和諧之美。有些環(huán)形句把對立子句、平衡子句和諧音子句集于一體,句子寫得非常漂亮精彩。據(jù)說亞里士多德早期的修辭學(xué)著作《忒俄得克忒亞》列舉了許多優(yōu)美的環(huán)形句,看來他專門研究過句子的寫作。
在散文行文中,除了節(jié)奏,語氣也非常值得關(guān)注,因為當(dāng)時的散文主要還是面向演講,語氣的不同對演講效果影響很大。亞里士多德把語氣視為語言運用研究的一個專門項目,涉及命令、祈求、陳述、恐嚇、發(fā)問、回答等語氣問題。他在《詩學(xué)》中說“一個詩人懂不懂這些語氣,不致引起對于他的詩的藝術(shù)值得嚴(yán)肅看待的指責(zé)”,因此這門學(xué)問“屬于演說藝術(shù)與這門藝術(shù)的專家的研究范圍”②[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81、367、368、369、379頁。。《修辭學(xué)》重點闡釋了其中的陳述、發(fā)問、回答以及譏笑等問題。
陳述就是說明事情,提出問題。陳述的速度,重要的不是快慢的問題,而是是否適中。所謂適中,是指用簡短的話就把事情講清楚。例如,使聽眾相信事情發(fā)生了,造成了傷害或構(gòu)成了罪行,或足夠表明事情是如你想造成的印象那么重大就行了③[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81、367、368、369、379頁。。陳述有一些技巧。例如,在陳述中,把過去發(fā)生的事情轉(zhuǎn)化為正在發(fā)生的事情來講述,可以起到引起憐憫或憤慨的情感效果。例如《奧德賽》中,奧德賽反用了這一技巧,他在向妻子講述自己的故事時采用過去式,免得佩涅羅佩聽了心里難受④[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70頁,注釋6。。陳述還應(yīng)當(dāng)表現(xiàn)修辭藝術(shù),如陳述時,應(yīng)當(dāng)順便講一些足以表現(xiàn)作者美德的話。例如:“我總是勸他為人要正直,不要撇下他的兒女。”或者講一些表現(xiàn)對方的邪惡的話,如:“可是他回答道,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能生一些別的兒女。”或者順便講一些使陪審員喜歡的話⑤[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81、367、368、369、379頁。。這些說話技巧旨在影響聽眾的判斷。陳述應(yīng)當(dāng)表現(xiàn)性格,使聽眾認(rèn)為你是這樣的人,例如,“我愿意這樣,我寧肯這樣;盡管無利可圖,還是這樣好”。前兩句話表示有德行;后兩句話表示有見識。有德行的人追求高尚的事情;有見識的人追求有益的事情。因此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應(yīng)該使用前者。陳述還要能表現(xiàn)情感,例如,“他瞪了我一眼就走了”,“他嗤之以鼻,揮舞著拳頭”,這種話有說服力⑥[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81、367、368、369、379頁。。
發(fā)問和回答既是語氣問題,又是辯證問題。從辯證角度來看,它們非常復(fù)雜,亞里士多德的分析學(xué)說里有大量的討論,這里不予贅述,僅從語氣角度來了解發(fā)問和回答。問句則包括反問句和疑問句,二者的差別在于,前者是結(jié)論,后者是問題⑦[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81、367、368、369、379頁。。
亞里士多德總結(jié)了四種發(fā)問的最好時機。在發(fā)問時,意欲提問的人首先應(yīng)當(dāng)找到進(jìn)行抨擊的根據(jù);其次,提出問題并逐個整理;最后,把這些問題推向被質(zhì)疑者⑧[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工具論》,張留華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09頁。。發(fā)問的根本旨趣在于通過提問來支配論證過程,以使回答者由其論題必然地說出最悖理的答案來①[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工具論》,張留華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18、420-421、418頁。。因此,不應(yīng)當(dāng)在推出了結(jié)論之后再發(fā)問,也不應(yīng)用發(fā)問的方式提出結(jié)論,除非真理在自己這一邊。
亞里士多德指出,對于不同的問題,有相應(yīng)的合適的回答方法。例如,如果問題是大家同意且又與論證不相關(guān)的,回答者就應(yīng)承認(rèn)和同意它;如果是大家不同意且又不與論證相關(guān),回答者也應(yīng)承認(rèn),但是,說明大家不同意這個問題,以防頭腦簡單的人草率對待;如果它與論證相關(guān)且又被大家同意,回答者就應(yīng)說明,雖然它是大家同意的,但是離起點太近,并且,如果要認(rèn)可它,設(shè)定的命題就會被破壞;若它與論證相關(guān),卻不是大家所同意的公理,回答者就應(yīng)當(dāng)指出,如果確立這個,就會導(dǎo)致極其蠢笨的結(jié)果,等等②[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工具論》,張留華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18、420-421、418頁。。總的回答原則是,指出結(jié)論的不成立或悖理似乎不是由他自己負(fù)責(zé),而是在于對方的論題;因為最初那個不應(yīng)該設(shè)定的論題可能是某一類錯誤,而且對方在設(shè)定之后又沒能適當(dāng)?shù)鼐S護它③[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工具論》,張留華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18、420-421、418頁。。
關(guān)于譏笑,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在論戰(zhàn)中似乎有一些用處”,正如高爾期亞所說:應(yīng)當(dāng)用戲謔擾亂對方的正經(jīng),用正經(jīng)壓住對方的戲謔。《詩學(xué)》中提到了譏笑的內(nèi)容,即滑稽的事物是某種不引起痛苦或傷害的錯誤或丑陋④[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80、301、頁。。但要注意有些譏笑并不適宜“自由人”使用,比如嘲弄比打諢更符合自由人身份⑤[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80、301、頁。。這種差異的背后體現(xiàn)的是演講姿態(tài)問題,“自由人”(即城邦公民,或者說,男性奴隸主)不需要取悅別人,因此不適宜使用打諢方式。
四、余論
總之,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修辭術(shù)作為一種技藝的學(xué)科,需要使用各種技巧以增強語言表達(dá)的效果,不過,各種言說技巧必須不露痕跡,使文章語言顯得自然而不矯揉造作,因為話說得自然才有說服力,而矯揉造作只會適得其反;從日常語言中選擇詞匯,能把手法巧妙地遮掩起來⑥[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80、301、頁。。這是亞里士多德對于修辭風(fēng)格的基本態(tài)度。
亞里士多德的散文語言學(xué)說繼承了古希臘修辭學(xué)成果,例如,高爾期亞(前483?—前436?)甚至認(rèn)為修辭是最重要的問題,主張采用詩的辭藻,講究對偶⑦[古希臘]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詩學(xué)〉〈修辭學(xué)〉》,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頁,注釋11。。柏拉圖(前427—前347)認(rèn)為基本用語應(yīng)該界定,詞類應(yīng)該恰當(dāng)安排⑧從萊庭等編著:《西方修辭學(xué)》,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頁。。伊索格拉底主張散文應(yīng)當(dāng)有節(jié)奏,強調(diào)隱喻字的重要性,重視字音的和諧,主張環(huán)形句,認(rèn)為風(fēng)格應(yīng)當(dāng)與題材和時機相適合⑨羅念生:《古希臘羅馬文學(xu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0頁。。據(jù)西塞羅講,亞里士多德收集了古希臘修辭學(xué)的早期著作,精心考察了每一位作家提出來的規(guī)則,用清晰的語言把它們寫下來,并努力解釋困難部分,在吸引力和簡潔方面超越了原著。因此,熟悉了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也就熟悉了其他人的修辭學(xué)⑩[古羅馬]西塞羅:《西塞羅全集·修辭學(xué)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202頁。。
亞里士多德散文風(fēng)格理論影響深遠(yuǎn)。一般認(rèn)為,中世紀(jì)修辭學(xué)更多是西塞羅的,然而西塞羅風(fēng)格理論本就源于亞里士多德。在這一前提下,我們就容易理解為何波愛修斯(480—524)如此熱衷于翻譯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文藝復(fù)興時期,“西塞羅派”(又稱傳統(tǒng)派)繼續(xù)發(fā)揚亞里士多德—西塞羅一脈的傳統(tǒng);拉米斯(1515—1572)不僅像亞里士多德一樣對辭格和演講格外關(guān)注,更重要的是他把構(gòu)思取材和謀篇布局歸于邏輯學(xué)之下,修辭學(xué)被縮小為對文體風(fēng)格和演講技巧的研究。拉米斯的“修辭學(xué)革命”深刻影響了其身后直到17世紀(jì)的學(xué)術(shù)格局,對修辭學(xué)整體來說,它作為一門學(xué)科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文體風(fēng)格研究卻得到了高度重視。不過,隨著英語文學(xué)、法語文學(xué)、意大利語文學(xué)等歐洲民族文學(xué)的興起,文體風(fēng)格研究也顯示出偏重文學(xué)的態(tài)勢。當(dāng)然,亞里士多德兼言文學(xué)和修辭學(xué)風(fēng)格理論的遺風(fēng)仍在修辭學(xué)論著中時隱時現(xiàn)。威克納格(1806—1869)的《詩學(xué)·修辭學(xué)·風(fēng)格論》說:“散文正好跟詩相反,是詩的對立面,它是內(nèi)心知覺的語言表現(xiàn);這種內(nèi)心知覺以智力為基礎(chǔ),以真實為客觀材料。……散文是這樣一種形式,在那里,智力作為一種科學(xué)好奇心的器官記錄并表現(xiàn)它本身的經(jīng)驗和意見,換言之,它本身的知識,其目的是通過這種再現(xiàn)使得在別人心中開始活躍起來的智力可以獲取同樣的知識。”“風(fēng)格是語言的表現(xiàn)形態(tài)。”①[德]威克納格:《詩學(xué)·修辭學(xué)·風(fēng)格論》,王元化:《王元化集 卷二 文藝評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06、315頁。T.E.休姆(1883—1917)在《語言及風(fēng)格筆記》中強調(diào)詩歌語言再現(xiàn)形象的能力,認(rèn)為它必須“具體到可以把帽子掛在上面”;與之相對,散文語言則只是籌碼,是代數(shù)符號,“不作任何想象就能得出結(jié)論”,這一觀點被后來的新批評派所繼承②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306頁。。威克納格和休姆對散文語言藝術(shù)的理解與亞里士多德的散文語言學(xué)說存在一定的出入。不過,他們對詩歌和散文這兩種語言藝術(shù)特征的比較分析,與亞里士多德用《詩學(xué)》《修辭學(xué)》探究文體風(fēng)格的方式頗為接近。
作為古希臘修辭學(xué)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開創(chuàng)了系統(tǒng)的修辭學(xué)理論,孕育了不少學(xué)科的理論胚芽,例如其中的情感訴求涉及的聽眾及其心理對現(xiàn)代傳播學(xué)和心理學(xué)有很大的啟發(fā)。與此類似,亞里士多德的散文文體學(xué)說也成為西方語言學(xué)、風(fēng)格學(xué)的源頭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