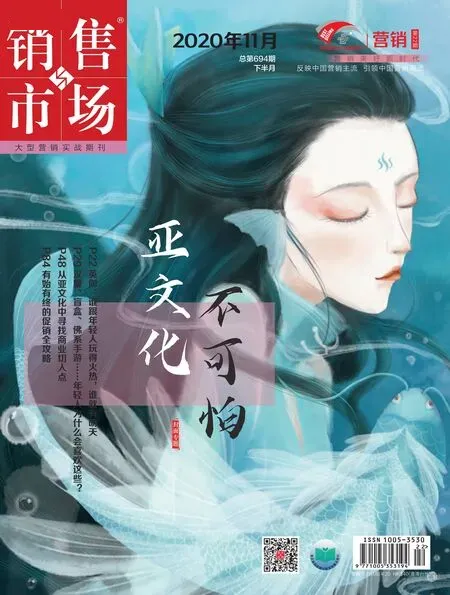是誰控制了我們的生活
文/張翼帆
有種說法,當今世界的五大科技巨頭是微軟、蘋果、谷歌、臉書和亞馬遜,并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市場競爭可能不會終結谷歌、臉書和亞馬遜在各自核心市場的霸主地位。那么,這對我們會有麻煩嗎?
平臺在扮演上帝嗎?
“曾經有一個IT 屆的大拿,在2005年左右就說過總有一天,如果連谷歌也搜不到某個東西,那這個東西就是不存在的。世界有可能會變成這樣,這是一個預言。但是這個預言到了2020年變成了什么?總有一天,如果說一樣東西是不被算法推薦的,那它就是不存在的。”這是一位導演在談及“短視頻是否會對長視頻產生沖擊”時說的話。
比如,當我某天打開一個短視頻平臺,刷到一個影視劇推薦的視頻,因為我喜歡里面的某位演員,所以就點進去看了,那可能以后我只要一打開這個視頻軟件,都會給我大量推送一些影視劇推薦的視頻。久而久之,我的信息接觸面就只剩下影視劇短視頻這一個接觸點了。再如,疫情期間,有消息誤傳雙黃連口服液可以起到有效防疫的作用,一時間各大信息平臺都在推送這則消息,很多人就信以為真,然后就出現了各大藥店雙黃連被搶購一空的情形,最終當然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人力去辟謠,要知道,這是一件很浪費資源的事情。
這就是推送對我們思考能力的傷害。無論是大眾根據自身喜好去獲取信息,還是因為平臺算法接觸外界信息,都會營造出一個回音壁,在這個回音壁里,你很容易會認為你的喜好就是全世界。實際上,我們獲取信息的結構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久而久之就會處于蠶繭一般的狹隘空間,我們每一個個體都是與世隔絕的孤立者。這也就是所謂的“信息繭房”。
此外,由于互聯網的便捷性和共享性,現在大量的信息內容生產方式都是UGC、PGC 或是PUGC,那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信息選擇了我們,而不是我們選擇的信息。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也就是說,對大家思考能力的傷害,關鍵不在某個平臺本身,而是一些算法對大家思考能力的傷害,這才是我們需要擔心的問題。
平臺應該扮演什么角色?
那平臺究竟是什么?它又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
“平臺”越來越多地被用于指代這樣的混合型實體:將數字技術作為一種產品或服務的使用者或消費者與供應者之間的接口。平臺與以下實體有一些共同特征:協調供應鏈的傳統商業;連接較小的供應商與市場的中間商或批發商;連接終端用戶之間的網絡;供個人供應商和買家見面交易的場所或市場。
長期以來,一些金融機構、金融組織也可以被稱為平臺。傳統集市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一個為賣家、買家見面交易提供場所的平臺。更近一些的例子包括能夠讓消費者和零售商完成交易的支付卡網絡,或者是為項目開發人員和電腦用戶協調技術標準和合作條款的操作系統。還有一些形式非常新穎,例如“共享經濟”的對等平臺。
平臺是解決經濟組織基本問題的一種新方式,即在缺乏完整信息的情況下協調供求關系。傳統市場利用的是地點或時間,平臺則利用技術來改進協調效果。參與者不需要在同一地點參與配置,而且交易雙方無須同時進行。
這樣看來,平臺更像是個場所,是連接信息提供者和信息接收者的紐帶,信息接收者是有自由選擇信息的權利的。而且,如今早已不是“贏家通吃”的時代,競爭公司如果能在更大的新市場打造資深的主導地位,那么將有極大的可能超越目前這些科技巨頭。
善用平臺的力量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新聞行業固有的模式已經發生徹底改變,人們在工作和社交上,已經越來越依賴于數字媒體。不論是臉書,還是微信,或是抖音等短視頻平臺,今天在世界范圍內的活躍用戶數都達到了不容忽視的程度,網絡社交媒體平臺已經成為很多用戶獲取信息的重要來源。
同時,平臺所具有的信息易獲取性和共享性的優勢,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一旦某個信息輸入端口存在問題,隨之將會產生大規模的、錯誤的數字化信息。這個“虛假信息”,將會瞬間被數不清的用戶接收到,并可能作為判斷依據,而隨之也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如網絡暴力等。
但是,我們也應該明白,“劍的鋒利,不在于劍,而在于使用他的人”。數字化媒體的便捷性,不是我們濫用信息的理由,數字化媒體市場還需要更多制度上的完善與發展,以及第三方的監督。無論是信息的提供者還是信息的接受者,都應該善用平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