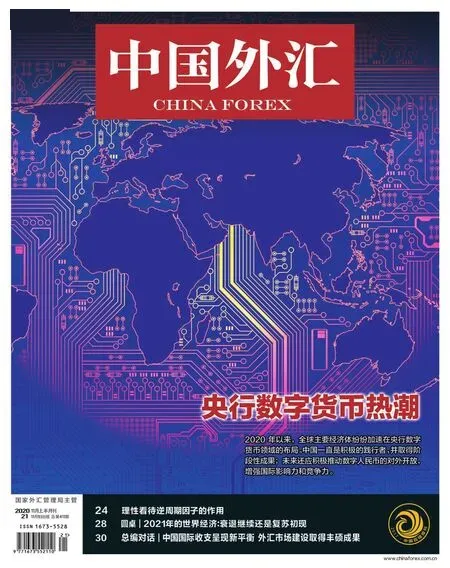理性看待逆周期因子的作用
文/韓會師 編輯/孫艷芳
雖然在官方表態中,對此次逆周期因子的退出使用了“淡出”二字,但本質上是對已經發生事情的描述,并不涉及未來“逆周期因子”是否還會使用。對此,市場不必過度解讀。
2020年10月27日,外匯市場自律機制秘書處(以下簡稱“秘書處”)發布公告稱,“近期部分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價行基于自身對經濟基本面和市場情況的判斷,陸續主動將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價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這被市場普遍解讀為監管當局10月以來第三次釋放的對人民幣持續升值不滿的政策信號。上兩次分別為:10月12日,央行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20%下調為0;10月21日,外匯局宣布近期計劃將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額度新增約100億美元。自2017年5月面世到現在的三年多來,逆周期因子已兩次啟動,兩次退出,其實際作用如何?未來是否還會重返江湖,頗受市場關注。
逆周期因子再次“隱退”是報價銀行的常規操作
逆周期因子肩負穩定匯率波動的重任。2017年5月26日,秘書處確認引入“逆周期因子”,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價模型從此變為“參考收盤價+參考一籃子貨幣+逆周期因子”的三因素模型。當時,人民幣貶值預期較強,我國銀行結售匯持續逆差。盡管國際收支經常項目保持較高的順差規模,但卻因結匯意愿不足,購匯需求旺盛,難以在結售匯市場轉化為對人民幣匯率的支撐力量。逆周期因子誕生之前,資金外流對人民幣即期匯率產生的巨大下行壓力很容易抵消國際外匯市場波動(即參考一籃子貨幣)兌人民幣中間價施加的上漲拉力,從而出現無論美元指數是升是跌,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都傾向于下跌趨勢。這很容易對投資者心理造成負面影響,進而加劇人民幣“貶值-貶值預期增強-進一步貶值”的惡性循環。這也是外匯市場“羊群效應”的突出表現。逆周期因子的使命就是在中間價定價模型中內嵌穩定機制,避免市場情緒波動通過影響收盤價導致中間價嚴重偏離經濟基本面。
理論上,逆周期因子可以對中間價的波動進行雙向調節,即在市場過度做空人民幣時抑制貶值幅度,在狂熱做多人民幣時降低升值幅度。但2014年至今,由于人民幣總體上處于貶值通道,絕大多數時間結售匯市場為逆差格局。這使得抑制貶值預期,恢復結售匯市場基本平衡成為首要任務,所以逆周期因子一直在抑制貶值上發揮作用。在人民幣貶值預期淡化,甚至進入階段性升值行情時,報價行會自動將逆周期因子恢復中性,也就是將中間價定價模型恢復至“參考收盤價+參考一籃子貨幣”的狀態。在逆周期因子推出后,2017年8月開始,銀行結售匯市場持續大額逆差格局告一段落,雖然尚未恢復全面順差,但月度結售匯順逆差交替出現且逆差規模大幅萎縮的局面,說明市場預期已經出現較大分歧,單邊貶值預期趨于淡化,交易層面已經不會對人民幣匯率施加非理性的貶值壓力。2018年1月9日,媒體報道報價行已經將逆周期因子調整至中性,后被秘書處證實。
2018年6月開始,隨著中美經貿摩擦不斷升級,疊加美聯儲加息刺激美元指數攀升,人民幣貶值預期再次抬頭,突出表現為8月銀行結售匯逆差再次擴大到100億美元以上,同時人民幣兌美元從6.40附近快速逼近6.90。8月24日,外匯市場自律機制秘書處宣布,“8月份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行陸續主動調整了‘逆周期系數’”,從而正式宣告逆周期因子的回歸。
需要強調的是,報價行可以基于自身對經濟基本面和市場情況的判斷決定是否使用逆周期因子對中間價進行調節,當報價行認為根據“參考收盤價+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得出的中間價并未嚴重偏離基本面的時候,就可以隨時將“逆周期系數”歸零。因此,逆周期因子的回歸并不意味著在此后每一天的中間價里面都有逆周期調節的因素。這也就是為什么每一次秘書處都只是對報價行已經采取的行動進行事后確認,而非具體指出哪天逆周期因子發揮了作用。
循著上述邏輯,不難看出,逆周期因子今年再次退出實屬報價行的常規操作。5月下旬以來,由于我國在全球抗疫中動手最早、效果最好,經濟率先復蘇,驅動外匯市場情緒迅速好轉,疊加人民幣資產較高的利率優勢,以及歐美大規模量化寬松催生強烈的全球資產配置需求,海外資金持續流入我國。市場情緒、經濟基本面、跨境資金流動均對人民幣匯率構成支撐。到了9月下旬,市場輿論已經對人民幣繼續維持強勢形成較為趨同的預期。在這種市場環境下,逆周期因子再次停止發揮作用實屬正常。其實根據多家市場機構測算,今年6月以來,隨著人民幣步入升值通道,根據“參考收盤價+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得出的中間價預測值與實際的中間價的差別大多十分微小。這說明,報價行停用逆周期因子的時間要遠遠早于秘書處發布聲明的10月27日。
不能高估逆周期因子對市場情緒的調控能力
作為中間價報價模型的一部分,逆周期因子的核心作用是調節羊群效應和順周期行為對中間價的過度干擾。投資者則通過觀察逆周期因子發揮作用的程度來判斷監管當局對市場匯率走勢的態度。但需要注意的是,逆周期因子雖然有上述調節功能,但并不能改變匯率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基本機理,這就意味著逆周期因子不會改變整體的匯率走勢,改變的只是匯率波動的節奏。這就好像開車下坡,剎車會改變下坡的速度,但不會改變方向。但速度的調節也很重要,其直接關系到能否最終“人車平安”。
還必須看到的是,盡管逆周期因子的確會對投資者情緒產生影響,但也不能夸大其能力。雖然2017年5月和2018年8月,官方兩次公告逆周期因子啟用之后,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趨勢均很快被階段性扭轉,但這功勞卻不能被逆周期因子獨享。
監管當局對市場走勢的適度引導,是逆周期因子發揮預期作用的重要保障。雖然逆周期因子可以對中間價進行調控,但中間價公布之后,當天的即期匯率波動仍然主要是受到市場供求力量的左右。在購匯需求較為旺盛而結匯意愿不強的情況下,結售匯市場的逆差格局很容易耗干銀行間市場的美元流動性。此時,如果沒有央行以較為優惠的價格提供美元流動性,人民幣很容易被打壓至2%的日間波幅下限,進而導致即期匯率和中間價嚴重偏離,進而使逆周期因子對市場情緒的引導作用大打折扣。所以,歷次逆周期因子啟動后,央行都會在銀行間市場做出一定程度的配合,以進一步加強對市場情緒的引導。
例如,2017年5月,在逆周期因子首次啟用之后,6—8月的人民幣對美元持續升值,但銀行結售匯市場卻保持了逆差格局,央行外匯占款余額也連續三個月下降。2018年8月,逆周期因子再次官宣啟動之后,9—12月,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匯率走出倒“V”行情,人民幣貶值趨勢被扭轉,但同期銀行結售匯市場保持逆差格局,央行外匯占款連續4個月下降。很明顯,如果沒有央行在即期市場的配合,在市場結售匯持續逆差的情況下,單純依靠逆周期因子對中間價進行調節,很可能出現人民幣中間價頻頻高開,而即期匯率卻頻頻低走,甚至頻頻觸及日間跌幅上限的尷尬局面。這不但會傷害人民幣市場化改革的公眾形象,人民幣即期匯率頻頻“跌停”的新聞炒作,也很容易進一步惡化市場預期,從而令逆周期因子難以發揮抑制羊群效應的作用。
回到當下。如果將秘書處官方10月27日確認逆周期因子的淡出,與當前人民幣持續升值的背景結合起來看,可能的確有引導市場預期,打壓人民幣多頭熱情的用意;但央行目前已經基本退出了常態化的外匯市場干預,對市場投機最大的威懾力量隨之消失,加之報價行停用逆周期因子在機構投資者內部也早已有較高的共識,因此,可能并不會對市場情緒造成明顯影響,人民幣多頭行情仍可能延續。
人民幣匯率仍然需要逆周期調節機制
雖然在官方表態中對此次逆周期因子的退出使用了“淡出”二字,但本質上是對已經發生事情的描述,并不涉及未來“逆周期因子”是否還會使用。對此,市場不必進行過度解讀。作為一個政策工具,筆者認為,只要有其發揮作用的需要,將來完全可以再次激活。
當下,國際政經局勢錯綜復雜,大國博弈趨于激烈,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后續發展的高度不確定性,我們更需對未來可能發生的資本逆流風險保持高度警惕。特別是在我國民眾和企業外匯風險管理意識不強、匯率風險管理工具較為匱乏的背景下,采取包括逆周期因子在內的多種手段,及時引導市場情緒,避免匯率過度波動沖擊實體經濟,十分必要。
對匯率進行管理和調控難免招致一些輿論壓力,但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從來不是世界的主流。從歷史經驗看,發展中國家和中心貨幣國家相比,綜合實力嚴重不對等,聽任匯率自由浮動不但不能讓匯率有效吸收外部沖擊,反而會加劇外部沖擊的負面影響,甚至使其變為沖擊的來源。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選擇對匯率進行不同程度的管理,是歷經多次貨幣危機沖擊后得出的經驗,也是一種不得已的自我保護。逆周期因子是我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組成部分之一,即使未來逆周期因子退出歷史舞臺,我們也仍然需要有一定的制度安排,避免匯率在外部沖擊下發生嚴重脫離經濟基本面的暴漲暴跌,維護實體經濟的穩定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