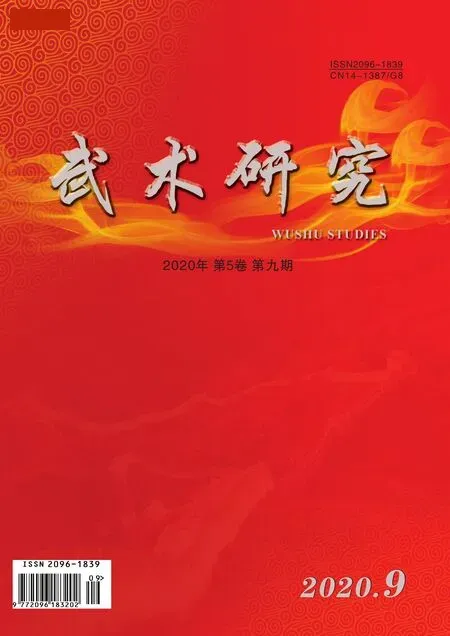云南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主要影響因素研究
田世昌 母順碧 張愛華
云南師范大學體育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原生態”環境正逐漸銷蝕,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正面臨著失傳的困境。作為云南傈僳族民族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云南傈僳族傳統體育,其傳承與發展的過程內涵著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價值的認知、判斷、選擇和認可,其本質是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價值認同與需要滿足的過程。可以說,文化認同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而文化需要則是推動民族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動力。一種文化之所以能為人們所認同,能得到傳承與發展,就在于這種文化能滿足人們的各種需要。為此,本研究以文化認同為切入點,結合文化需要理論,從文化需要與供給的視角,分析影響云南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主要因素,為強化云南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建構其有效的傳統體育文化傳承機制提供借鑒。
1 云南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需求變化對其文化認同的影響
“文化在其最初時,以及伴隨其在整個進化過程中所起的根本作用,首先在于滿足人類最基本的需要。”[1]文化需要是推動文化認同與發展的動力,文化認同必須建立在需要滿足的基礎上。增進人的文化認同離不開美好文化需要的充分滿足。[2]
隨著云南傈僳族社會經濟的發展,傈僳族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賴以生存的土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傈僳族的傳統體育文化需要也在發生變化。例如,游獵經濟時代,一把“勁弩”就是傈僳族一家人的生計所系,[3]射弩在傈僳族生產生活中的地位很高,弩弓不僅是傈僳族男子隨身所攜的工具,還是男子漢的配飾和身份標識。而當下的傈僳族射弩已由游獵經濟時代的生產需要向豐富文化生活和滿足休閑娛樂需要轉變,成為傈僳族每年“闊時節”、“澡堂會”表演的內容。
云南傈僳族聚居地區,由于地理環境因素的影響,道路交通極為不便,迫于生存需要的傈僳族人必須具備爬山、涉水、過溜索等生存技能。隨著怒江州社會經濟的發展,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索改橋項目建設已全面展開,隨著“溜索改橋”項目的完工,依靠溜索過江已成為歷史。如今,溜索在怒江已基本退出歷史舞臺,僅保留著幾對發揮旅游體驗用途。這些最后的溜索,成為見證大峽谷交通變遷的“活化石”。[4]
另外,隨著云南傈僳族社會生活場域的變化,為適應傈僳族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傈僳族的“上刀山,下火海”活動,也由最初的祈福免災、祈求村寨平安的“祭祀娛神”活動,演變為傈僳族“闊時節”“澡堂會”等民族節日的表演活動。而參加表演所獲得報酬的高低,也逐漸成為表演者的表演動力之一。通過“爬刀桿”儀式可以獲得某種資本,亦是“尼扒”們積極開展“爬刀桿”儀式展演的重要內驅力。[5]
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能否被本民族認同與接受,根本上取決于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能否滿足其本民族的文化需求。2017課題組在怒江州調研時發現,被調查對象中,有14%的傈僳族群眾認為,傈僳族傳統體育無法滿足人們需要是影響云南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活動傳承與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2 云南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供給變化對其文化認同的影響
2.1 云南傈僳族家庭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供給缺位對其文化認同的影響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是文化傳承的重要場域。在云南傈僳族聚集地區,家庭是傈僳族文化傳承的重要場域,對傈僳族文化傳承與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家庭教育的耳濡目染,能強化少數民族學生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了解,提升他們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感。[6]長期以來,傳統山地農耕經濟社會中的傈僳族個體是在家庭和社區環境中潛移默化地接受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熏陶,這是一種傳統的、不分時空,滲透于傈僳族兒童日常生活之中的“自發教育”,是民族體育文化最本真的傳承方式。在被調查的傈僳族群眾中,有40.3%傈僳族群眾認為,他們主要是通過家庭了解本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
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傈僳族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以及現代學校教育的發展,現代傈僳族家庭已缺乏本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供給的動力。一方面,隨著云南傈僳族地區學校教育的發展,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傈僳族學齡兒童紛紛進入學校,接受學校教育。而2010年國務院頒發的《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41 號),進一步使入學兒童的年齡繼續向前延伸,削弱了家庭對青少年兒童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教育傳承,瓦解了傈僳族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的家庭場域。另一方面,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逐漸取代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不再是維持傈僳族家庭生計,滿足家庭生存需要的重要手段。而應試教育背景下,學校教育卻已成為傈僳族群體獲取更多生存與發展資源,改變人生命運,成為家庭幸福的重要途徑。許多傈僳族家長不再將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作為家庭教育的主要內容,取而代之的是督促孩子們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期望通過知識改變孩子人生命運,繼而缺乏家庭民族體育文化傳承(供給)的動力。
2.2 學校教育中云南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供給不足對其文化認同的影響
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來看,文化傳承的本質既是一個文化過程,也是一個教育過程。學校是文化傳承的重要場所,學校教育的本質功能是文化傳遞,學校教育是保護和傳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7]學校是民族傳統文化走向普及化、科學化、規范化的必由之路,具有系統進行民族傳統文化傳承的功能。
國務院辦公廳,2005年3月26日印發的《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中提出教育部門和各級各類學校要逐步將優秀的、體現民族精神與民間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編入有關教材,開展教學活動。[8]伴隨著“民族民間文化進校園”的深入推進和各地校園文化建設熱潮的出現,云南傈僳族地區各學校加大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供給,部分學校把民族健身操、民族舞蹈等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納入學校體育教育。2016年怒江州教育局上報州文體局的“十所民族文化傳承基地學校名單”中,涉及到傈僳族文化傳承的學校主要有“怒江州民族中等專業學校、怒江州民族中學、怒江州實驗小學、怒江州直幼兒園、瀘水市民族中學、和和福貢縣省定民族完小”,其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內容主要是舞蹈操和射弩。
然而,在應試教育的沖擊下,傈僳族地區學校缺乏民族體育文化傳承的持續動力, “民族民間文化進校園”實施收效甚微。在目前的升學考試體制下,家長、社會和地方政府都把升學率作為評價學校質量的核心指標,甚至成為唯一指標。無論是學校,還是學生和家長,出于自身利益需要,最終無奈而理性地選擇了應試教育。因而學校在國家政策規范體系中,逐漸形成“轟轟烈烈講文化傳承,扎扎實實搞應試教育”的格局。
學校體育也無一例外,初中學校體育加入到“考什么就教什么,考什么就練什么”的應試教育機制中,而高中學校體育則讓位于其他學科考試,出現了理論上很重要,忙起來則不重要的尷尬局面。
3 現代體育文化供給對云南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沖擊
認同的核心是價值認同。[9]文化認同內涵著價值的判斷、選擇和認可,即對文化是否能滿自身需要程度的認可。農耕社會中,相對封閉的傳統體育文化的環境,使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與其它民族體育文化間缺乏互動與交流。傈僳族只能主動選擇或改造已有的本民族體育文化,或者是創造新的民族體育文化,來滿足自身的民族體育文化需求,因而比較容易形成對本民族體育文化的認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現代化步法的加快,以西方價值觀念為主導的現代體育,借助龐大的媒介帝國和經濟優勢,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深入到世界各個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中,改變著人們的體育文化認知、價值觀念和需要。現代體育文化以其“更快、更高、更強[10]的”體育精神和公平競爭、拼搏進取的價值觀念,和平、友誼、公正的體育理想,風格迥異的活動形式和豐富多彩的活動內容,在全球化進程中得到快速傳播。
云南傈僳族地區的傈僳族青少年兒童進入學校,在學校體育教育中接觸更多的是現代競技體育,而本民族傳統體育卻很少接觸。長期的學校體育認知與體驗,強化了傈僳族青少年兒童的現代體育文化認同。傈僳族青少年兒童選擇現代體育文化來自滿足自身的體育文化需要的過程,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傈僳族青少年兒童對本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需要,弱化了他們對本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認同。
調查結果表明,被調查對象中,57.9%傈僳族群眾認為自己了解現代體育,66.3%的傈僳族群眾喜歡現代體育文化,48.1%的傈僳族群眾認同本民族傳統體育滯后于現代體育。在面對現代體育與傈僳族傳統體育選擇時,認為會選擇現代體育占24.4%,在文化適應過程中采取了“同化”模式。從受教育程度來看,無文化群體中,認為了解現代體育的為36%;小學學歷群體中,認為了解現代體育的為50%;初中學歷群體中,認為了解現代體育的為56.9%;高中或中專學歷群體中,認為了解現代體育的為66.4%;大學及以上學歷群體中,認為了解現代體育的為73.8%。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越高,了解現代體育文化的人數比例也就越大。
當現代體育作為一種主流文化在云南傈僳族地區被傈僳族群體所接受時,產生于山地農耕文化背景下的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將很難適應工業化社會背景下的傈僳族生產生活需要。在現代體育與民族體育文化碰撞與交融的過程中,部分傈僳族年輕人對本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缺乏自信,缺乏學習和傳承本民族體育文化的意愿,對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缺乏認同感。
4 大眾傳媒對云南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沖擊
文化認知是文化認同的邏輯起點。文化認知的過程就是文化選擇的過程,人們對文化的選擇取決于人們對文化體驗的感覺,對文化價值選擇的能動性。個體對文化的認知結果會決定個體對文化的認同態度。可以說,沒有對文化認知的存在,就沒有所謂的認同。
大眾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大眾媒介和其傳播的內容逐漸滲透到傈僳族生活的各個領域,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封閉性已被打破,傈僳族正經歷著不同體育文化認知與選擇的過程,經歷著本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與其他體育文化的“認異”的過程。大眾傳媒正改變著傈僳族群體對本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認知,繼而改變著傈僳族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態度。
大眾傳媒在打破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封閉性的過程中,也為傈僳族文化需求的滿足提供多元化選擇。傈僳族群體可以隨時通過報刊、書籍、廣播、電視、互聯網絡、移動媒體、智能手機等新興傳媒選擇各種電影、音樂、繪畫、攝影、藝術欣賞、收藏和各種現代體育活動來滿足自身不同層次的文化需求,繼而弱化了對本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需求。
大眾傳媒在不經意間已悄然改變著傈僳族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在本土與外來、傳統與現代、正統與非正統等觀念的交融碰撞中,文化認同變得越來越模糊,原有的文化價值認同正在被改變。在大眾傳媒的作用下,傈僳族正經歷著傳統的單一民族體育文化認同向更多依賴外來現代體育文化的多元認同發展。大眾傳媒在改變著傈僳族的體育文化需求偏好,也改變著傈僳族的體育文化供給與認同。
5 云南傈僳族地區體育場地設施匱乏對傈僳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影響
行是知之成,人們對文化的選擇取決于人們對文化體驗的感覺。文化實踐中所經歷的良好情感體驗,以及所獲得的滿足感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價值認同的源泉。民族成員在本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活動中親身體驗的內容越豐富,印象就越深刻,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價值的認知度就越廣,對其價值認同度就越高。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實踐,離不開必要的體育場地設施。聚居在瀾滄江、怒江、金沙江“三江并流”,“依山負谷”傈僳族,怒江大峽谷特殊的地理環境,使該地區的傈僳族群體很難有充足的場地設施來開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活動。2013年,第五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結果表明,云南省怒江州人均體育場地面積1.10平方米,低于同時期云南人均體育場地面積(1.23平方米)水平和全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1.46平方米)水平。調查結果表明,在被調查的542名傈僳族群眾中,有36.9 %的認為沒有場地器材是影響其參與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活動的主要因素之一,應加大場地設施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