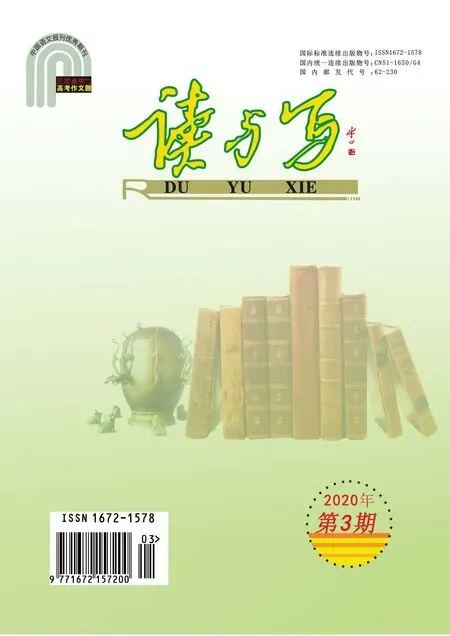我的閱讀時光
管俐珍
(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棠閣學校 江西 永豐 331500)
“年少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在人生的長河中閱讀必不可少,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對讀書的體悟截然不同。靜坐臺前,我想靜靜地理一理我的閱讀時光。
每年到了七八月份是我最悠閑的時光,除去收割稻子的那幾天,剩余的時光都可以待在祖父母的老屋里。老屋沒什么特別的,木質結構的瓦房,屋后是矮山,有幾顆參天的老樟樹;屋前是小溪,潺潺的流水清澈見底。祖父總是戴著眼鏡坐在躺椅上看書或者看報,祖母總是在河邊浣洗,百無聊賴的我順手撿起些書來看,有時候是《故事會》,有時候是《民間故事》,那時才讀三四年級很多字不認識,好在書里面都是些引人入勝的故事,或長或短。個別“攔路虎”并不能阻擋我閱讀的腳步。頭頂有樟樹蔥郁的樹冠籠罩,面頰上有來自山谷的風拂過,耳畔是門前桃樹李樹上高唱的鳴蟬,小小的我就在作者新奇的世界里跟隨主人公一起喜怒哀樂。回想那段閱讀時光多么自由自在,沒有負擔,沒有目的,而是純粹地愛上文字,雖如隙中窺月,卻是閱讀的最好境界。如果你有孩子,不妨從小陪她讀繪本,在他小小的心里埋下閱讀的種子,靜待它長成參天大樹。
因為大量閱讀的緣故,我在同齡孩子中漸漸顯露出語言的天賦來。大大小小的習作比賽,朗讀競賽獲獎很多,至今在老屋的墻壁上貼著。或許世上并沒有什么天賦可言,所有的天賦皆來自小時候不經意的熏陶。到了中學時代,課業負擔開始加重,閱讀時間受到了極大地擠壓,只有在完成作業的間隙“偷摸”閱讀,那時候郭敬明的小說風靡校園,相信很多90后都曾經被他筆下那些憂傷的故事賺足了淚水,都曾經在筆記本上摘抄了無數句令人感慨萬千的話語,那些青春我們當時都或多或少在經歷,故而讀起來頗有感同身受的意味。《悲傷逆流成河》《夢里花落知多少》《小時代》等等,很多已經被搬上了電視熒屏,但當時那些薄薄的書,那些明媚而憂傷的文字卻成了我永久的記憶。那些“地下黨”式的閱讀并沒有像大人們所擔心的那樣影響我學習,反而告訴我如果多努力一點,或許才不負青春。讀高中時有本專門面向學生的刊物,定期刊登學生投放的稿件,這幾乎成為高中時代我最雀躍的一件事。自己閑暇時在紙張上隨意書寫的心情體悟,有朝一日被整整齊齊地刊印在報紙上,那種喜悅不是人人都能體會,看著自己的名字神氣十足地立在標題下方,那種自豪只有酷愛閱讀,酷愛寫作的人才會感同身受。因為每次都占領著大量版面,漸漸在學校里小有名氣。這讓我漸漸發現:閱讀或許不僅僅是閱讀,閱讀量經過一定的累積可以逐漸轉化為書寫的能力。人們常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寫來也能吟”,也說的是這個道理。
寫作的素材大部分來源于現實生活。但是生活大多數時間是波瀾不驚,重復單調的,如果你原樣照搬,你的文章無疑是寡淡無味的,閱讀恰恰可以彌補這一點,這是其一。再者,閱讀別人的作品,往往可以啟發我們發現不同的觀察視角,進而發現不同的寫作方向。哪怕是再千篇一律的生活結合自己的體會以及細致的觀察,也能脫穎而出,與眾不同。在我平時的教學中也發現把作文寫的寡淡無味的孩子比比皆是,究其原因,大抵是他們既不好好閱讀,也沒有去好好去體悟生活。不閱讀,是孩子們寫不好的根源。
在英雄城—南昌,我度過了自己的大學時代。過去了這么多年,江西師大留給我影響最深的依舊是閱讀。紅石房后的顯微湖是我們語教班讀書的好地方,晨光微熹,女孩子們三三倆倆來到湖邊,或坐在秋千上默讀,或坐在草地上背誦,或依靠在柳樹上互相提問,與湖里的游魚,與湖邊的不知名的小黃花構成了最美的景。我人生中大量中外名著的閱讀都是在這個階段完成的。每天夜里在寢室和圖書館的那條小道上走過,我或許是最富有的,精神的富有。如果說小學階段的閱讀最自由,中學階段的閱讀最個性,那么大學階段的閱讀是頗具深度的。
閱讀伴我走過了二十個年頭,也或許將伴我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