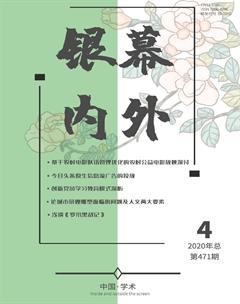新聞作品在媒介融合時代的文化記憶建構策略
一、緒論
隨著全球資本的擴張,經濟結構一體化,信息網絡化加快了信息傳播的自由交流,全球性資源的再分配拉動和刺激了規模空前的文化商品流動和文化形態對撞。加之近幾年動蕩的國際政治環境,以及從網絡新語境下成長起來的一批擁有不同于傳統意識觀念的青少年。這些因素都令人擔心,在全球化的歷史語境中,傳統的文化遺產可能會逐漸被消解。那么,如何將優秀的民族文化、民族遺產繼承下來 如何在多元文化對沖中建構民族核心凝聚力 如何在復雜的國際形勢中構筑屬于本民族的文化記憶 這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給了我們落腳的方向,即:能夠通過敘事性的文本論證“集體”現狀的合理性。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中華民族經歷過挫折與磨難,但正是這些挫折與磨難,賦予了我們無比珍貴的精神文化財富,這些精神瑰寶維系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命脈。不論在何種背景下,中華民族都擁有區別于別國的特殊的文化積淀。而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作為現實生活的一種呈現,其本質也是對現實社會的建構過程。新聞內容的選擇和框架的建構,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對現實社會的感知。因而,新聞能夠選擇特定的新聞主題,通過報道引起關注和情感認同,通過報道與話語主體共同建構文化記憶,使我國珍貴的文化精神得以傳承。
在媒介融合時代,在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推動下,各種媒介內容、分發渠道、終端和組織等不同層面相互滲透交融,新聞報道也有了更多元化的呈現方式,能從更多的維度去建構集體記憶。因此,筆者認為,考察媒介融合時代新聞作品的文化記憶建構策略,不但重要,而且有相當的必要性。
二、概念界定
談到文化記憶,就必須先從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開始講起。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最早在他的《論集體記憶中》第一次表述記憶的社會框架。哈布瓦赫認為個體記憶很難直接被感知,而需要借助某些載體,如文字等。這種通過“他者”的喚醒而建構的社會現象便是集體記憶。在“集體記憶”基礎之上,德國揚·阿斯曼及阿萊達·阿斯曼夫婦進一步提出了“文化記憶”。所謂文化記憶,指的是一種限定于特殊的時期和特殊的社會所獨有的,可以被重復使用的文本內容、意象概念以及儀式觀念。文化記憶是存在于社會和文化之中的,在歷史語境下存在的,本質是一種文化,但又不僅僅是文化,它是一種強調或反復,是在代際循環中存在的想似而可傳承的經驗或知識。
在媒介融合時代,新聞作品已經不僅僅是單一的,消除不確定性的信息集合了。新時代新聞作品以其豐富多彩的形式,多元的視角和其中內嵌的文化內核而超越了傳統新聞報道特征,源遠流長、經久不衰。要研究這一時代的新聞作品是如何構建出文化記憶的,必須要將其放置于文化記憶領域。因此,筆者將借助第29屆中國新聞獎媒介融合類獲獎作品,從新聞作品的主題、敘事、視聽層面探討新聞作品在媒介融合時代的文化記憶建構策略。
近年來,媒介融合已成為打造適應現代傳播體系的新型主流媒體的必由之路,縱觀媒介融合的研究,多是從媒介融合的的概念、動因和利弊角度探討媒介融合對新聞業,對社會的影響。筆者在知網上使用“媒介融合”和“文化記憶”為主題詞進行搜索,僅找到4篇相關文獻,都是探討媒介融合背景下節目的創新或國家認同,可見將媒介融合和文化記憶相結合的深入探索還不多見。而國內有關新聞報道的文化記憶的研究同樣較少,筆者在知網中以“文化記憶”為主題詞,查找到相關文獻3767篇,而以“新聞”“文化記憶”作為主題詞搜索,共得到相關報道98篇,以“報道”和“文化記憶”進行搜索,共得到相關結果75條。筆者對這些文獻分類整理如下,發現其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側重對文化記憶的研究;第二,探討宏觀層面媒介和文化記憶的共振;第三,將文化記憶與新聞報道相結合進行研究。縱觀這些著作,從文化記憶或者媒體報道的角度展開的文獻不在少數,但涉及新聞報道與文化記憶結合的闡述并不多,將其放在媒介融合時代下進行探討的文獻更是幾近沒有,因此這一部分內容十分值得深入挖掘。
因此,筆者將以第29屆中國新聞獎媒體融合獎項獲獎作品為例,選擇其中較為明顯建構文化記憶的內容,如《山西晚報千里走黃河系列報道》、《一個講了55年的故事,你真的了解它嗎 》、《改革開放四十年系列產品》從它們的主題選取、敘事方式、視聽結構進行分析,試圖歸納出新聞作品在媒介融合時代的文化記憶建構策略。
三、新聞作品在媒介融合時代的文化記憶建構策略
(一)在主題層面
毫無疑問,新聞的主題是新聞作品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決定了新聞作品在“說什么”。新聞主題中包含了新聞作品的表層含義和深層價值觀念,它同時也具有著藝術性和傳承性。一部新聞作品應當通過何種主題展現其思想內涵和要表達的觀念,如何通過文字、圖片或視覺符號將用戶的情感認同喚醒,這都是我們需要研究的方向。
(二)在敘事層面
敘事作為新聞文本中最終要的一環,決定著文本“怎么說”的問題。敘事可以決定新聞作品的走向。新聞可以通過表述而完成敘事,通過這種敘事表達,創造出新的記憶點,為用戶奠定基礎的文化認同,構建新的文化記憶,并通過反復強調的方式來完成這種認同,用共同的記憶強化彼此認同的雙方之間的關系。
(三)在視聽層面
新聞可以通過文字符號和視覺語言的勾連而完成敘事,視覺聽覺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圖像等文化符號,本身會產生非常強烈的隱喻與暗示,會給用戶以直接的沖擊和記憶點。阿斯曼曾將經文、繪畫,也列入了“回憶形象”之中。站在現在的歷史維度上,不論是向前還是回顧傳統,文化記憶不僅僅會停留在文字符號之中,還會存在在其他視覺符號之中,尤其在現在的融媒體時代,對文化記憶的建構可以通過更為豐富的形式表達。
四、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媒介融合時代的新聞作品如要構筑共同的記憶,在主題方面,應當選擇合適的主題,深入歷史之中,既要結合傳統,也要推陳出新,立足于當下的時代。在主題選擇上,不但要積極表達國家形象,同時也需要結合歷史,融合文化等內容,使用戶產生共鳴,并且主題選擇也要注重格局,強調人文關懷,這樣的主題選擇才能為更多的用戶所產生情緒認同和情感共鳴,進而構筑共同的文化記憶。
敘事策略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融合新聞作品尤其需要通過優秀的敘事手法,多角度的展現社會層面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內容,因此,更應該在敘事上注重選擇一些能夠喚醒人民認同感,以及用戶情感勾連的故事或事件。敘事策略上,應當偏重于故事化敘事,使讀者可以讀的進去;其次,使用人文化的表達方式,輔以民族共通的隱喻符號,以此產生初步的情感聯系;最后,用平視化的視角或第二人稱,給予用戶參與感,以最大程度的延展用戶記憶內容,喚醒用戶心底的民族情感和歸屬感。
至于視覺語言方面,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技術的進步,融媒體新聞工作者們更應當探索更多元的更豐富的表達形式,創新表達方式,在互動的基礎上建構記憶的相關性。第29屆中國新聞獎媒介融合類獲獎作品中,《“聲”動云南 “音”你而美》《時光博物館》等作品,就是強調視覺符號,加以人文化的解說內容和聽感,并輔之錯綜復雜的敘事技巧,進行內在文化記憶的傳承和情感認同。
參考文獻:
[1] 邵培仁.范紅霞.傳播儀式與中國文化認同的重塑[J].當代傳播,2010(03).
[2] 王霄冰.文字、儀式與文化記憶[J].江西社會科學,2007(02).
[3] 吳瑛.論傳媒對民族文化記憶的喚起.[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01).
[4] 趙靜蓉.《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J].讀書,2016(01).
[5] 邵鵬.媒介作為人類記憶的研究——以媒介記憶理論為視角[D].浙江大學,2014.
[6] 楊琴.新聞敘事與文化記憶——史態類新聞研究[D].四川大學,2007.
作者簡介:劉晨(1995—),女,在讀碩士,研究方向:體育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