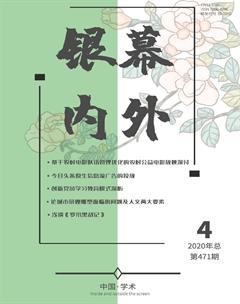中世紀反猶行為產生的現實原因
摘要:猶太人在中世紀社會受到的迫害數不勝數,分布范圍基本涉及了西歐各國,時間上持續了數個世紀之久。探究中世紀反猶行為、現象發生的現實原因,需要著重考慮政治、經濟方面的影響。
關鍵詞:中世紀;迫害;猶太人;基督教
某位學者說過:“反猶主義是一場經濟戰爭。”這句話雖然把經濟因素在反猶主義里起的作用擴大化了,但有一定道理。一方面,中世紀猶太人從事被基督教認為是“充滿罪孽”的放貸業引起了基督教徒的仇視和嫉妒另一方面,統治者、世俗民眾出于對猶太人財富的嫉妒,故意殺害、驅逐猶太人以此來抵消自己的欠款,掠奪猶太人的財富。
猶太人并不是天生的放貸者,猶太人成為中世紀為人所不齒的“高利貸者”是在農業、手工業、商業等行業的參與權被限制之后的無奈之舉。中世紀初期大部分猶太人在歐洲從事農業生產,由于基督教會禁止猶太人在星期日進行勞動,而且猶太律法規定猶太人在自己的安息日不能勞動,這就導致猶太人一周之內不得不停工兩天。中世紀農業效率地下,農業季節、時間變動大,嚴重影響猶太人能依靠農業存活的幾率。而且,公元5世紀起,西哥特人法律明令禁止猶太人擁有土地。因此,猶太人無法靠土地存活,就自然而然的放棄了農業。10世紀前猶太人是歐洲出色的手工藝人,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歡迎,但10世紀后,城市的興起、手工業行會的成立,猶太人被排斥出了手工業領域,“當歐洲基督教國家手工業行會制度普遍確立之后,猶太人各種手工業經營便被有效地阻止。”擺在猶太人面前只有商業這條道路,但是,隨著歐洲商業的發展,愛琴海周邊商業城邦的興起,非猶太人在商業領域地位的增強,猶太人不出意外的被排擠出了商業領域。此時,放債業正好興起,而基督教認為放貸活動是一種罪惡 ,禁止基督徒從事放貸活動,“從早期教父時代,經過查理曼時代,一直到托馬斯·阿奎那,教會一直都頒布高利貸禁令并使之形成一套系統理論。”于是猶太人便轉向了有利可圖的放貸業,正如一位學者所說的“與其說是猶太人選擇了放貸業,不如說是放貸業選擇了猶太人”中世紀基督教徒認為放貸業是最骯臟、最可鄙、最下賤的行業,因此從事這一行業的猶太人就必然會受到歐洲基督教徒的歧視與厭惡。
阿巴·埃班在其著作《猶太史》中寫道:“如果某位主教或世俗統治者想裝滿自己的錢包,只需驅逐猶太人并沒收他們的財產就夠了。”這是中世紀猶太人遭到迫害的經濟方面原因真實寫照。當猶太人成為歐洲放貸業的主角,變得日益富有時,他們和歐洲各地的世俗統治者的矛盾就越來越尖銳,各地的世俗統治者為了掠奪猶太人的財產,采取各種手段,如設立名目繁多的稅:人頭稅、財產稅、屠宰稅……重大事件,猶太人要“自由樂捐”,除了上述掠奪方式之外,國家在必要時刻還會驅逐猶太人來掠奪他們的財產,若經濟需要,還會再次把他們召回國。12到14世紀,法國政府為了金錢,曾五次驅逐猶太人,每次驅逐后不久又會重新召回,尤其是在英法百年戰爭,法王約翰二世及眾臣被英國俘虜時,為了籌集巨額贖金,法國人將早已被驅逐的猶太人重新召回,以頒發“特許狀”等名義掠奪他們的財富,但1394年時又把他們驅逐出去。1186年英王亨利二世傾吞林肯郡亞倫的財產,1291年愛德華一世對于境內猶太人的大驅逐,15世紀西班牙對于猶太人的驅逐等一系列事件的起因都包含了對于猶太人財富的掠奪的因素。
政治也是中世紀猶太人遭受不平等待遇的重要原因。“剝削和壓迫都不是他們引起怨恨的主要原因;而沒有可見的政治作用卻擁有財富才是最不可容忍的,因為誰也不理解無功為何受祿。當猶太人同樣喪失了他們在公共事物中的作用和影響,除了財富之外一無所有時,反猶主義就達到了頂峰。”猶太人在中世紀政治權利的缺失使得基督徒能夠“肆無忌憚”的對猶太人進行迫害,不用擔心報復。猶太人是沒有國家的民族,只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隔都”中,依靠教俗統治者施舍的權利來生存,他們在遭受侵害時沒有自己的國家政權的力量來保護他們,面對整個社會的壓迫只能通過改宗,出走或是殉道等消極方式來保護自己。消極方式助長了迫害者的囂張氣焰。
形成中世紀猶太民族沒有自己的國家這一現象很重要的原因是猶太民族的“客民”身份。“客民”是為了自身的安全,在土著人中尋找某種保護的外鄉人。習俗規定:“認為是客民的人必須依附于主民生活;沒有保護人的客民是社會隨意襲擊的目標;沒有受到庇護或無主的客民如果遭人殺害,兇手不會受到懲罰;除非獲得有權有勢個人的庇護,或受到部落之間協議、國與國之間條約的保護,客民將不像其他社會成員那樣享有絕大多數基本權利;客民的財產可以被視為無主財產,其后代不享有繼承權;任何向客民提供住所的人必須對其行為負責;客民必須依據庇護人的法律生活;對有庇護人的客民的任何攻擊都被認為是對庇護人的攻擊;客民必須向庇護人交納稅金或特別人頭稅;如果客民沒有尋求庇護,或不交納稅金,或庇護和被庇護關系沒有獲得當權者認可,那么,在一年之末,他將淪為奴隸。”
猶太人因為頑固的保持自己本民族的傳統,拒絕皈依基督教而被歐洲排斥,于是便被視為“永恒的外邦人”、“永遠的流浪漢”,“客民”身份成為了猶太人特有的身份標識。“客民”身份的固定使得他們喪失了公民權,淪為一個沒有任何社會權利的民族,自然也就得不到任何保護,遭受侵害也無處訴說。這一身份使得猶太人“在歐洲的任何地方,不論他們到達的時間是多么早,生活在那里的時間是多么長,作出的貢獻是多么大,他們都永遠被看成是外鄉人。”
參考文獻:
[1] 亞伯拉.思危:猶太人的賺錢哲學[M].重慶出版社,2007.
作者簡介:李多多(1995—),男,江蘇南京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上古中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