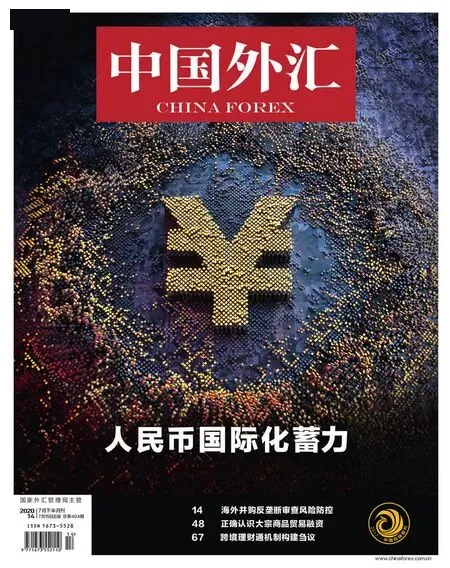縮表式擴張
文/宗濤 編輯/張美思
自全球暴發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主要央行開啟了新一輪擴張資產負債表的行動。與之前有限定數量的“量化”寬松不同,部分央行甚至開始不設上限地擴張資產負債表。與之相比,中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自2014年、2015年以來,規模一直穩定在30萬億元—36萬億元人民幣之間。即便在今年疫情的沖擊下,人民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也基本保持穩定,并沒有像其他主要央行那樣大幅擴張。盡管如此,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貨幣政策沒有對疫情做出足夠有力的反應。實際上,判斷貨幣政策的取向,不僅要看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還要看資產負債表的結構、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和資金價格的變化。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歐、美、日央行開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在四年內從危機前不到1萬億美元擴張到4.5萬億美元。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也是投放基礎貨幣的過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美聯儲主要是從機構手中購買國債和資產抵押支持證券,同時投放出基礎貨幣,實現資產端和負債端的同步擴張。2017年開始,美聯儲開始縮表,資產端減少對國債和資產抵押支持證券的持有,負債端的基礎貨幣也同時減少。
與其他主要央行不同,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仍處在正常區間,主要不是使用資產負債表擴張和收縮的手段,而是更多使用存款準備金率工具。
在2002年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外匯流入快速增長,中央銀行為保持人民幣匯率的有序調整,需要買入外匯,同時投放出人民幣。這個過程是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民銀行投放出的流動性可能超過經濟需要。為避免流動性過剩,人民銀行用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將部分基礎貨幣深度“凍結”。法定準備金是基礎貨幣,也是商業銀行的錢,但只能存放在人民銀行,不能用來放貸。
2014年以來,隨著外匯流入的減少,人民銀行開始了相反操作。外匯儲備的減少,伴隨著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縮小。同時,人民銀行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解凍商業銀行的流動性。2018年以來,人民銀行已十次降準,釋放流動性約8萬多億元,平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15%降至目前的9%左右。
短期來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下降后,央行資產負債表不變,人民銀行投放的基礎貨幣也不變,但商業銀行存放在人民銀行賬戶中可以自由動用的資金增加了,也就是法定準備金變成了超額準備金。商業銀行可以用這些資金發放貸款,從而增加了貨幣供應。可以看到,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下降后,基礎貨幣沒有變,但貨幣乘數增加了,廣義貨幣M2也隨之增加了。因此,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雖然保持穩定,但貨幣政策其實具擴張導向。
從稍長一點時間,比如一個星期后或者是下個月的數據看,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還會導致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縮表”,從而形成看似貨幣緊縮的現象。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后,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金可能超過了正常需要的水平。目前人民銀行向商業銀行支付的超額準備金利率為0.35%,相對來說是很低的。因此,商業銀行會考慮減少在人民銀行的超額準備金存放,這可以通過用超額準備金償還向人民銀行的借款實現。這個還款過程就是人民銀行“縮表”的過程。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中央銀行縮表,基礎貨幣也是減少的,但商業銀行可自由使用的資金和貨幣乘數都增加了,其所產生的擴張效應,將超過“縮表”帶來的緊縮效應,因而貨幣總體上是擴張的。此外,近年來,人民銀行在使用存款準備金率工具的同時,還通過中期借貸便利、抵押補充貸款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這使得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在總體上保持了基本穩定。
當前的金融數據形勢也可以佐證央行的政策效應。5月末,廣義貨幣M2與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分別為11.1%與12.5%,都明顯高于去年。可見,雖然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有“縮表”效應,但貨幣總量是擴張的;同時,金融市場的利率這兩年也有明顯下降。
總而言之,更深入地觀察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和資產負債表結構的變化,對于比較國內外貨幣政策的取向和內涵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