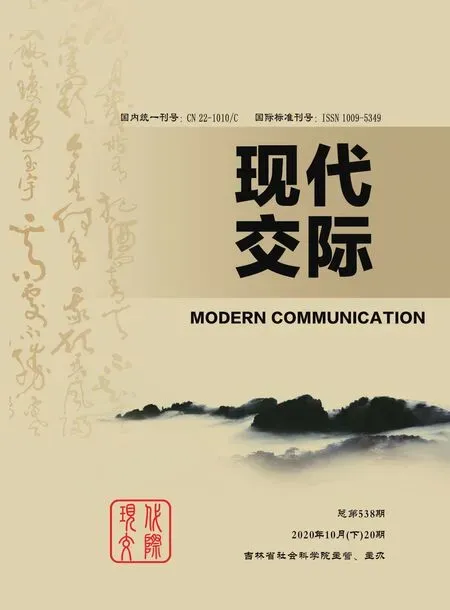從概念整合視角探析反烏托邦文學的隱喻性
——以《我們》為例
毛曉娟
(西安外國語大學 陜西 西安 710128)
反烏托邦文學是對烏托邦文學的一種顛覆。“烏托邦”(utopia)一詞最早由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意為“不存在的地方”“好的地方”,意在指涉一個完美無缺的理想社會。烏托邦文學通過諷刺黑暗現實,表達對美好社會的向往;而反烏托邦文學是前者的“逆流”,同樣是構筑虛幻的時空,反烏托邦文學通過刻畫烏托邦社會的“暗流”受到讀者的歡迎,這不僅得益于作者新奇的設定,也與作品的隱喻性密不可分。
從亞里士多德開始,隱喻就被視作詞語層次上的一種修辭方式,其功能也被看作一種“附加的”“可有可無”的裝飾。[1]20世紀30年代,理查茲發表了《修辭哲學》,首先提出了隱喻互動理論。20世紀80年代,喬治?萊考夫從認知層面對隱喻現象重新解讀與定義;他在文中指出:“我們用以思維與行為的日常概念系統,其本質在基本上是隱喻的。”隱喻是一種認知活動,而對隱喻現象的解讀同樣是一種認知功能的體現。
一、概念整合:心智空間的交互作用
概念整合旨在完善概念隱喻理論,并揭示其內部運作機制。針對概念隱喻理論的不完善,弗科尼亞提出了心智空間理論,他總結出:詞匯表示的不是事物,而是思想和概念,思維空間由此引出,語用功能建立在思維空間中,據此,我們才能把客觀世界中并不存在的東西表達出來。[2]經歷了二十年左右的完善,他又在心智空間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論;他認為隱喻活動在四個空間的共同作用下完成,包括兩個輸入空間、一個類屬空間及一個合成空間。概念過程不是單一從源域向目標域的投射過程,而是對兩個不同輸入空間的壓縮和整合的結果;在合成空間中出現輸入空間中不曾出現過的新結構和概念。[3]一般情況下,概念整合的具體過程為:兩個輸入空間進行選擇性映射并結合后,產生一個新的抽象結構,被命名為類屬空間;隨后,經過這三個心智空間的認知加工步驟,各項成分進入第四個空間,即整合空間,得到前面幾個空間中未曾出現的概念。概念整合理論下心智空間的運作機制如圖1所示:

圖1 概念整合運作圖式
二、《我們》中的隱喻現象分類例析
《我們》是一部經典的反烏托邦文學作品。根據隱喻特征及功能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三類隱喻:沖突化隱喻、陌生化隱喻及委婉化隱喻。這樣的分類方式跳出了傳統的修辭隱喻及認知隱喻分類的窠臼,有利于讀者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認識《我們》中涉及的隱喻現象。
1.沖突化隱喻
為了達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作者營造反烏托邦世界時需要提出一些與常理相悖的概念。當讀者觸及這類概念時,會造成認知上的沖擊。而后在“沖突—分析—解惑”的過程中得到對作品更深一層的理解。如《我們》中對于靈感的描述:“他們能夠創作,結果只是使自己靈感枯竭——癲癇的一種未知形式。”[5]31日常生活中的靈感對于藝術創作是至關重要的,靈感被藝術家們稱為“繆斯女神”;然而,在大一統國,靈感卻是一種病態的癲癇。這種隱喻便與讀者的認知產生了沖突。讀者要站在“一統國”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如圖2所示。概念整合視角下,輸入空間1:靈感概念和輸入空間。2:癲癇概念便建立了起來。兩個輸入空間的相互投射得到了相關性特征:突發性和不可控性。在類屬空間中,靈感和疾病的相同特征被提取出來。最后在合成空間得到“靈感像癲癇”的隱喻結果。由此讀者可以看出,這樣“不合常規”的隱喻既體現了“一統國”對創造力的扼殺,也從側面反映了“一統國”人民對現狀已經習以為常,甚至變得麻木。

圖2 靈感—疾病概念整合過程
2.陌生化隱喻
通過隱喻,某些尚未定型的經驗借助已成形的經驗得到組織和表達。[6]當源域難以借助日常經驗完成理解時,就會給讀者陌生的感覺。這時,就需要以隱喻為媒介理解源域和目標域之間的關聯,從而體會這類隱喻的內涵。《我們》中的每個篇章都由主人公D-503的“日記”組成。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向“古代人”介紹“一統國”的情形,因而很有可能會帶來一些超越讀者常識范圍的體驗。如“一統國”的居民一律以號碼稱呼。文中不乏對這一設定的呈現:“成百上千的號碼穿著式樣統一的制服”[5]21“號碼們一排排地從身邊走過”[5]89“我們每個號碼身上都有一個看不見的滴答作響的節拍器”[5]127。那么,如何從認知的角度去理解這種隱喻呢?如圖3,以概念整合的理論分析,首先,我們可以建立輸入空間1:人類概念和輸入空間。2:號碼概念。然后對兩個輸入空間進行選擇性投射,得到相關聯的成分:集合性、序列性。將兩個輸入空間的成分進行整合便進入了類屬空間。在類屬空間中,人和號碼的概念被提取出了相同的特征。最后到了合成空間,兩個原本無關的概念被整合成同一個概念,由此得出“人是號碼”的隱喻。號碼不再擁有“人”的個性與感情,只是毫無差異的工作機器。作者把“號碼”作為人的隱喻,表現了人的異化和“一統國”內如數字一般嚴苛的極致理性。這個隱喻及衍生的設定貫穿全文,始終為讀者帶來理解號碼們生活的新鮮感及認知上的沖擊感。

圖3 人類-號碼概念整合過程
3.委婉化隱喻
反烏托邦文學作品的設定雖然奇特,但并不是憑空而來。在政治的高壓下,作者為安全起見,對于思想的批判往往需要采取“含沙射影”的方式,這種“點到為止”的委婉化隱喻在反烏托邦文學中屢見不鮮。如在《我們》中,對于“詩歌”的解釋是:“詩歌——這是為國家服務的工具。”[5]73這樣的比較體現出現實世界和“一統國”的極大差異。在現實世界中,詩歌是藝術的結晶;而在“一統國”中,詩歌成為一種用于思想教化的工具。如圖4所示,按照概念整合的模式,我們可以確定輸入空間1:詩歌概念和輸入空間。2:工具概念。兩個輸入空間相互映射,得出的相同特征為主觀性和可操作性。到了類屬空間,只有相似性保留了下來。然后,在合成空間,兩個概念融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詩歌是工具”的隱喻。“一統國”的詩歌是為施恩主歌功頌德的政治工具,詩歌只是用來愚化和奴化號碼們的心智的。“一統國”中,詩歌成為禁錮人思想的枷鎖;而現實世界中,那些政府的御用文人在粉飾太平。由此,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形成了一種委婉而又巧妙的對應。

圖4 詩歌-工具概念整合過程
三、反烏托邦文學的隱喻性
對于讀者而言,認知語言學視角的隱喻,并非一種偶然的現象。可以說,隱喻是無處不在的。而反烏托邦文學的幾個主要創作手法,如沖突化、陌生化、委婉化,都與隱喻現象息息相關。
1.沖突化
在認知互動的過程中,認知沖突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當隱喻所聯結的目標域和源域之間距離過遠,造成認知與常識不符的情況時,就會出現認知沖突。如果語言結構形式上是矛盾的,而在矛盾的結構形式下有相互聯系的意義,那么語言就會充滿張力。[7]為了解讀隱喻張力,讀者要調動自己的認知系統,依據概念整合的上述步驟加以映射并結合,以理解文本的深層的荒謬感和諷刺感。如喬治?奧威爾《動物莊園》中,一只名為“摩西”的烏鴉在動物農場中整天宣揚關于“糖果山”的傳說:“所有動物死后都會到那兒”“位于天上云層后面一點兒的地方”“每周有七個星期日”。讀者調動自己的認知系統就會發現“糖果山”的種種特征與“天堂”相似。動物農場中,烏鴉“摩西”不斷渲染“糖果山”的美好來迷惑莊園里的動物們;而在現實世界中,宗教不斷描繪“天堂”的神圣美好來麻痹虔誠的教徒。當理解到這一層時,就能體會到作者對于宗教的諷喻。
2.陌生化
“陌生化”是文學作品的一個常用手段,是將人們習以為常的事物進行陌生化處理,可以有效地刺激人們的感知,從而增加文學作品的吸引力。[8]“陌生化”是反烏托邦文學作品中一個顯著的藝術技巧。作者會塑造一個“烏托邦”式的世界,然后在小說的情節及世界觀一步步展開的過程中,撕碎“烏托邦”社會偽善的面具,暴露其內部的丑惡。為了使烏托邦世界有別于現實世界,作者會設置一些概念來描繪新世界中的獨特景觀,如《1984》中,主人公溫斯頓工作的“真理部”,這樣的部門是現實世界沒有的,因而激發了讀者的興趣與好奇心。隨著情節的推進,讀者便會發現,“真理部”所謂的“真理”是最高領導階層的“真理”,為了維護它,甚至可以銷毀、篡改、再版報刊書籍。在荒謬感中,讀者終于明白,“真理部”隱喻的是一種維護極權思想的工具。理解了這一層的隱喻,就能明白極權思想對人思想鉗制的程度之深,以及作者所表達出來的對未來社會思想自由的隱憂。
3.委婉化
與傳統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不同,反烏托邦文學通常不直接批判現實,而是用一種較為委婉和隱晦的方式表達對社會問題的批判及擔憂。[9]通過隱喻,作者可以借用其他領域的概念或創造新的術語,不留痕跡地批判、映射現實世界,同時還能豐富文本的內容,增加其可讀性。
這種委婉化之所以存在于反烏托邦作品中,是因為其描繪的虛構世界與現實世界中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們》中掌握生殺大權的“施恩主”、《美麗新世界》中控制人精神的“福帝”,以及《1984》中無處不在的“老大哥”,無論哪種稱謂,都以一種迂回的筆觸指向了“最高統治者”的身份及權威。雖然具體的呈現方式不同,但是作為一個根隱喻,最高權力下的社會建構方式則呈現出類似的特色。這些特色放在概念整合理論中,可以被更加直觀地理解。
四、結語
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視角,反烏托邦文學以其諷刺性的思想及形象化的語言,受到讀者和研究者的青睞。然而,鮮有研究著眼于烏托邦文學的隱喻現象,也未能挖掘烏托邦文學與認知隱喻的關系。基于此,通過概念整合理論,對《我們》中出現的隱喻現象進行分類并例析,以便探尋出認知隱喻在反烏托邦文學中運作的基本機制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