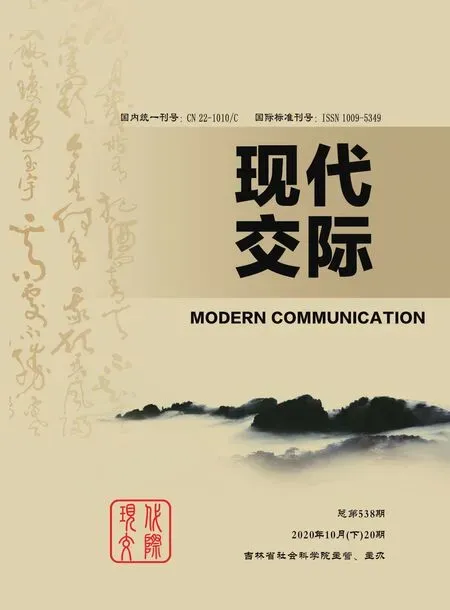童年創傷經歷、家庭環境與成年后焦慮的關系
杜 蕾 張 楠 劉永恒
(德州學院教育科學學院 山東 德州 253023)
社會發展速度不斷加快,各種心理問題越來越多。成年人是社會發展的中流砥柱,憑借豐富的人生閱歷,成熟的人格,謹慎的思考支撐著人類社會的大廈;同時,他們也承受著來自社會、家庭的各種壓力。一些成年個體,因為早期發展不完整或認知方面的局限,較容易出現抑郁焦慮、軀體化等心理問題[1]。適度的焦慮有利于個體的生存和發展,但過度的焦慮則會影響身心的健康發展。
本文試圖探討童年期創傷經歷、家庭環境與個體成年后焦慮的關系,填補對焦慮影響因素研究的空缺,推動對焦慮的研究和調節;同時關注個體早期成長經歷,重視童年創傷經歷在個體成長過程中的作用,以便心理工作者幫助焦慮個體平復早期心理創傷,保持更穩定健康的身心狀態。
一、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于2019年3月至2019年6月,共發放40份問卷,包括10名來訪者,12名臨床心理科病人,18名大學生。回收39份,剔除無效數據后,有效問卷38份,回收率97.5%,有效率95%;其中男11人,女27人,年齡在16—52歲,平均年齡為23.79;被試學歷為高中及以下10人,專科2人,本科25人,碩士1人;被試包括學生16人,來訪者10人,臨床心理科病人12人。
(二)研究工具
1.焦慮自評量表(SAS)[2]
焦慮自評量表(SAS)由Zung于1971年編制,是一個含有20個項目,4級評分的自評量表,用于評出焦慮病人的現在或過去一周的主觀感受。SAS 適用于具有焦慮癥狀的成年人,具有較廣泛的適用性。
2.童年期創傷問卷(CTQ-SF)[3]
問卷包括5個分量表:情感虐待(emotional abuse)、軀體虐待(physical abuse)、性虐待(sexual abuse)、情感忽視(emotional neglect)和軀體忽視(physical neglect),共28 個條目,每個分量表含5個條目,每個條目采用5級評分。
3.家庭環境量表中文版(FES-CV)[4]
由費立鵬等人于1991年在美國心理學家Moss R.H.編制的“家庭環境量表(FES)”的基礎上修訂改寫而成。該量表含有10個分量表,分別評價10個不同的家庭社會和環境特征。
量表具有較好的效度和重測信度。問卷使用要求受試者具有初等以上教育程度,主試應監控受試者完成量表的全過程,在受試者不能理解多個項目時,應中止測試并確認答卷無效。
(三)研究方法
將焦慮自評量表、童年期創傷問卷和家庭環境量表裝訂成冊,選取臨床心理科病人、來訪者及學生共40人發放問卷,采用統一指導語,填完后立即回收問卷。經過篩選,有效問卷共38份。將獲得的調查結果使用SPSS19.0錄入數據并進行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驗、方差分析、相關分析等統計分析。
二、結果與分析
(一)焦慮、童年期創傷經歷和家庭環境的描述統計
研究顯示:38名被試的焦慮自評量表得分平均數為48.13,標準差為13.50。童年期創傷問卷得分平均數為56.66,標準差為17.94;其中情感虐待得分平均數為9.63,標準差為4.03;軀體虐待得分平均數為9.53,標準差為4.66;性虐待得分平均數為9.21,標準差為4.07;情感忽視得分平均數為10.58,標準差為4.02;軀體忽視得分平均數為10.00,標準差為3.70。家庭環境量表中的親密度得分平均數為6.32,標準差為2.90;情感表達得分平均數為5.32,標準差為1.80;矛盾性得分平均數為4.89,標準差為2.51;獨立性得分平均數為5.34,標準差為1.46;成功性得分平均數為5.74,標準差為1.84;知識性得分平均數為3.84,標準差為2.53;娛樂性得分平均數為3.76,標準差為2.94;道德宗教觀得分平均數為4.42,標準差為1.57;組織性得分平均數為4.47,標準差為2.44;控制性得分平均數為3.71,標準差為2.03。
(二)焦慮、童年期創傷經歷和家庭環境的相關研究結果
(1)童年期創傷及其各因子在性別上無顯著差異。
(2)焦慮自評量表中的得分在性別上無顯著差異。
(3)家庭環境中的各因子在性別上無顯著差異。
(4)焦慮與被試類型無顯著差異。
(5)情感虐待、軀體虐待和性虐待在被試類型上有顯著差異。
(6)家庭環境中的情感表達和控制性因子在被試類型上有顯著差異,家庭環境中的其他因子在被試類型上無顯著差異。
(7)焦慮狀況與童年期創傷經歷有顯著正相關關系(r=0.668),童年期創傷經歷中的情感虐待(r=0.438)、軀體虐待(r=0.451)、性虐待(r=0.564)、情感忽視(r=0.756)和軀體忽視(r=0.724)均與焦慮狀況顯著正相關。
(8)焦慮與家庭環境量表中的親密度、情感表達、成功性、組織性和控制性因子顯著負相關,與家庭環境量表中的矛盾性因子顯著正相關。
三、討論
(一)人口學變量與焦慮、童年期創傷和家庭環境
1.性別與焦慮、童年期創傷和家庭環境
通過分析38名被試的問卷調查結果得出,童年期創傷及其各因子在性別這一人口學變量上無顯著差異,這與何劍驊(2016)的研究結論不一致。由于本文隨機選取的被試樣本男生11人,女生27人,男女分布不均衡,難以研究童年期創傷經歷在男女之間的差異;其他研究更多關注學生群體的童年期創傷經歷,而本文研究的被試不僅局限于學生群體,還包括社會人士,被試特征相對廣泛且分散;被試在報告虐待經歷時可能會出現隱瞞行為。所以本文的研究結果與其他研究出現了不一致的地方。
研究顯示,焦慮狀況在性別這一變量上無顯著差異。前人的研究更多聚焦于青少年焦慮狀況,青少年大多是學生,他們面對的升學壓力基本相同,彼此之間的焦慮狀況可能不具有顯著差異。但是,由于個體之間的家庭環境、經歷事件和心理素質不同,所以焦慮在不同個體中會有一定的差異。本文研究的被試職業不同,面臨的社會環境不同,所處的年齡階段也不同,因此,焦慮在性別方面并無顯著差異。
研究表明,家庭環境各因子在性別上沒有顯著差異。這與王佳寧(2016)對內蒙古大學生家庭環境的研究結果不一致,王佳寧的研究聚焦于內蒙古大學生的家庭環境,地域比較集中,學生群體的被試特征也比較集中;而本研究的被試并非集中于同一地域,被試來源不同,被試年齡和特征都有一定的差異,且本研究的被試數量較少,即使被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結果也可能與其他大樣本研究存在不同。
2.被試類型與焦慮、童年期創傷和家庭環境
通過對38名被試類型進行分組,將大學生記為1,來訪者記為2,臨床心理科病人記為3,在此基礎上分別與焦慮、童年期創傷和家庭環境進行差異分析,得出焦慮與被試類型無顯著差異。童年期創傷中的情感虐待、軀體虐待和性虐待在被試類型上具有顯著差異。其中被試類型中的來訪者和大學生在情感虐待方面有顯著差異(p=0.014);來訪者和大學生(p=0.033),臨床心理科病人和大學生(p=0.042)在軀體虐待方面有顯著差異;來訪者和大學生(p=0.041),臨床心理科病人和大學生(p=0.021)在性虐待方面有顯著差異;來訪者和臨床心理科病人在童年期創傷經歷方面沒有顯著差異;但是來訪者和臨床心理科病人和大學生在童年期創傷經歷的某些因子上差異顯著;家庭環境中的情感表達和控制性因子在被試類型上有顯著差異。家庭因素對心理健康水平、人格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家庭是社會支持的重要基礎,也是精神刺激的重要來源。不管是來訪者還是臨床心理科病人,他們都是在心理方面遇到了問題而尋求幫助的,在家庭環境方面或多或少會與大學生的家庭環境有一定差異。
(二)焦慮與童年期創傷經歷
研究結果表明,童年期創傷及其中的情感虐待、軀體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視和軀體忽視五個因子均與焦慮有顯著正相關,這與之前有關研究結果一致。童年期創傷經歷是指個體16歲之前經歷的使其身心健康、社會功能、生活方式和理智受到沖擊,超出其承受能力的事件。而在16歲之前,個體正處于身心快速發育發展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遭受的創傷事件對個體心理健康發展會產生一定的阻礙作用。如果個體在這個時期遭受的創傷未能治愈,會對個體的心理素質和心理承受力產生負面影響,導致各種心理問題,對身心健康不利。
(三)焦慮與家庭環境
研究發現:焦慮與家庭環境量表中的親密度、情感表達、成功性、組織性和控制性因子有顯著負相關,與家庭環境量表中的矛盾性因子有顯著正相關。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一致。家庭環境是指家庭情境中影響家庭成員健康發展的各種事物的總和;其中,父母及其他親人對個體的態度會對個體心理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果家庭成員與個體之間的關系不夠親密,或情感表達不足,個體感覺不到家庭成員對自己的支持和愛護,可能會因為缺乏依賴感和安全感而產生心理問題;如果家庭中矛盾較多較強烈,也會使個體對家庭失去信心,處于失望甚至絕望狀態,引發心理問題。家庭是個體早期成長的主要生活環境,家庭環境會對個體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響,良好的家庭環境有利于個體心理的健康發展。
四、結語
第一,童年期創傷經歷與成年后焦慮顯著正相關,童年期創傷經歷的各個因子與成年后焦慮顯著正相關;第二,家庭環境中的親密度、情感表達、成功性、組織性、控制性和矛盾性因子與成年后焦慮相關,其中親密度、情感表達、成功性、組織性和控制性與成年后焦慮顯著負相關,矛盾性與焦慮顯著正相關。
研究過程中,采用方便取樣進行問卷調查,最終取得有效數據38份,在研究的過程中,由于樣本數量偏少,被試年齡及其他特征分布廣泛,男女所占比例不均衡導致在分析人口學變量的影響時與前人研究出現不一致的情況。本研究調查的被試特征較分散,與前人的研究相比缺少顯著的人口學特征,在以后的類似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適當擴充樣本量,把握好性別平衡。
希望可以推動對焦慮和童年期創傷經歷及家庭環境方面的研究,促進焦慮問題的解決,幫助焦慮個體更好地了解自己,為研究焦慮問題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