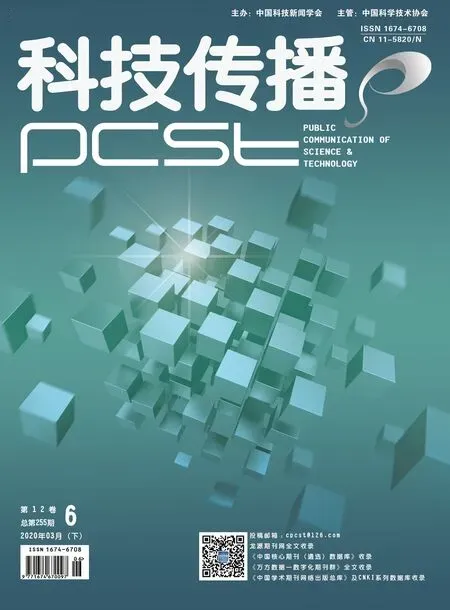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的新聞專業主義
鄧 珂
1 新聞專業主義的源頭和流傳
19 世紀末,阿道夫·奧克斯入主《紐約時報》,并向社會提供嚴肅的社會新聞,成為新聞專業主義的源頭。從中可以看出,從新聞專業主義這個理論誕生之時起,它就是與為大眾提供信息不可分割的。新聞專業主義之所以剛剛誕生就受到受眾和新聞專業從業者的熱烈追捧,概因它既符合受眾心中大眾媒體的形象,又能夠幫助媒體機構業減少內耗、擴寬受眾市場、減少外部干預。
新聞專業主義簡單來說就是社會媒體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導向,以公正、全面為原則,向社會大眾提供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它規定了新聞相關從業者要以社會利益為第一原則,不是某一利益集團手中的“擴音喇叭”,而是社會的觀察者,以科學、理性、客觀的態度來報道事實,不摻雜個人的情感,更不會向政黨、財團低頭,為他們搖旗吶喊。
1.1 新聞專業主義在西方社會的發展
新聞專業主義雖然早在100 多年前就在西方社會誕生,但從其誕生以來,它就沒有在西方社會真正的實現過。新聞媒體作為行業之間的“無冕之王”,一直都被其背后的政黨或財團牢牢的握在手中,從來沒有將其權柄遺落出去。尤其是在對外報道中,例如在伊拉克戰爭過后,《紐約時報》就用大量的版面來為自己之前在對伊拉克報道中曾經煽動美國國民支持對其發動戰爭而道歉,又或者在最近的香港事件中,可以看到不論是英國的BBC 還是美國的ABC,這些國際大型傳媒集團,在他們的報道中,都沒有做到其標榜的客觀、公正,皆存在著明顯的傾向性。
1.2 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在20 世紀的90 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新聞專業主義也隨之流入中國。但是對于這個理論,學界與業界之間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學界渴望憑借新聞專業主義理論架起一道防線,將外界的干預完全阻隔在這道防線之外。但是國內新聞行業的從業者,卻對新聞專業主義是否能夠在中國實行畫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因為中國的新聞媒體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其肩上往往承載著宣傳的職責。而宣傳與單純的傳遞信息是截然不同的,宣傳有其目的性和傾向性,而這些是與新聞專業主義互相違背的。
所以,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存在一個可適用的范圍,就像真理,也僅僅是在其范圍之內才是真理一樣,它并不是無限制的可以做到完全覆蓋的。同時,國內的新聞媒體也承載著進行新聞報道,向社會受眾傳遞信息的職責。只有專業的新聞機構面向社會大眾傳遞的嚴肅新聞,才是新聞專業主義所應該適用的地方。而像八卦新聞,道聽途說的小道消息則不在其使用范圍之內。
2 新媒體時代的新聞專業主義
進入新媒體時代后,行業壁壘被逐漸打破,各式各樣的人和平臺都紛紛涌入傳媒行業。曾經由傳統媒體行業所壟斷的傳播渠道被打破,傳統媒體的話語權被稀釋,我們進入了一個“萬眾皆媒”的時代。隨之而來的便是人們對傳統媒體的考問,專業的媒體是否應該繼續存在,曾經所堅持的新聞專業主義是否繼續堅持下去?
2.1 沖擊之中愈發需要專業眼光
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對于傳統媒體,既是一個沖擊,但同時它也能促進傳統媒體行業的進步、升級。在曾經由傳統媒體主導的大眾傳播體系下,傳播渠道被傳統媒體牢牢把持,擁有絕對的主導權,而現在,人人都可以成為信息的傳播者。
人人都可以進行傳播導致傳播內容的擴大化,但這些海量信息的涌入,也使得傳媒平臺的專業性被無限拉低,這就需要專業的眼光來對這些信息進行審查、分辨,要從海量的信息中提取出來人們感興趣的內容。傳統媒體以往的輝煌不等同于專業性,要走出曾經的光環,提高自己的專業水準,在自媒體時代脫穎而出,成為內容生產者的標桿。
2.2 社會化傳播考驗媒體內容的交互性
新媒體技術使得傳播有原本的單向傳播轉向了更加具有交互性的互動傳播,越來越多的信息通過社交網絡進行傳播,專業媒體也不得不擴展自己的業務范圍。但是社交化的傳播與過去的以傳統媒體為核心的大眾傳播有所不同,社交化傳播的傳播內容要更具滲透力。內容是否具有社交價值,能否維系自身的社交形象都是媒體在生產內容時所應該要考慮的。因此,媒體在堅持專業主義的同時,也需要探索新道路,適應社交化傳播。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在媒體走向社交化傳播的同時,有許多媒體只注重形式創新,搶占傳播市場,而忽視了媒體是專業性。這些媒體,雖然在短時間內可能會因為其新穎的形式吸引受眾的眼球。但這種本末倒置的經營方式,長久以往,必然會影響到媒體的影響力與公信力。這些都是媒體在走向社交化的道路上應該思考的問題。
2.3 信息繭房挑戰媒體傳播的穿透性
當個體的社交對象成為信息源,社交網絡成為信息過濾網,用戶的個性化信息獲取用一種低成本方式得以實現。但社交網絡也會將一些信息阻隔在外,為信息繭房埋下伏筆。多元交織的關系網絡中,也暗藏每個人的社會“圈子”,網絡中的圈子也會強化信息的同質性。
信息繭房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是人們自己心里選擇而造成的。但是對于社會媒體的傳播而言,這也是一種障礙。所以,傳播信息是否具有穿透信息繭房的能力成為衡量一家媒體傳播技巧、傳播內容、傳播實力的標準,這對任何媒體而言都是一個未曾經歷過的全新考驗。
2.4 “后真相”時代的新聞專業主義
“客觀事實的陳述,往往不及訴諸情感和煽動信仰更容易影響民意”,這是牛津詞典在2016 年收錄“后真相”這個詞時對其做出的解釋。新媒體的崛起,使得越來越多的信息是通過社交App 進行傳播,一個個社交App 構成了新媒體時代的社交網絡。但是,多數在社交網絡進行信息傳播的公眾并沒有專業的傳播素養,很難做到客觀、公正地對信息進行篩選,往往是根據自身的情感傾向、價值取向進行傳播;其次,因為網絡傳播內容多為碎片化的傳播內容,這使得受眾往往不能根據這些零星內容來對事實有個準確的認知,這些都使得“后真相”問題在社交網絡時代誕生并成為人們質疑新聞專業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傳統媒體時代,新聞內容需要時間調查結果,并逐層上報審批,最后呈現在受眾面前的是一個經得起任何考驗的事實真相。而在新媒體時代,發達的社交媒體削弱了傳統媒體的把關人作用,使得真相逐漸挖掘的過程是與傳播同時進行的,人們對于真相的獲知過程如同盲人摸象,直到最后才能匯集一切線索,得到正確答案,而公眾的情感早已在一次又一次的反轉中消磨殆盡,對于媒體專業性的質疑聲也日益高漲。
盡管從哲學層面看,真相似乎有著多面性,但從媒體角度來說,準確描述和判斷一些基本事實,仍是必須的。在對事實的挖掘中,媒體仍是主要的力量。媒體仍然需要到達現場、探求真相的能力,穿越迷霧、核查事實的能力,透過表象、直達深層的解讀能力。
反轉新聞的不斷涌現,說明著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后真相”時代,但某種意義上也推動了公眾對于事實和真相的挖掘。相比于傳統媒體時代,公眾所知道的“真相”只是媒體想讓公眾知道的“真相”,受眾只能選擇接受和服從。今天從社會各界質詢出的“真相”相比之前,會更貼近事實內容的深層。從某種意義而言,“后真相”推動了公眾對事實真相的追尋。
3 重塑新聞專業主義,引領未來發展
在當下的中國,傳統媒體失去了曾經的光環,其公信力受到公眾的質疑,而有償新聞、媒介審判的出現,也使得新聞專業主義被人們畫上一個大大的問號。新聞行業的聲譽使得傳媒市場進入嚴冬,而傳媒市場的嚴冬導致出產的新聞內容質量糟糕,最后使新聞行業的聲音每況日下。面對這種周而復始的泥潭,就必須堅持新聞專業主義,堅持新聞從業者的這一倫理才能拯救新聞,將其從泥潭中帶出。
3.1 新聞從業者:繼續堅持新聞專業主義
新聞專業主義作為支撐整個新聞行業的行業信念,是每一個新聞專業從業者都需要遵守的原則。新媒體的崛起,并不代表著新聞專業主義走下了神壇,相反,任何一個想要走向專業化的新媒體平臺都需要新聞專業主義來保持其繼續生存下去的養分。
但是專業的傳統媒體仍是踐行新聞專業主義的主力軍,新聞從業人員作為新聞專業主義最忠實的擁簇,將會成為新聞行業的專業性標桿,積極推動新聞專業主義的普及和實踐。
3.2 個人:媒介素養成為個人“必修課”
針對新媒體時代公眾成為新的傳播主體,社交平臺成為新的傳播渠道,有部分學者認為新聞專業主義不僅僅只是新聞從業人員需要遵守,而是所有想要參與新聞內容生產和傳播的社會公眾都需要遵守和執行。
而最基礎的就是提高公眾個人的媒介素養,盡量以一種理性、客觀的態度參與新聞傳播活動,同時在傳播新聞內容時努力做到全面,將新聞故事完整的帶給公眾,避免碎片化傳播。
3.3 傳播平臺:嚴守法律與道德的約束
傳播平臺在現在的傳播模式框架下,扮演者愈發舉足輕重的角色。平臺在制定算法推送規則時,都應該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導向,以公正、全面為原則。平臺規模越大,其能撬動的社會影響力也會愈大,一個合格的傳播平臺,越要牢牢遵守法律與媒介倫理道德的約束,以公眾利益為第一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