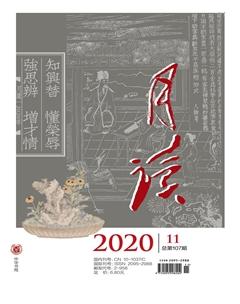盛唐書壇
葛承雍
唐代“貞觀之治”以后,政治上相對安定,文化交流頻繁。至開元年間,文化上的推陳出新達到了空前高度,整個社會充滿著一種恢宏、奔放的氣象。知識分子們心中普遍蘊含著事業上的自信、為國建功的榮譽、拓邊開疆的渴望、生活的熱情浪漫、強悍豪邁的風度,這就是產生“盛唐氣象”的社會氛圍和思想基礎。
從高門子弟到寒士新貴,從上層文人到市井書生,他們豪飲放歌,追求仕進……似乎這個世界就是他們縱橫的天地,這個時代就是他們馳騁的年華,全部身心就要投入到這個富強興盛的社會中。整個盛唐時代的社會心理是青春的、健康的、豐滿的、歡樂的、開拓的,翻涌著積極向上的力量。
在這種時代環境下,文化藝術新境大開、百花齊放,詩歌、音樂、舞蹈、繪畫、雕塑……組合成宏闊博大、輝煌燦爛的壯麗圖卷。而其中書法的發展,甚至達到了無可再現的高峰,既是這個時代最普及的藝術,又是這個時代最成熟的藝術。不僅各種書體一起出現,而且還有了不同的流派典范;不但有著許多知名的大書法家,還有數目更多的民間書法家;不但存有風神各異的精美書法作品,還留有自出心裁的大量手寫宗教經卷。上層社會不再把書法當成酒醉飯飽之余的消遣,不再當作標明身份、點綴風雅的精神玩物,而是把它當作展現才華的方式和人品高尚的反映,當作自由心理和自信力量的體現。下層社會也不再把書法當成掙錢糊口的一種手段,而是把它當作一種藝術追求。這就是書法藝術在盛唐時期受到社會各個階層喜愛的一個原因。
自魏晉至隋,書法名跡以真、行、草書為主流,隸書絕無僅有,篆書幾成絕響,如同有著一個漫長的斷層或一段書體的空白,除了沿襲舊格之外,幾乎無所作為。而盛唐則書體皆備,真、草、行、隸、篆,各立門戶,開宗創派,蔚為大觀。這對書法的繁榮來說無疑是一個福音,因為它不僅提供了新的文化類型,并且呈現出唐人的文化追求。與秦漢以來碑志或其他寫在絹或紙上的書法作品不留書家姓名不同,唐代不少碑志、經卷甚至習字帖都署有執筆者的姓名爵里,從而使此人的作品得以流傳。從當時社會心理的角度看,人們不厭其煩地題寫姓名,似乎都是在證明自己價值的存在、自己的權利、自己的社會地位和文化水平,體現了人的自我意識和創造力終于被社會所承認。這也是盛唐知識分子地位獲得提高的反映。
初唐的行書已經很漂亮,像歐陽詢的《張翰思鱸帖》《夢奠帖》等,處處顯出深厚的楷書功底。但其風度體貌如同初唐楷書一樣還沒有從梁宋氣質中擺脫出來。到了盛唐,行書則以一種活潑酣暢的新姿態展現出來,它不再是輕盈華美、云霧輕籠,而是風流多姿、精神瀟灑,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李邕。這位出身書香門第的文人,官至北海太守,人稱“李北海”。他的書法初取二王而又有六朝氣勢,還得力于歐、虞、褚諸家,但既得其神妙,乃擺脫舊習,自具面貌,筆力一新,奕奕動人。他不僅以制作銘頌而聞名天下,還擅長以行楷入碑,筆勢雄健,結字沉穩。《岳麓寺碑》是其精心之作,強調正斜、伸縮、動靜、疏密的對比,在章法布局端莊凝重下,呈現出生動多姿、跌宕有致的意趣,有著自己的行書風格。
史載李邕“性豪侈,不拘細行”,提倡創新,反對照搬模仿,并宣稱“似我者俗,學我者死”,深刻地揭示了書法創作觀的內涵和規律,告誡后人要理解他的革新精神和個性特點,才不至于生搬強套,走向僵化。這也是盛唐書法藝術家們取得超過前人成就的重要原因。
以草書著名的有孫過庭、張旭、懷素等。孫過庭書名著于一時,他的貢獻在于其書法的破碎感和鋒利感,粗頭粗眼,下筆率意,有一種大氣磅礴的大師氣度,使人感受到他的草書中有一種強烈的充滿生命意蘊的跳躍。從孫過庭《書譜》和傳世的其他帖刻來看,其書法圓熟濃潤,筆勢堅勁,點畫時有側勢,遇直筆向左上轉折而出時往往取蘭葉狀破鋒形,結構規律性強。而孫過庭草書《景福殿賦》,幾乎筆筆都用露鋒,明確地顯示出筆勢的意向。這種兩端尖而動,中截肥而硬的線條,承上啟下,映左帶右,鮮明地體現出筆畫的來龍去脈和連貫血氣。如果說珠圓玉潤與中鋒運筆是書法中不變的金科玉律,那么孫過庭書法線條不完整的破碎和不含蓄的鋒利,則使他敢蹈異境,用側筆偏筆來違背二王的教誨,也有悖于唐初諸家的楷范。
有學者指出,至遲在盛唐已形成張芝、張旭、懷素為一家,王羲之、王獻之為一家,智永、孫過庭為一家的三派草書,有的濃潤圓熟,有的婀娜飄逸,有的沉著剛健,諸家錯布,變化之速、花樣之多、更迭之繁,實為魏晉以來所未見。書法的多維圖景和文化的豐富層次決定了盛唐書壇的蓬勃格局和創新風貌。
杜甫對草書大師張旭十分推崇:“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難得”,“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李白在《草書歌行》中對懷素的狂草十分稱贊:“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
草書與詩歌相輔而行,能吸引這么多的知識分子,恐怕不僅僅是線條的節奏符合樂曲音符,也不單單是字形體貌的浪漫瑰麗,而是具有同一審美氣質。那飛舞神速的線條使他們豪邁,欲揚先抑的均衡使他們浮想,流暢矯健的層次使他們激蕩,驚心動魄的節奏使他們傾倒,旋轉劍舞的動勢使他們鼓舞,草書最能表現他們當時的思想感情,最能反映他們的群體心理,最能集眾美于一身。從急驟強烈的狂草揮灑到聲動山岳的舞蹈胡樂,正是那個時代的社會氛圍和文化心理的真實寫照,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渴望成功的心聲。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敘說盛唐書法音樂性的美,我是非常同意的:“那如走龍蛇、剛圓遒勁具有彈性活力的筆墨線條,那奇險萬狀、繹智遺形、連綿不斷、忽輕忽重的結體、布局,那倏忽之間變化無常、疾風驟雨、不可遏制的情態氣勢,盛唐的草書不正是這紙上的強烈舞蹈么?絕句、草書、音樂、舞蹈,這些表現藝術合為一體,構成當時詩書王國的美的冠冕。它把中國傳統重旋律重感情的‘線的藝術,推上又一個嶄新的階段,反映了世俗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上升階段的時代精神。”
假如說古雅幽深,尚得漢魏遺意的初唐歐陽詢、薛純陀、殷仲容的隸書皆稱名手,那么至盛唐時期,隸書風貌嬗變,趨于平滿淺近。特別是唐玄宗李隆基喜愛風骨豐麗、端莊秀雅的隸書,寫有《孝經》等碑版。為什么在楷書成熟、草書創新的時代,把這個已經失去實用價值而僅有藝術價值的書體又搬上了盛唐書壇呢?這不能不考慮玄宗一生的崇道活動。唐玄宗上臺后崇道抑佛,目的在于利用道教重振屢遭蹉跌的李唐王朝。而西漢之初崇尚“黃老之術”的治國功效,對他有著重要影響。西漢實用的隸書自然也成了他崇尚道教的手段與工具。開元后期,國泰民安,道教的煉丹、引氣等,更成了玄宗企求長生益壽的方術,隸書因而也成為盛世升平的文化點綴,成為玄宗多才多藝、閑情逸致的娛樂手段。因此,在一個不那么迫切需要隸書的時代,隸書因得天子的青睞而顯赫一陣,幾成書壇的大宗。
唐代篆書最著名者是李陽冰,他也是盛唐書壇上的一位大家,官至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可算是一個大知識分子了。他的篆書,“勁利豪爽,風行雨集,識者謂之倉頡后身”。盛唐、中唐許多書法家寫楷碑都請李陽冰題篆額,認為這是聯璧之美,獨步天下之妙。李陽冰的篆書作品有《三墳記》《縉云廟碑》《遷先塋記碑》《清涼寺碑》《城隍廟碑》等。
在盛唐開放、創新的文化環境里,以復古為準繩的篆書卻門庭中興,重返書壇。人們可以看到書法各體的延續性總是環環相扣,唯獨篆書從秦漢之后至少有五百余年的明顯斷裂,而在盛唐這個時期又重顯身姿,既不是因為唐初發現了秦國的《石鼓文》,也不是因為它是一種可供選擇的美妙格式,而是盛唐博大沉厚的文化層次需要相對高雅的美學目標,需要在方寸之間表現活生生的藝術價值。但是,盛唐的篆書并沒有在文字上改換門庭去迎合皇帝的喜好,在對篆書抱著堅決維護的態度下,只對自身風格加以改革,以示它還不落伍,進而表現出新的突破。
盡管有人認為李陽冰的篆書沒有金文、《石鼓文》之樸茂渾厚,沒有李斯小篆的圓融挺勁,沒有漢篆的方整剛健,甚至連后代的摹刻也不如,但實際上這不過是借古人來壓唐人,用背負的傳統來規范唐人的創新,是因循守舊的心理反映罷了。篆書沒有其他書法藝術的社會功能大,藝術出新之難遠遠超過其他書體,因而在盛唐沃土中它的重振和突破是不朽的,在唐之后直到清代,篆書再也沒有興盛和創新,這本身也反證了盛唐篆書的獨特價值。
正因為盛唐具有無限開闊的天地,社會上逐漸形成一種崇尚書法的風氣。從千唐志齋這個書藝博覽館中不僅可以看到初唐秀美圓潤、剛健婀娜的書風,更可看到盛唐灑脫流暢、生動嫵媚、豐腴敦厚而渾圓奇倔的各種風格,勁力肅穆的篆書,豐滿淺近的唐隸,奔放不羈的狂草,風流秀美的行草,以及循規蹈矩的楷書,或步晉法,或開新則。雖然這些不都是出自方家名手,但那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的爭妍局面,顯示出那個時代書壇的光彩和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