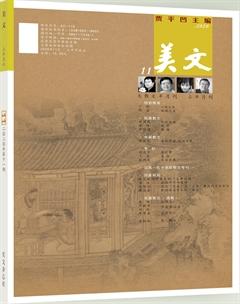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何云燕 壯族,廣西天等人,文學博士。廣西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2012-2013年美國波士頓大學“聯合培養博士”訪問研究員,2016年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訪學學者,2018-2019年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者,曾發表數篇散文作品。
一
離別的日子逼近,用特定的儀式跟劍橋告別似乎成了周圍人的一種默契。我選擇在劍橋大學中心做一次英文講座,講講自己的經歷和收獲,以感謝新職員與新學者中心那些自愿者的慷慨扶助。蘇(Sue)說一定要在我離開之前帶我去參加她們學院的高桌晚宴(High Table)一次。了解劍橋大學的人都知道正式晚宴(Formal Dinner)是這所全球頂尖大學的一個重要傳統,一般只有跟大學產生深度關聯的人才能參加。高桌晚宴則是正式晚宴的最高規格——只有正式教職員及其他們邀請的人才能參加,通常都是赫赫有名的教授們坐鎮。倘若哪個本科生或者研究生能在正式晚宴上被邀請到高桌去,基本就是被默認為得到了平日那些嚴苛教授們的認可和青睞了。
聽到這個消息,我心里充滿期待。心想,這才是最好的告別儀式!
蘇因為在瀕危語言研究上的卓越成就被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邀請去做資深研究員。初次見她是在一次中國學者沙龍聚會上。彼時沙龍是在鄭醫生家舉辦。曾經當選“中國十大科普醫生”的鄭醫生不僅醫術高超的麻利手腳讓大家贊嘆,而且其識人辨物的眼力也大家是公認的。所以,當一向笑盈盈、沉穩寡言的鄭醫生兩眼放光、嘴角抑制不住喜悅地向眾人介紹蘇時,我們都心照不宣地捕捉到蘇的到來有多么重要。她一言不發地坐在邊上聽大家討論,神情嚴肅,令人有些生畏。聚會結束時大家也識趣地相互點點頭微微笑道別。
第二次見面時彼此才熟絡起來。原來她是一個非常愛笑的人,笑起來非常爽脆,浸透著一種清澈透明的高興。蘇說上次剛剛到劍橋還在倒時差所以不大愛說話,然后又補充“不太熟的人也不太愛聊”。我喜歡簡潔的人,所以很快就喜歡上了這個愛笑的、頭發有些卷的大姐。平日里我們很少談論學術,只是閑聊。周末大家約著去倫敦看劇、去周邊小鎮踏青,她也樂呵呵地跟著。倘若遇上惱人的天氣,她就是從來不抱怨、總是安慰人的那位,以至于我經常忘了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學者,有時候就沒大沒小地開起玩笑。她偶爾會講些自己年少時的逃難經歷,輕描淡寫的,像是說別人的故事。
“您應該是一個大家閨秀。”她的從容坦蕩讓我很好奇。
“哪里,哪里。”她呵呵地笑
“那您的母親應該是一個大家閨秀。”我又問。
“沒有,沒有。”她呵呵、呵呵地笑。
這是我們常有的對話模式。我總認為,如果不是來到劍橋,我大概很少有機會跟這么可愛的人兒成為好友。在國內也許我們會相遇,但往往是會場上的一面之緣或點頭之交,即使相互添加微信之后也可能很快相忘于江湖。
二
蘇說要帶我去參加高桌晚宴,我欣然地接受,而后便安心地等待。
過不久,蘇發信息跟我確認月份。隔一段時間后,問要個人的基本資料,叮囑我準備好深色裙子。再過一陣,要補充研究方向的信息。突然有一個天很著急地給我發信息、打電話,說要確認一下我所在的英文系的準確英文名稱。最后終于敲定了二月份的第二個周四。路上偶遇的時候她告訴我:周四好,周四晚上是專門的外賓參觀夜(Visiting Night)。
期盼已久的周四終于到來了,我早早穿上提前準備好的黑色小裙,化好淡妝,披上黑色大衣。根據她的建議,我沒有帶上包包,把手機和鑰匙放入大衣的兜里,估摸著時間,蹬著皮鞋踏著暮色出門。走到莫德林學院西廂的時候離我們約好的時間還差五分鐘,等了一小會兒還沒見到蘇。于是就往前走一小段路到莫德林橋上,眺望學院給蘇配備的河畔住所,看到窗戶沒燈光猜想她應該出門了,又折回原點。沒過多久就看到蘇從古老厚重的大木門縫側身而出。她披著黑袍,膝蓋之下露出了裙角和中跟皮鞋。這儼然是我第一次見到她穿裙子的模樣。
“您穿裙子很漂亮啊!”我脫口而出,她呵呵地笑。隨即領著我穿過馬路走到東廂。
有時候真的不得不信冥冥之中的緣分。莫德林學院恰好在我租的房子附近,是我進入市中心的必經之路,所以便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學院。巧的是我第一次參加劍橋大學學聯組織的正式晚宴也是在這所學院。沒想到此次訪學唯一一次參加高桌晚宴也是在莫德林。臨別時再來,熟悉而陌生的感覺頓生——我熟悉這所學院的物理空間,但是未曾有機會深入了解這個學院的文化氣質。這個周四的晚上終于有機會了!
“我們先去聽音樂吧。晚宴七點半正式開始,但是我想讓你全程體驗一番,所以就讓你早點過來。等會兒聽完音樂之后有個餐前酒會,應該是去院長家里喝杯酒,之后再去餐廳。用完晚餐后,還會上二樓去喝茶,那會兒還有餐后水果和芝士。”蘇邊走便跟我解釋。
“在院長家里喝酒?!我能不喝酒嗎?我酒量太糟糕,抿兩口臉就紅,太尷尬了。”我有點擔心。
“沒事!應該還有其他飲料。有水和橙汁。”
三
我放心地跟著蘇去聽音樂。音樂會是在莫德林學院的教堂里舉行,所有的程序都是大家熟知的。唯一讓我覺得比較新鮮的是莫德林唱頌隊有不少女生,而且還有小提琴配樂——很多學院都是管風琴伴奏的。我機械地跟著整個儀式的引導站起來又坐下。他們說什么唱什么幾乎沒有注意,而是完全沉浸在一種昏黃、幽暗、崇高的光影和聲音里,續而被眼前的蠟燭深深地吸引了。
整個屋子是不透風的,把冬日的寒冷徹底阻隔在門外。屋里一排排的蠟燭被套入干凈透明的細長玻璃杯里。除了人的呼吸,我想是沒有任何其他氣體在屋里轉動的,可是眼前的三根蠟燭卻在玻璃杯里不停地扭動,宛如被囚禁的火龍幼子,永不停歇地抗爭。哦,這不是蠟燭而是燭光!可是這么高的玻璃杯壁圍著,屋里沒有一絲風穿過,這燭光舞動的力量從哪里來?是人的呼吸嗎?還是人躁動不安的靈魂映射之上?想起前些日子在劍橋大學老校(Old School)禮堂舉行年度校長論壇,作講座的是一個有爵位的教授、副校長,他講的是全球氣候變暖背景下的全球政治和經濟問題。講座后的招待會里,我們幾個到場的中國訪問學者圍著他問問題。中途被一個印度裔長相的女士打斷了一會兒。在這位女士道別的時候,這位副校長突然感嘆了一句:“似乎有一種力量撕扯著我們,要把這個世界撕裂開。”我是在轉身瞬間聽到的這句話,不免有些吃驚,至今都不知道他指的是脫歐還是其他國際事務。吃驚是因為這不是我第一次聽到類似的話語,最近一次是在劍橋人文社科跨學科研究中心參加會議時一位老紳士親口跟我說:“當今世界總是有一種無形的力量逼迫我們相互提防、相互怨恨。這種力量越來越強烈。我們該怎么辦呢?”我茫然不知所措,只能說:“也許是因為全球經濟整體下行的緣故吧。”“好吧。”老紳士對我的回應也表現得無可奈何。他的問題竟然困擾了我好一會兒,但很快就釋然了: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啊,我沒有能力去操這份心。
屋里的燭光不停扭動。我盯著最前邊的那一根看得很出神。這個燭心在急劇的舞動中被玻璃杯壁分成了三個光點,三個光點有規律地交叉扭動,分分合合,永不停息。我想起最令人心碎的燭光是茨威格《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
如今他躺在那兒,那個可愛又可憐的男孩兒,在他窄窄的兒童床上,就跟他死去時一模一樣,只是有人合上了他的眼睛,他那雙慧黠的深色眼睛,別人把他的雙手交疊在白色衣衫上,在床的四角高高地點著四根蠟燭。我不敢望過去,一動也不敢動,因為燭光若是搖曳,就會有影子掠過他的臉和他緊閉的嘴,就仿佛他臉上還有表情,而我會以為他沒有死,以為他會再醒過來,用他清亮的聲音對我說些天真溫柔的話語。但我知道他死了,我不想再望過去,免得我再一次懷抱希望,又再一次失望。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孩子昨天死了,如今在這個世上我還有的就只剩下你,就只有你,對我一無所知的你,你渾然不覺地玩樂,借著事物與人群來消磨時間。就只有你,從不曾識得我的你,我一直深愛的你。(姬健梅譯)
每次讀到這段話,尤其是讀到英譯版,我都感覺內心深處最柔軟、最脆弱的部分被扎上了無數刀。所以我現在很少去翻閱這小說了,它太令人憂傷絕望。現在的我喜歡莎士比亞在《麥克白》中的燭光:
“熄滅了吧,熄滅了吧,短促的燭光!人生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在舞臺上指手劃腳的拙劣的伶人,登場了片刻,就在無聲無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著喧嘩和騷動,卻找不到一點意義。”(朱生豪譯)
莎士比亞的這段話讓我覺得今夜的燭光真是太曼妙了,像極楊麗萍的舞蹈。我想只有楊麗萍這樣的舞蹈家才能跳出火的生命力,可以創造一切也可以毀滅一切。美到極致是恐懼和敬畏,恐懼和敬畏生命的短暫與無常。
四
“走吧!”不知過了多久,身旁的蘇把我從燭光中喚醒。我才注意到,音樂停了,祈禱的聲音停了,教堂里的人們紛紛往門外走。
我默默地跟在蘇身后,隨著人群移動。走到教堂大門的時候,我們遇上唱誦隊。這時我才看清楚他們的臉。大都是臉龐輪廓立體的年輕白人。走出教堂,年輕人的本性就釋放了,他們開始輕松自然地談笑起來,其中幾個人走進隔壁的房間拿起桌面上的準備好的香檳和紅酒。角落里的大笑三兩聲的起伏,但很快就散去。蘇叫住了其中一個發色比較深的白人女生,跟她確認當晚的安排,并為我們做了介紹。
“這女生人非常好,很能干,她在其他學院做博士,來我們學院做兼職。晚上還參與學院晚宴的一些安排工作。”蘇輕車熟路地引著我向右轉入一條漆黑的過道,邊走邊說。我右手扶著墻,小心翼翼地跟著她,生怕不小心踩空。穿過走道之后,我們向左轉,借著遠處的微光才知道我們來到了一個庭院的小花園。樹影幢幢如護衛為我們擋住冬夜漸冷的風。
我們走著,腳下沙沙聲響起。我這才接過話:“這女生看起來很年輕,就能在劍橋讀博士,而且邊工邊讀,真是很能干!”
“是啊,在劍橋讀博很不容易呢。”
“嗯。哎呀,這個小花園的路面都鋪上了沙子嗎?走起來有點意思,但就是不好快走。”
“是啊,他們也不怕下雨踩過之后會弄臟屋子。不過屋子門前有毯子。”
“我經常路過你們院長家門口。我發現他們臨街大門的內庭也都鋪滿了沙子,有好幾次想走進來,但是看到標著‘私人領地的字樣就不敢了。闖私人領地在美國是犯法的,若被屋主槍擊也是白白送命。還好,英國人沒有槍。英國人規矩多。”越走燈光越亮,我的話就多了起來。
燈光來自院長家的大門。單看外表,這房子沒有什么特別之處。門口沒有什么人接待,讓我有些不習慣。蘇則徑直地把我帶到挨著大門的一個小屋,讓我把外套脫下來。小屋里還有兩位老太太,打過招呼之后我就跟著她們排隊把衣服掛在墻上的掛鉤。
“我能把手機留在大衣兜里嗎?”我問蘇。
“沒關系,放著吧。反正又不允許照相。”
人陸陸續續地到來,屋里的走道開始被擠滿。放下外套和包包,大家很自覺地來到會客廳。院長的會客廳被一道巨型拱門分成了兩個部分,外廳被傳統的英式家具圍成一個大圈,墻上掛著各式各樣的油畫和相片。里廳放著一個巨大的桌子,鋪上桌布,擺著酒水飲料和零星小點心。我們都知道劍橋大學基本都給在任期間的院長們在各自的學院里配備獨立的生活空間,有大型的花園和房子,而且有專人專業管理。院長的家不僅僅是私家的居所,還承擔一定的公共服務功能,尤其是學院的重要社交服務。院長的家也就成了呈現學院風格的窗口之一。誠然,莫德林院長的家居裝飾也是精心布置的。
“院長在里面,我帶你去認識一下。”我跟著蘇走進了里廳,來到一個體型高大、滿臉胡腮、披著紅領大黑袍的先生面前。蘇跟他打招呼后簡單地介紹了我。院長一邊用很清晰的語音叫我的中文名字一邊跟我握手,然后問我來劍橋的原因和基本情況,數分鐘的交談他仿佛已經很了解我了,不得不暗自佩服——看來提前幾個星期了解要來客的信息這真是很好的主意。
見過院長,又認識了當晚學院的幾個負責人,包括教職工主任、校友主任等,她們不僅僅是學院事務的管理者也是各自研究領域的名家。之后我們就退回外廳參觀。外廳的鋼琴上擺著幾張家庭相片,我湊近觀察, 蘇也陪著過來。
“這是院長一家吧,他有幾個孩子?”我問。蘇說她也不知道。這時候一位女士笑盈盈地向我們走來。
“你們在研究我們的家庭相片嗎?”她先開口了,并且做了自我介紹,原來是院長夫人。她給我們介紹相片中的女兒和兒子。
“您就兩個孩子嗎?”
“噢,是的,兩個已經足夠我們操心了。我兒子學過中文。”看來院長夫人也得出來參與學院的社交工作,而且充分掌握均等分配時間與客人拉近距離的才能。為了不耽誤夫人的“工作”,我主動說:“您可以用我的英文名字Jackie叫我,我的中文名字對講英語的人來說太難了。有蘇在,我相信我一定有一個很美好的夜晚。您先去照顧其他客人吧。”
夫人離開后,我跟蘇說,我最近在做一個小的調研,我發現劍橋很多本科甚至博士畢業的女士生了孩子之后主動選擇做家庭主婦,因為她們覺得生活和工作一樣重要甚至比工作更重要。“你們院長夫人是家庭主婦嗎?”我問。蘇答:“我們院長很有名,他這么忙,估計他夫人也應該是家庭主婦。”等大半年之后,我們都回國了才發現這位莫德林學院院長夫人其實也是一個學者,經常到倫敦去講學。
五
基本上都拜見過院長及其夫人之后,眾人就由司膳官引導著,踩著沙沙作響的路穿過花園來到餐廳,先是進入一個燈光幽暗的小房間,宛如哈利波特電影里的小暗室。眾人不約而同地緘默不語,自覺地把隨身攜帶的大衣和包包遞給已經等候在此的穿著制服的工作人員,然后依照站立的位置先后進入大廳。
凝重的夜色中,餐廳大廳的光線尤顯微弱,但是很溫暖、很安靜。借著微光,我看到里面已經坐了不少學生。時光頓時回到初到劍橋之時的那次正式晚宴。那時我們是以學生的身份,在同樣的餐廳里坐著聊天,帶著抑制不住的好奇忍不住地四周張望,但又不敢挪動身子。一聽到兩聲鑼鼓就知道教授們要進來,大家馬上閉上嘴巴、老老實實地挺腰坐直,并向高桌的方向行注目禮。等教授們和客人都坐定、動手用餐之后大家才動起來,但依然是安安靜靜、規規矩矩地按“三道菜”的用餐秩序吃飯。等教授們起身要離開高桌的時候,大家放下手中刀叉,目送著那些“大人物們”移步往二樓的茶室。直到教授們的身影消失在二樓的門道里,大家才松一口氣,舉杯互敬,高聲談笑起來。
今天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彼時自己曾經坐過的餐桌,別有一番滋味。但沒有來得及仔細體會,餐廳的工作人員已經有條不紊、緊鑼密鼓地把頭餐、正餐、甜點一輪輪地送上來。吃的什么,我很快忘記,唯有“等右手邊的人先進餐”的規則留存腦中。餐后莫德林學院很貼心地贈送給每個人一顆印有其院徽的巧克力塊做紀念品。
吃飯的時間是有一定限制的。司膳官定然對此很有經驗,等大家基本品嘗過甜點后便搖鈴示意教授們和客人們起身上二樓。我們在幽光中穿過學生們的餐桌,只見學生們都放下了刀叉,靜靜地等待著教授們離去。我跟在蘇后面踏著木梯上樓。
“我剛才吃飯的時候坐在你對面,按規定等會兒在茶室我們就不能坐在一塊兒了。你要照顧好自己!”蘇拉著我,輕聲囑咐。
六
我們到了茶室門口,蘇看了看,說:“我坐在這門邊上,你到最里面去,坐在院長夫人旁邊吧。”我說好的,徑直走向夫人,夫人見到我,微笑點頭:“你好,Jackie,歡迎你來到茶室,你的晚餐如何?”我暗自吃驚,夫人竟然還記得我的英文名字,連忙回答:“謝謝,晚餐非常好。”她示意我坐在她右手邊的位置上。其他人也陸續走進來,自然而然地坐在臨近的空位上。坐定后我望了望蘇,她也一直在看著我,我們正好坐在長桌的一頭一尾,中間兩邊各隔著八個人的位置。桌上擺著幾個大燭臺,燭心靜靜地燃燒,幽幽地照著滿桌的水果、點心,幾個角落里還整齊放著幾瓶酒水。在昏黃的光中,蘇和我沖彼此笑了笑。
看到夫人在招呼剛剛入座的其他人,我就主動跟鄰座的女士攀談起來。女士告訴我她的先生在莫德林工作了快五十年,到如今已經退休十年了,今天是帶一個從法國過來的朋友體驗劍橋正式晚宴的,因為他們的朋友很好奇。“實際上那些不在劍橋大學工作的朋友們都很好奇,所以我們經常帶朋友來。很長一段時間來,我們幾乎每個月都來一兩次。你知道嗎?退休人員回來吃飯是免費的!當然我們要支付客人的費用。”鄰座的這女士是地道的英格蘭人,當她聽說我是來學習英國文學文化的,她似乎馬上有了使命:“你來到劍橋真是太棒了。”隨即滔滔不絕地介紹起周邊的風土人情。中間還不忘記提醒我:“我的侄女現在北京學習中文。”我盯著自己面前滿盤的各式各樣的芝士,一邊研究怎么吃一邊認真地回應她的熱情,頓時覺得平時嚴肅的英國人可愛之處就是只要打開他們的話閘他們也和北京人一樣能侃。
我們聊得正歡的時候,院長進來和大家一一問候,然后就在隔壁的圓桌入座。院長夫人乘著間隙把自己左右兩邊的人介紹相互認識。如此,坐在她右邊的我認識了坐在她左邊的一對夫婦。那對夫婦說自己是開寄宿學校的,主要客戶就是中國人。最初是在他們自己家里開辦,二十年前他們家就住著不少中國孩子。妻子把名片遞給我之后說:“中國的父母很勇敢,能把自己年幼的孩子獨自送到英國來上學,太了不起了。我自己就沒有勇氣把孩子單獨送到外國去。因此我必須認真地對待他們的孩子。所以他們很信任我。我們后來就開創自己的寄宿學校。現在有兩百多個學生了,當然他們都是從世界各地來。我們的管理很好。”
“兩百多個學生,你們太了不起了。我看到名片上寫著你們在南安普頓。你們的孩子在劍橋大學讀書嗎?”為了感謝她對華人同胞的善意,我也表達對她們的關切。
“我們有三個孩子,但是他們都還小。我們今天來劍橋是想捐贈。我們希望大學發展越來越好,我們才能有機會把孩子們送到好學校來。”
“Jackie,你在劍橋做什么研究?”這時,院長夫人問我。
“我要做英國文學文化研究。在劍橋英語系主要是做文學研究吧。”
“你研究哪位作家?”
“呃,我原來主要聚焦美國文學研究,準確來說是研究美國十九世紀的作家。現在剛剛開始系統學習英國文學,還沒有具體化到作家。當然我之前很喜歡狄更斯,但是不知道為什么最近突然覺得簡·奧斯丁很值得研究。問題是我之前不太喜歡奧斯丁啊!真是好奇怪。”說著說著,我竟然沉思了起來。
院長夫人點點頭,放下剛剛切好的藍芝士,柔和地對我笑了笑:“Jackie,也許是因為你發現外面的世界太大太紛繁復雜,你想退回(retreat)到內在世界,退回到你自己的生活空間里。”——這或許是我當晚聽到的最貼切的話。我對夫人的敬意油然而生。我想很多年后,我應該還能回到她跟我說這句話時的畫面。
七
不知過了多久,院長又走過來跟我們一一道別。“Yunyan(云燕),謝謝你今晚的到來。我們還有些事情要處理,我們先回去了。希望你能度過一個美好的夜晚。”
院長和夫人離開后,眾人漸漸散去了。蘇邀請我轉到二樓的其他房間去參觀。二樓同樣是別具洞天,我們倆猶如在宮殿里尋寶,探索莫德林學院教職工不同的活動室;參觀了一些古畫古書,還有林林總總的家具擺設。因為擔心回家太晚,很多有趣的物件來不及細細欣賞。
走出茶室門口,等候在外的工作人員很準確地把大衣遞過來給我。
“他們還把衣服送上來,我以為我們得自己回一樓后面那個小房間拿呢,問題是他怎么知道是我的衣服。”接過衣服,我轉身就用中文悄悄問蘇。
“可能是人不多了,也可能是他們訓練過真的記得。反正我來過這么多次,他們也沒有給錯過。”
“哎呀, 對了,你們院長好牛,竟然能用我的中文名字跟我道別,記性也太好了吧。”
“呵呵,他們早就做足了功課,所以才早早問要你們的信息,而且要的信息還是比較詳細的。”蘇樂了。
“還有啊,你們院長夫人有透視功能,竟然一句道破我困苦已久的感受……”下樓的時候,我按捺不住地一直跟蘇感慨。
走出餐廳大樓,打開手機看時間,已經十點了。于是趕緊跟蘇走出大門。蘇問我:“今晚感覺如何?”
“非常好,很值得體驗。”
“希望你覺得值得。在二樓茶室的時候我一直往你那邊看,擔心聊得不好你會覺得煩悶。后來我看到你聊得很開心,就放心了。其實,聽音樂的時候我也怕你坐不住,沒想到你坐在那里一動也不動。”
“嗯。非常有儀式感,高桌的體驗和普通正式晚宴真是很不同。”
“我們學院的晚宴據說是劍橋保存傳統最好的。你有沒有注意到,整個晚宴過程都是只有蠟燭照明,沒有任何電燈。”
我恍然大悟:“對啊,怪不得我總覺得走哪兒、哪兒都是幽幽暗暗的。哈哈!還有,我整個晚上都想不起手機了,把手機放在大衣兜里,嚴格遵照不允許拍照的規定。”
“老外似乎不像咱們這么愛照相。其實在二樓茶室可以拍照的。”
“沒關系,我打開了全身體驗系統,都拍在腦子里了。”
八
跟蘇道別之后,我獨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路上行人很少,皮鞋跟打在石板路上的聲音分外清晰。更深露重,寒風撲面而來,情緒一下子沉下來。
回家途經一個丁字路口,小小的路口三邊聳立著三個教堂,據說分別是天主教、基督教和猶太教。平時路過,也沒有見太多人出入其中。記得數年前在美國求學的時候,一位文化研究教授所開設的課程題目就是“西方衰老的教堂(Aging Churches)”,大意是當代西方去教堂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只有老者在堅持傳統的宗教儀式。在劍橋遇上了研究經濟學的張家衛教授,記得他說過:科技主義是現在年輕人的新宗教,AI和生物高科技才是年輕人的信仰。
劍橋小鎮冬日十點之后,人影消散,喧聲盡逝,遠近處哥特式教堂建筑令夜色顯得愈發神秘莫測。萬物靜謐如謎。走在這大街上,內心的迷惑掩藏了獨自夜行的焦慮。在劍橋近一年,我絕少在這么晚的時間行走在外。或許是偶有車輛經過、遠處有行人身姿以及周邊房屋燈火的光亮給我勇氣,此時此刻我竟然如此安然地行走在沉靜的夜晚之中,唯一相伴的是自己的腳步聲。
過了回家途中唯一的紅綠燈,就是一個私人宅院改造成的小型博物館。櫥窗里有一幅顯眼的伊斯蘭女子圖像。不知道何故,想起前些日子見過的一位女士——科索沃前總統阿蒂費特·雅希亞(Atifete Jahjaga)。她應邀到劍橋學生聯合會做講座。聽說她35歲當選總統,而且是在科索沃局勢尚未完全穩定的情況下當選。一個女子能在民族和宗教沖突此起彼伏的國家當選總統,不得不令人欽佩。此外劍橋學生聯合會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圈子,這次是不多見的開放講座,我和好友決定前往參加以一睹芳容、一探究竟。講座上雅希亞女士說自己彼時是選舉出來的世界上最年輕的總統,在任期間非常關注民生,經常走訪戰爭中遭受傷害的女性,鼓勵她們發出自己的聲音,把自己的苦難和屈辱講出來,以抵抗和防止悲劇的再發生。在場的劍橋學子踴躍提問,甚至還有女生問她如何平衡好家庭和事業的關系。雅希亞女士的英語雖然有濃重的口音,但是英語極其流利。“我猜她應該是在英美國家受的教育,即使是出生于科索沃,但是應該不是普通人家。”我對好友感慨。好友不置可否。
一個小時的講座很快就結束了,我們下樓的時候恰好和雅希亞女士擦肩而過,我突然想問她一些問題,可是說出來的卻是:我可以不可以也跟您照相。她笑著說:當然,我很高興。跟第一個要求者合影完畢后,她竟然找到了被人群擠開的我。不知是因為我和朋友是當晚極為少數亞裔面孔的緣故還是其公眾溝通的本能使然。
合影的時候我沒有一絲興奮。或許是在擦肩而過的那一瞬間,我已經找到了答案。我明白,這位從小接受良好的歐美教育熏陶、沒有遭遇過底層人苦難的雅希亞女士已經在自己認識和能力范圍內做了她最大的努力。我又有什么資格去問詢其他問題呢。事實上,我很懷疑自己疑問的合理性,因為作為一個學人我深知世界上很多偉人的誕生都是數代甚至數十代家源的積累沉淀,底層人出頭則是鳳毛麟角。
看到櫥窗里蒙著面紗的伊斯蘭女子畫像。我知道,此時此刻在深沉夜色中信步的自己是何其幸運。我生長在一個偏遠的壯族山村。兒時的小伙伴在我剛剛踏入高中的時候已經被逼遠嫁他鄉了。幸運的是我們的時代日漸富足。當我還在劍橋訪學的時候,兒時的好友已經當上了奶奶。她十六歲嫁到南寧周邊一個很貧窮的村子,在后來的20年里,她靠自己的奮斗把自己的家搬到這個城市的中間。對我而言,她的故事一點都不遜于雅希亞女士。
抬頭仰望這夜的劍橋天空,和兒時自由貪玩到半夜見到的夜空是沒有差別的。我猛然很好奇:是什么樣的力量把我從壯鄉小山村帶到這個舉世聞名的文化圣地的?為此,命運要交給我什么任務?還是僅僅讓我體驗與感受這個奇妙的世界?我馬上要踏上歸程了,回歸生長的那片土地上,心中既憧憬又惶恐,因為我最怕辜負這冥冥中的美意。
說來也真是奇妙,我是來到劍橋之后才更了解徐志摩。從前我不喜歡詩人徐志摩,但是現在對學者、文化人徐志摩充滿了敬意。他說: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