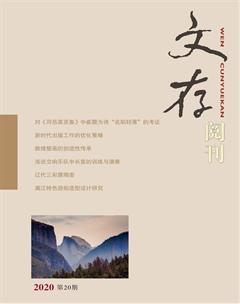精神分析視野下的《金色筆記》考辯
摘要:萊辛早年的成長經歷,特別是她母親對孩子的過高期望和控制欲帶給萊辛終生的傷害和恐懼,她總是試圖逃離,逃離她母親的控制,逃離婚姻和孩子,這些使她在與人的交往中陷入深深的危機。為了緩解精神危機,她接受了心理治療。這些在其作品《金色筆記》中都有體現,它不僅影響到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也影響到情節結構。萊辛在作品中真實記錄了自己接受心理治療的體驗和感受。她更青睞于榮格的理論,從中受益頗多,但也對其充滿質疑和反思。
關鍵詞:多麗絲·萊辛;《金色筆記》;精神分析;心理治療
萊辛的《金色筆記》主要探討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英國城市男女對婚姻愛情的理解,但它的探索是豐富而復雜的,不僅僅局限于這些方面,本文從精神分析角度解讀《金色筆記》,探索作者早年成長經歷對其寫作《金色筆記》的影響,以及在文本中作者如何運用精神分析理論探索人物的潛意識,并通過它對心理分析進行反思。
一、成長經歷對萊辛創作《金色筆記》的影響
萊辛出生于伊朗,成長在非洲。她的母親出生于英國中產階級,受到良好的教育,因為戰亂到非洲謀生,和丈夫一起經營一家農場。雖然生活不盡如人意,充滿了沮喪的氛圍,但她依然保持著英國中產階級的文化和理想,把自己的希望幾乎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她把精力熱情地投入到對孩子的教育中,希望他們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成長。過度的期待和控制激起了子女的反感,萊辛從小養成了叛逆的性格,她一直都在逃離世俗賦予一個女性的常規的生活,避免變成像她母親那樣的人。“她十四歲就逃離了學校,十五歲就逃離家庭,二十四歲的時候,她又要逃離丈夫和兩個孩子。”[1]110萊辛離婚后再次結婚,又再次離婚。婚姻不是因為愛,而是因為其它,或許是想從父母的家里逃出來,或許是因為政治目的,但無論因為什么,她都不會把它們看做最后安全的港灣,她會一直逃離下去,因為她最害怕被人束縛住。她害怕婚姻中的丈夫和孩子像她的母親那樣控制她,使她失去自由,失去自我。她要獨立自由的自我,要成為自己,就必須逃離這些束縛。
這是萊辛的宿命,她和任何人,包括親人和情人都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她總給人疏離、謹慎、冷靜的印象,她的內心強悍而獨立,但也脆弱。在人生孤獨的旅程中,她靠寫作來自我救贖,從中尋求突破口釋放自己內心的積郁。寫作陪伴她一生,是她最忠實的伴侶,它慢慢療愈了她內心自兒時起就產生的焦慮和恐懼。
作家的早年成長經歷大都會對他們的寫作產生巨大的影響。萊辛的原生家庭塑造了她叛逆狂野的孤傲性格,為了治愈內心的孤獨和痛苦,她找到了文學這個最好的療愈手段。她通過文學思考心中的困惑,思考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從而更好地認識自我認識社會。因此,她的作品都打上了她自身艱難成長的烙印。
《金色筆記》中的主要人物安娜就有萊辛自己心靈的影子。安娜與周圍人的關系像極了萊辛與親人朋友的關系,她也離了婚一個人帶著孩子孤獨地生活。她也通過寫作謀生,尋求精神的獨立和自由。安娜的內心充滿了混亂和各種矛盾,內心時常會因為和男人的關系而緊張焦慮。她和情人邁克爾同居,但她始終沒有安全感,活在惶恐之中。她對他人沒有信任,她心思過于敏感,也許正是因為此,對方離開了她。被拋棄后,她幾乎瀕臨崩潰,不得不去向心理醫生尋求幫助,治療持續了好幾年。她后來和男性的交往也很難深入,總是冷淡隔膜,更多地體驗到失望、焦慮和痛苦,而不是和諧和幸福。
安娜的形象以及她的人際關系模式都有萊辛自己的影子,她通過記錄和創作展示內心,梳理混亂的情緒,思考人生的意義。
《金色筆記》中其他的人物和人際關系無不如此,婚姻中的伴侶,或非婚姻束縛下的情人們,他們的關系都淺顯冷漠,沒有溫情和信任,他們都痛苦、孤獨,獨自苦苦掙扎,脆弱無助,無法從他人那兒獲得安慰和幸福。這些都來自于萊辛自己的生命體驗,早年原生家庭的過多干預和控制帶給她的恐懼伴隨她一生,使她不能和他人建立深刻的聯結,獲得情感的滿足。
二、《金色筆記》中的心理治療
《金色筆記》中的安娜陷入精神危機后連續幾年看心理醫生,接受心理分析治療。萊辛自己也接受過三年左右的心理分析治療,她通過作品記錄了這段經歷,并對它進行了思考。
萊辛1948年離開非洲到了倫敦,她離開非洲應該是想更遠地逃離家庭和束縛,獲得更大的自由空間。但是三年后,她的母親寫信給她,要來倫敦和她一起生活。“這封信直接讓萊辛病倒在床,以此逃避會吞噬她的一切。”[1]220為了度過這場精神危機,萊辛接受了心理治療。“他母親在倫敦的四年里,萊辛有三年的時間,每個星期都要到蘇思曼夫人那里去兩到三次。萊辛覺得,如果沒有這些理療的話,她早就被母親強悍到無法忍受的存在壓成了碎片。”[1]221心理分析治療幫助她獲得內心的平衡,度過了危機。“萊辛將這個過程看做是對自我的救贖。”[1]221
萊辛的心理分析醫生蘇思曼夫人是榮格心理分析的忠實擁護者。萊辛也青睞榮格的理論,他的理論對萊辛產生了巨大影響,她認為“榮格的心理模式比弗洛伊德的更具有吸引力。”[2]6因為弗洛伊德“比榮格更關注個人,而榮格的集體無意識把視野拓展到了全人類。”[3]51
萊辛在《金色筆記》中通過人物記錄了自己對榮格精神分析的體驗和探索。安娜一周兩三次去看心理醫生馬克斯太太,持續了幾年。他們一起探討安娜的夢,通過夢對人的無意識進行探討。這些夢是理解萊辛作品的重要方面,我們很難說這些夢都是人物安娜做的夢,因為安娜這個人物本身是虛構的,也不能肯定它們都是萊辛本人曾經做過的夢,它們很可能來自萊辛的虛構。萊辛虛構這些夢為了什么?也許她希望通過夢更深入地探討人物的深層心理,也表明萊辛受到了心理分析學派的影響,對它們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在《金色筆記》中,安娜對心理醫生講述夢,自己也分析夢。心理醫生更多的是個傾聽者,偶爾說句話或點點頭,她的工作中心似乎主要是為了幫助安娜恢復寫作能力,因為她熱愛文學藝術,傾慕安娜的寫作才能。安娜概括自己的夢是“缺乏感情” [4]227她覺得自己最主要的問題是“不能深切地感覺任何東西” [4]229,原來豐富的感覺喪失了,這讓她恐懼。
安娜會見心理醫生時總是長篇大論地和對方辯論,她相信自己釋夢的方式,她更強調夢的非個人性,也就是榮格所說的“集體無意識”,夢不僅僅是純粹私人化的,不僅僅和欲望有關,而是和更復雜的歷史文化積淀以及社會生活相關。萊辛分析夢,更多地運用了榮格的“原型”意象,把它們當作理解人物和社會的一種象征。《金色筆記》中安娜的夢多次出現這樣幾個意象:“邪惡的花瓶”、“殘酷無情的丑矮人”、“善良的女巫”,安娜給花瓶和丑矮人命名“那是有關毀滅的噩夢,……是關于惡意和怨恨的法則的——那是種以惡為樂的法則。”[4]471
這些噩夢多次在安娜的夢里出現,大概六七次之多,花瓶帶有破壞性,“它癲癲狂狂又趾高氣揚地蹦跳旋舞,顯得毫無理性,冷酷無情,不僅威脅著我,也威脅著一切活著的生命。”[4]471又丑又矮的老頭“不住地陰笑,傻笑,或竊笑,顯得丑陋,卻生氣勃勃,強健有力,而且,他所代表的純粹是惡意、怨恨,以惡為樂。”[4]471每當安娜感到焦慮,內心充滿矛盾和混亂的時候,她就會做這個噩夢,她被這種無法控制的充滿毀滅性力量的夢魘所困擾。而當后來夢中的惡意法則以人的面貌出現時,她感覺更加可怕。因為“把那股可怕的駭人的力量約束在一種與神話或巫術有關的形體內,就安全得多了,而若讓它逃逸出來,變得無處不在,化身為人,此人又有權力來擺布我,那就太可怕了。”[4]472
后來她和美國人納爾遜交往時又做了這個噩夢,在這個夢中,她擔心自己變成邪惡的花瓶,變成丑老頭,變成巫婆。
這個噩夢貫穿安娜若干年的生活,它們是惡的象征,是一種具有毀滅性的神秘力量,起初安娜把它們和神話聯系起來,與原始的神秘力量聯系起來,后來她慢慢意識到它還是現代人的象征,甚至包括她自己。她解釋夢,不僅僅把它們與自己的私人生活相聯系,還與遠古神話原型,以及現代社會人的空虛焦慮相聯系。她與心理醫生一起探討人們內心的善和惡,馬克斯太太提醒她關注人內心善意的建設性力量,安娜在夢中也多次夢見馬克斯太太,她是“善良的女巫”的原型。
三、《金色筆記》對精神分析的反思與質疑
萊辛曾說,“我認為榮格的觀點就本身來說還不錯,但他的思想來自于那些眼光更深遠的東方哲人。中世紀的伊本·阿拉比和噶扎里對集體無意識或什么,就比榮格等人具有更先進的觀念。”[3]52后來萊辛意識到榮格理論的局限性,轉向了蘇菲主義,而且被卷入了反精神病學運動,她被人認為是心理分析學派的敵人。
在《金色筆記》中,安娜接受心理分析治療時,總是帶著審慎的挑釁的目光,有時候甚至是充滿敵意的。她說馬克斯太太總是聽到符合她的理念的陳述就微笑,不符合她的理論時她就皺眉。安娜反對馬克斯太太依照自己的理論給她強行貼標簽,她對任何理論和學說都抱著質疑和審慎的態度。她在和對方交流時熱衷于表達自己的觀點,和對方進行辯論,并指出對方的不足。萊辛通過安娜表達了自己對心理分析的質疑。
參考文獻:
[1]卡羅來·克萊因.多麗絲·萊辛傳[M].劉雪嵐 ,陳玉洪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
[2]Shadia S.Fahim. Doris Lessing :Sufi Equilibrium and the Form of the Novel. London :St.Martins Press,1994.
[3]王麗麗. 多麗絲·萊辛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4] 多麗絲·萊辛.金色筆記[M].陳才宇,劉新民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作者簡介:
胡波蓮(1973—),女,漢族,湖北江陵人,湖北工業大學外語學院,講師,碩士學位,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及歐美文學.郵寄地址:湖北工業大學外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