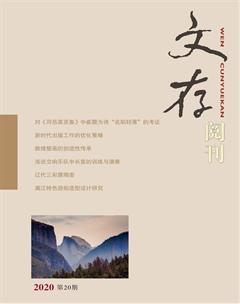《南方車(chē)站的聚會(huì)》
李穎
摘要:本文試圖通過(guò)對(duì)影片《南方車(chē)站的聚會(huì)》中男女主角的生存境況、行動(dòng)邏輯等進(jìn)行綜合剖析,闡釋影片中主人公悲劇結(jié)局的深層哲學(xué)原因,并引申至處在每個(gè)身處消費(fèi)社會(huì)的個(gè)體所面臨的愛(ài)欲困境,資本在消除一切差別性的同時(shí)空前的填充了人們對(duì)于愛(ài)欲的同一性想象,人們沉溺自我,愛(ài)欲死亡。
關(guān)鍵詞:南方車(chē)站的聚會(huì);資本;愛(ài)欲
引言:阿蘭·巴迪歐在評(píng)價(jià)德國(guó)哲學(xué)家韓炳哲的作品《愛(ài)欲之死》時(shí)談到“當(dāng)今社會(huì)越來(lái)越像一個(gè)同質(zhì)化的地獄,而愛(ài)欲的經(jīng)驗(yàn)不在其中。個(gè)體的內(nèi)在危機(jī)在于,一切事物均成為被消費(fèi)的對(duì)象,從而毀掉了愛(ài)欲的渴望。”這句論斷亦揭示了影片《南方車(chē)站的聚會(huì)》中角色悲劇性命運(yùn)的根源:個(gè)體在對(duì)幸福的追求中被金錢(qián)所遮蔽從而使得每一個(gè)選擇的判斷依據(jù)發(fā)生偏差,最終親手建構(gòu)了令人嘆息的命運(yùn)。男主角周澤農(nóng)自我獻(xiàn)祭式的自首,劉愛(ài)愛(ài)在愛(ài)欲和金錢(qián)中的反復(fù)猶疑以及楊淑俊內(nèi)心對(duì)于舉報(bào)款“得”與“不得”的激烈博弈。這諸多表面矛盾的背后深藏著資本世界社會(huì)意識(shí)中的“幸福”與真正的“幸福”之間的根本對(duì)立,每一個(gè)主角在奮力追逐前者的過(guò)程中無(wú)意識(shí)地與后者背道而馳。
一、“正直的犯罪者”
周澤農(nóng)無(wú)疑是這部敘事片最核心的角色。他自身攜帶著宿命的限定性,雖然是社會(huì)底層卻并非是好吃懶做的標(biāo)準(zhǔn)底層符號(hào)化形象。作為一個(gè)中年人,他卻有著不合時(shí)宜的少年血性,自身又背負(fù)著作為中年人的社會(huì)性責(zé)任。這種棱角使角色充滿張力卻造成了家庭的支離破碎。而遭對(duì)手暗算死里逃生卻失手殺死警察的事件遭遇又規(guī)定了他的脆弱。與健壯身體所對(duì)應(yīng)的,是他極易被摧毀的命途。在國(guó)內(nèi)的電影語(yǔ)境中,人物的此開(kāi)端也直接表露了故事結(jié)局,死亡是他唯一的歸屬。因此,影片最本真的情緒氛圍是一種困獸之斗的悲涼與逃無(wú)可逃的絕望,他所有為了抵抗的行動(dòng)的底層都是最深的消極性與否定性。手下兄弟因自身的比拼承諾而死,丈夫與父親雙重身份的失職造成了周澤農(nóng)社會(huì)性身份的湮滅。在消費(fèi)主義背景中,唯有金錢(qián)是他一切的救贖,金錢(qián)亦成為其追求的悖論。為了物質(zhì),他走上犯罪之路,但他的行動(dòng)舉止間卻充斥著一股子俠氣,包括他決定以自己為妻兒換取30萬(wàn)的線索費(fèi)總是有些舍生取義的意味。這位“正直的犯罪者”,他的行為與目標(biāo)卻處在兩個(gè)極端,極度對(duì)立。倘若他不以追求金錢(qián)為目的,圍繞他的,就是另一套生活邏輯了。這不僅是周澤農(nóng)單一層次群體的生存困境,甚至也不僅是當(dāng)代中國(guó)底層大眾的困境,而且是如今的狀況,是人類(lèi)面對(duì)人生概念的模糊性與采取行動(dòng)的具體性的矛盾,是確定性行為與不確定性結(jié)果的失控。
二、“脆弱的自我保護(hù)者”
影片文本的敘述人毫無(wú)疑問(wèn)是劉愛(ài)愛(ài),陪泳女的身份好似一把無(wú)形的錘子在不斷敲擊她瀕臨瓦解的靈魂。與此相呼應(yīng)的,金錢(qián)是她的唯一可能的保護(hù)罩,男性角色無(wú)法帶給她持久的安定,周澤農(nóng)賜給她片刻的歡愉后又用金錢(qián)打破了她的幻覺(jué),她赤裸地意識(shí)到自己身份的不堪,甚至低于殺害警察的兇手。而隨后劉愛(ài)愛(ài)所遭受的性暴力又徹底摧毀了她對(duì)于男性的想象。這些境遇,將她推入了對(duì)物質(zhì)的追求。如果情感是虛無(wú)與不確定,那么她便選擇物質(zhì)這種實(shí)在,并以此成為她抵抗世界的盾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周澤農(nóng)作為男性象征著資本邏輯的效率與權(quán)力,他目的的達(dá)成卻是劉愛(ài)愛(ài)這個(gè)柔弱的女性角色來(lái)實(shí)現(xiàn)。這不可謂是另一種女性意識(shí)的書(shū)寫(xiě),他身邊幾乎所有的男性角色都因?yàn)檫@筆舉報(bào)費(fèi)背叛他,給他內(nèi)在支撐的,都是女性的力量。
尤其是他目的本身就是為了妻子楊淑俊。妻子形象很明顯具備某些“傳統(tǒng)中國(guó)美德”,她堅(jiān)忍不拔,默默守候,在丈夫角色缺席五年的情況下依舊照看家具店并撫養(yǎng)兒子。即便她如此堅(jiān)韌,命運(yùn)亦緊緊依靠著男主人公。這個(gè)角色更像是男主人公救贖自己的解藥,在影片中或者在這個(gè)故事中,她和男主角周澤農(nóng)的愛(ài)欲始終缺席。表面看來(lái),周澤農(nóng)是要給她帶來(lái)“更好的生活”才背離她,但進(jìn)入更深的內(nèi)里,遠(yuǎn)離與拋棄是同一行為的“一體兩面”。如果說(shuō)周澤農(nóng)被射殺的結(jié)局是這場(chǎng)群體暴力的顯性承擔(dān)者,那么作為妻子的楊淑俊以及被誤殺警察的妻兒則是暴力的隱形承擔(dān)者,以一種緩慢而又持久的方式。
三、“毒藥”與“解藥”的身份迷思
影片中劉愛(ài)愛(ài)去找楊淑俊并告知她周澤農(nóng)要見(jiàn)她一面時(shí),楊淑俊有句臺(tái)詞:“他說(shuō)要去賺錢(qián),一走就是五年”。話中所提及的“賺更多的錢(qián)”其實(shí)是資本世界給與人們的誘惑,它與網(wǎng)絡(luò)社交平臺(tái)相融合,將極少部分“有錢(qián)人”的生活展示暴露于大眾眼前,借助虛假幻象的同時(shí)配合消費(fèi)主義的話語(yǔ)來(lái)建構(gòu)起物欲社會(huì),刺激大眾并使其進(jìn)行自我剝削。相較于資本家對(duì)于勞動(dòng)者的剝削,這種剝削往往被受剝削主體內(nèi)化為自我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將其看作是追求成功的唯一路徑。在當(dāng)今數(shù)字化社會(huì)的表象之下,資本,或者說(shuō)金錢(qián)成為唯一的尺度。人在其中被擠壓、被考量而難以收獲真正的愛(ài)欲。如同韓炳哲認(rèn)為當(dāng)下人們執(zhí)著于成功便會(huì)加劇自我束縛,他者無(wú)法顯現(xiàn),愛(ài)欲隨之消失。“當(dāng)今世界,自戀主體的核心是追求成功”,成功可以通過(guò)確認(rèn)“我”的成績(jī)而與他者分離,他者就成了“我”的參照物,這一獎(jiǎng)賞性的邏輯將自我更加牢牢地編織在了自我的主體之中,使得自我與愛(ài)欲步步遠(yuǎn)離。”
四、結(jié)語(yǔ)
資本主義社會(huì)中的一切異質(zhì)現(xiàn)象的原因來(lái)自于其一致性:金錢(qián)使得一切沒(méi)有任何不同,它消除了事物本質(zhì)上的差別。[1]這也是影片悲劇性的根源所在,金錢(qián)在主人公心中是一切抽象概念的本質(zhì)表現(xiàn)與具象身份,它是男主人公失諾的丈夫與缺席的父親身份的同一性補(bǔ)償,是女主人公誠(chéng)信的證明與衡量,是二人的“愛(ài)情替身”,是兩個(gè)女性角色結(jié)契的抵押物,是誘惑亦是背叛,而在影片的社會(huì)層面也是公權(quán)力實(shí)施正義的手段。
這也是當(dāng)前個(gè)體生存所面臨的具體困境,人類(lèi)生活的核心是對(duì)愛(ài)的追求。可當(dāng)下的人們卻在愛(ài)中感受到的疼痛越深。資本的介入下,人類(lèi)的本質(zhì)追求被金錢(qián)與成功所籠罩,在此背景下的人們誤以為追求后者便能達(dá)到幸福彼岸,殊不知這樣卻走向了名為“自我”的空間。這種追求愈極致,自我的束縛便愈發(fā)牢固,最終墮入“自戀”式的憂郁癥無(wú)法掙脫而消亡。而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高度發(fā)達(dá)帶來(lái)想象力的無(wú)限填充。人們從自我出發(fā)對(duì)愛(ài)進(jìn)行想象,這種想象又并非源自主體,而是被資本牽引具備著特定的指向性。這種由資本制造的想象無(wú)法產(chǎn)生真正的愛(ài),只會(huì)制造無(wú)數(shù)同質(zhì)化的客體。
參考文獻(xiàn):[1]韓炳哲(德),宋娀(譯).愛(ài)欲之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