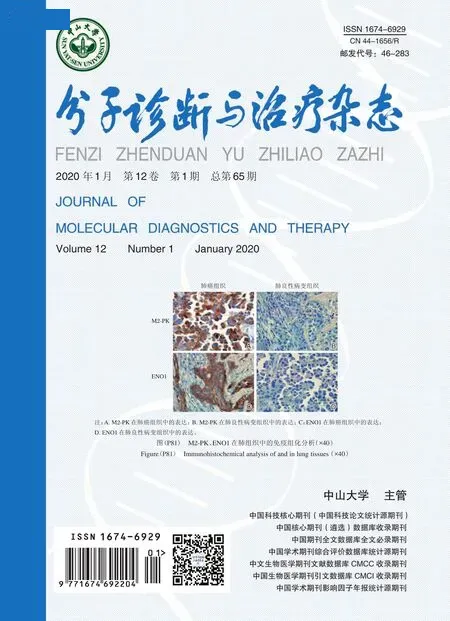原發性肝癌的分子診斷標記物研究進展
王凱 高帥
原發性肝癌是目前我國第四位的常見惡性腫瘤及第三位的腫瘤致死病因,嚴重威脅我國人民的生命和健康[1]。在我國,肝癌的高危人群主要包括: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和(或)丙型肝炎病毒、長期酗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食用被黃曲霉毒素污染食物、各種原因引起的肝硬化以及有肝癌家族史等的人群,尤其是年齡40歲以上的男性風險更大。外科手術治療是肝癌的主要治療方式之一。然而,大部分患者確診時已達中晚期,能獲得手術切除機會的患者僅有20%~30%[2]。對肝癌高危人群進行篩查,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小肝癌,是提高肝癌療效的關鍵。影像學檢查和血清分子診斷標記物是當前肝癌早期篩查的主要手段。影像學檢查主要包括B超、CT和磁共振等,通過直觀的肝臟占位性腫瘤包塊來判斷肝癌[3]。分子診斷標記物的檢測在原發性肝癌的篩查、早期診斷、預后判斷、復發檢測等發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和人類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等基礎學科向癌癥研究領域的延伸,肝癌分子診斷標記物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進展。本文將對近年來肝癌分子診斷標記物的研究做一綜述,以期對后期的臨床工作和科學研究提供指導。
1 肝癌相關基因
正常細胞的生長與增殖受兩大類基因調控。原癌基因提供正向調控信號,其可促進腫瘤細胞生長和增殖,并且阻止其發生終末分化傾向。抑癌基因提供負向調控信號,促使細胞成熟、終末分化和細胞凋亡。正常情況下這兩類信號保持著動態平衡,精準地調控細胞增殖和成熟。一旦這兩類信號中有一類信號過強或過弱均會使細胞生長失控而導致惡變。研究顯示,多種致癌基因參與了肝癌的發生、發展。這些基因改變與腫瘤抑制基因、癌基因、發育途徑的激活、生長因子及其受體相關,導致肝癌在細胞水平上保持異常高的復制水平,并使細胞避免凋亡的過程。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基因如PTEN基因、p53基因、IGF-2基因、TGF-α基因、c-myc基因、ras基因等,直接參與介導肝癌的發生、發展,并可作為肝癌早期診斷的特異性分子標記物[4]。Chen等人的研究中發現,大約50.3%的肝癌組織中可檢測到PTEN基因的低表達,與CD133、Ep CAM和CK19的高表達呈正相關。PTEN基因低表達是肝癌復發和總體生存率的獨立預測因素[5]。Liao等人通過加權基因共表達網絡研究發現,P53基因相關信號通路是導致乙型肝炎相關肝癌發生、發展的核心通路之一[6]。另一項研究顯示,c-myc可與HBx協同誘導非經典前折疊素RPB 5相互作用因子1(URI1)蛋白的表達升高,從而促進原發性肝癌的發生、發展[7]。Ha等人的研究中,IGF-2介導的E-cadherin蛋白缺失是導致小鼠肝腫大和肝癌細胞異常生長的關鍵因素。HBx誘導的IGF-2是可作為肝癌的潛在生物標記物,也是肝癌的治療靶點之一[8]。
2 DNA甲基化標記物
表觀遺傳學是指非遺傳改變(DNA甲基化、組蛋白修飾以及miRNA等非編碼RNA等)對基因表達調控,這種調節不依賴基因序列的改變且可遺傳,其中DNA甲基化是最常見的表觀遺傳現象。DNA甲基化是表觀遺傳學的重要調控機制之一,它是以S-腺昔蛋氨酸為甲基供體,在DNA甲基轉移酶(DNMT)介導下,將甲基基團轉移到DNA某些堿基上的過程。DNA甲基化多發生在CpG島上,是一種轉錄水平的DNA修飾方式,它能調節基因表達,并且在維持細胞正常分化、疾病的發生和發展中起重要作用。基因啟動子區域的DNA甲基化可抑制基因表達,在惡性疾病的早期診斷、風險評估、早期復發預測、治療反應監測及預后判斷中發揮重要作用,是目前的熱點研究方向。異常的DNA甲基化位點已經成為惡性腫瘤最有前景的分子標記物之一[9]。
有研究發現,基因組中常見的重復序列如LINE-1和Alu在肝癌患者中存在明顯的甲基化異常,或可作為肝癌診斷的標記物和治療的靶點[10]。我們的研究也發現,原發性肝癌具有特異的基因甲基化特征。在一項研究中,我們分析了178例手術切除的肝癌組織和20例正常肝組織中TFPI2基因的甲基化狀況。結果顯示,TFPI2基因在肝癌組織中的甲基化率為44.9%,癌旁組織中的甲基化率為10.7%,正常肝組織中的甲基化率為5.0%。同時,TFPI2基因甲基化與腫瘤復發和預后差明顯相關[11]。另一項研究中,我們分析了血清游離DNA中IGFBP7基因的啟動子甲基化狀態,結果顯示,肝癌患者血清游離DNA中的IGFBP7基因存在明顯的甲基化,IGFBP7基因甲基化與肝癌患者氧化損傷狀況、術后總體生存率及早期復發率有關[12]。聯合應用IGFBP7基因甲基化和AFP用于肝癌診斷時,其診斷效能明顯高于單獨應用AFP[13]。我們進一步分析了肝癌患者外周血單個核細胞中基因的甲基化狀況,結果顯示,肝癌患者外周血單個核細胞中NKG2D基因啟動子區域程度明顯高于慢性肝炎患者和正常對照者,NKG2D基因可作為肝癌診斷的良好生物標記物[14]。
3 miRNA
微小RNA(microRNA,miRNA)是一類內源性短鏈(17-25個核苷酸)非編碼RNA,其可以與信使RNA(messengerRNA,mRNA)的3’非編碼區結合誘導其降解。目前已有約500個miRNA基因被發現,其具有廣泛的生物學功能,可以調控細胞重要的生理過程。miRNA既可以作為原癌基因,也可以作為抑癌基因行使功能[15]。在肝癌中,miRNA參與調節細胞增殖分化及凋亡、上皮間充質轉化、轉移、血管新生等腫瘤相關病理過程。因此,miRNA的水平與肝癌的發生和進展密切相關,可作為診斷肝癌的候選標記物。
已有研究發現一些miRNA具有較好的診斷效能。例如,有研究發現miR-122的水平在肝癌中顯著上調,在健康人群中應用miR-122診斷肝癌的敏感性為90.0%,特異性為94.0%,AUC為0.954,而miR-122鑒別良惡性肝臟腫瘤的敏感性為64%,特異性為62%,AUC為0.667[16]。此外,miR-148a被認為是一種肝癌特異性miRNA,與肝硬化患者相比,肝癌患者血漿miR-148a的水平顯著降低,應用血漿miR-148水平從肝硬化患者中診斷肝癌的敏感性為89.6%,特異性為89.0%,AUC為0.919,而在AFP水平較低的肝癌患者中,miR-148診斷肝癌的敏感性可達90.6%,特異性可達92.6%,AUC為0.949[17]。一項薈萃分析發現,miR-125b診斷HBV相關肝癌的敏感性達95%,特異性達0.79%,AUC為0.95[18]。對于此類診斷敏感性較高的miRNA,可用于篩查早期肝癌,特別是在AFP水平較低的患者中更具意義。與單個miRNA相比,多種miRNA的組合可顯著提高其診斷效能。在一項納入934例受試者的研究中,miR-122、miR-192、miR-21、miR-223、miR-26a、miR-27a及miR-801的組合對于HBV相關肝癌的診斷具有較高的診斷價值,其從CHB患者和肝硬化患者中診斷肝癌的AUC分別為0.842和0.884,而對于早期肝癌(BCLC0期和A期),該組合的診斷AUC達0.884[19]。
近年來,外泌體miRNA在肝癌中的功能日益受到關注。一些特定的miRNA可在外泌體中富集,參與細胞間的信號傳遞。而外泌體的磷脂膜結構可以使包裹的miRNA在血液中更加穩定,具有較高的無創診斷價值[20]。有研究發現,與CHB及肝硬化患者相比,肝癌患者血清外泌體miRNA水平發生顯著變化,其中,miR-18a、miR-221、miR-222及miR-224水平顯著上調,而miR-101、miR-106b、miR-122及miR-195水平顯著下調[20]。另一項研究發現,與肝硬化相比在肝癌中,血清外泌體miR-122、miR-148a及miR-1246水平顯著上調,其診斷AUC分別為0.816、0.891、0.785[21]。外泌體miRNA在肝癌早期診斷中的應用仍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和驗證。
4 LncRNA
長鏈非編碼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是一類長度超過200個核苷酸的非編碼RNA,約占RNA分子的68%[22]。lncRNA可與轉錄因子相互作用影響其與靶基因的結合,也可參與染色質重排發揮增強子作用或作為分子海綿與miRNA或蛋白結合,在轉錄、轉錄后及翻譯等多個水平發揮其調控作用[23]。在肝癌中,與miRNA類似,lncRNA也可參與細胞增殖分化及凋亡、上皮間充質轉化、侵襲和轉移等多個腫瘤生物學過程[24]。
研究表明,多個lncRNA在肝癌表達異常或功能失調,如HOTAIR、MALAT-1、HOTTIP、H19、UCA1、HULC、GAS5、MEG3等[25]。其在肝癌中表達水平的差異為其作為候選診斷標記物提供了可能。例如,HEIH作為一種原癌lncRNA,不僅在肝癌肝組織中高表達,其在HCV相關肝癌患者血清中表達也異常升高[26]。Xu等研究了兩種血清外泌體lncRNAENSG00000258332.1和LINC00635用于肝癌診斷的準確性。研究發現,與CHB患者及肝硬化患者相比,這兩種血清外泌體lncRNA在肝癌患者血清中均呈高表達。其中,ENSG00000258332.1從CHB患者中診斷肝癌的敏感性為71.6%,特異性為83.4%,AUC為0.719;而LINC00635用于診斷的敏感性為76.2%,特異性為77.7%,AUC為0.750,均優于AFP(敏感性為54.7%,特異性為75.3%,AUC為0.666),而三者聯合用于診斷AUC可達0.894(敏感性為83.6%,特異性為87.7%)[27]。這些發現表明利用lncRNA作為無創診斷標記物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lncRNA應用于肝癌早期診斷有待更多大樣本臨床研究進行驗證。
5 蛋白標記物
AFP仍然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肝癌診斷標記物,以20ng/mL為診斷閾值用于早期肝癌診斷,只有大約1/3患者可以得到診斷。其低敏感性限制了其作為早期肝癌篩查標記物的應用價值。而以較低診斷閾值用于早期肝癌診斷,AFP可能獲得更好的敏感性,因此確定AFP的最優診斷閾值仍有待于更多研究證據。為提高AFP的診斷準確性,AFP可與其他診斷指標聯合應用。除AFP以外,其他用于肝癌診斷的蛋白標記物也得到了廣泛研究。
AFP具有3種糖化類型,與扁豆凝集素的結合能力不同,分別為AFP-L1、AFP-L2和AFP-L3。其中,AFP-L3僅來源于腫瘤細胞,因此被認為對于肝癌具有更好的特異性。AFP-L3的水平與AFP水平高度相關,但由于其更高的特異性,可用于AFP的替代檢測。在一項縱向研究中,研究者發現AFP-L3對于早期肝癌的診斷效能并不優于AFP(AUC0.77vs0.73),而AFP和AFP-L3聯合檢測可獲得更好的診斷效能(AUC0.83),以AFP 5ng/mL及AFP-L34%為診斷截點,二者聯合檢測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可分別達到79%和97%[28]。
維生素K缺乏或拮抗劑Ⅱ誘導蛋白(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 orantagonist-Ⅱ,PIVKA-Ⅱ)是因維生素K缺乏誘導產生的一種異常凝血酶原。在肝細胞惡性轉化過程中,維生素K依賴羧化酶系統功能受損,誘導了PIVKA-Ⅱ的產生[29]。在肝癌發生過程中,其水平顯著升高,因此可作為早期肝癌的篩查標記物。在一項來自國內的隊列研究中,Wu等發現PIVKA-Ⅱ診斷肝癌的效能優于AFP(敏感性76.92%vs64.34%,特異性86.26%vs 73.28%),血清PIVKA-Ⅱ的水平與腫瘤大小、分化程度及BCLC分期等均顯著相關,而對于早期肝癌的診斷,聯合PIVKA-Ⅱ(AUC0.812)和AFP(AUC0.797)可得到更高的診斷效能(AUC0.849)[30]。
高爾基蛋白73(Golgi protein-73,GP73)是一種2型高爾基體特異性膜蛋白,廣泛表達于各種組織上皮細胞中,而肝細胞中表達量較少。然而在肝癌患者中,血清GP73水平顯著升高[31]。Jing等的研究發現GP73診斷肝癌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92.31%和83.87%,陽性預測值為87.8%,陰性預測值為89.7%,具有較高的診斷價值[32]。
鱗狀細胞癌抗原(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SCCA)是絲氨酸蛋白酶抑制劑家族的成員,廣泛表達于鱗狀上皮中。其在上皮來源的腫瘤中呈高表達,可使腫瘤細胞逃避凋亡[33]。由于SCCA的表達是腫瘤細胞去分化的結果,因此被認為是肝癌的潛在標記物。Yu等的一項薈萃分析發現,SCCA診斷肝癌的敏感性為0.61,特異性為0.80,AUC為0.76[34]。此外,在腫瘤發生的早期,由于SCCA的表達升高,其可與IgM結合形成免疫復合物(SCCA-IgM)。Liu等的一項薈萃分析發現,對于肝癌的診斷,SCCA-IgM的準確性與SCCA相當(0.77vs0.80),但其與AFP聯合應用可獲得更高的診斷準確性(AUC0.90)[35]。
6 小結與展望
肝癌起病隱匿,大多數患者在確診時已錯過手術或治療最佳時機[36]。因此,肝癌的篩查和早期診斷對于治療和預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由于肝癌高度的異質性,傳統的診斷手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隨著分子生物學的不斷發展,我們得以從分子層面窺見肝癌更微觀的生物學特征。高通量測序、RT-PCR、芯片技術等分子診斷技術的發展使我們能夠檢測遺傳及表觀遺傳學上DNA、RNA及蛋白水平的改變,并開發新的無創診斷標記物。本文中,我們主要從肝癌相關基因、DNA甲基化標記物、miRNA、lncRNA、以及蛋白標記物等方面展現了當前肝癌分子診斷標記物的研究進展。上述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不同類型診斷標記物分別具有不同的臨床應用特點,可分別用于肝癌的早期診斷、治療方案選擇、預后判斷、復發預測等方面。同時,不同類型肝癌診斷標記物之間的聯合應用,可增加它們的診斷效能。然而,盡管與傳統診斷標記物相比,許多新型分子診斷標記物展現出更好的診斷效能,具有較好的轉化價值和應用前景,但仍需要大量高質量的臨床研究進行驗證,為更好的臨床應用提供堅實的證據和更優的聯合策略。因而,發掘更多的特異性分子診斷標記物并加以驗證,充分利用這些標記物的優勢,取長補短,為肝癌的臨床診斷、療效監測、預后判斷等服務,仍是當前一段時間臨床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