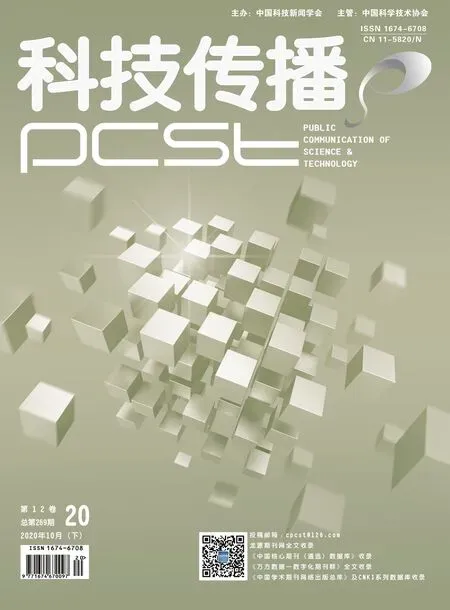環境法視域下我國遺傳資源保護的科普現狀分析
遺傳資源保護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中的重要一環。豐富的遺傳資源是醫藥、農業等領域持續發展創新的活力源泉和基礎保障。我國遺傳資源法律保護制度建設起步較晚,但是發展迅速。近年來我國遺傳資源保護正在受到更加廣泛的關注,同時學界對遺傳資源保護開展的研究探討也正在走向深入。制度層面的發展進步以及熱烈的學術爭鳴有力地扭轉了我國曾經遭受“生物剽竊”侵害的不利局面,然而我國遺傳資源保護仍然存在覆蓋面狹窄、保護客體不完整等相關問題。這些問題表明目前我國相關的遺傳資源保護措施還沒有在遺傳資源培育和獲取的起始點發揮足夠的作用,在遺傳資源保護思路上存在偏差,對遺傳資源保護的科普宣傳存在缺位現象。因此在對遺傳資源保護相關科普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思考如何搭建開端與終端有效連接的遺傳資源保護模式,將公眾參與保護制度化,是現階段我們應當思考的重要問題。
1 我國遺傳資源及其保護現狀概述
遺傳資源是具有實用或者潛在實用價值的遺傳材料及遺傳信息。其中遺傳信息具有可復制性、無體性特點,而含有遺傳功能單位是遺傳材料的主要標志[1]。我國將遺傳資源認定為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含有生物遺傳功能的材料、衍生物及其產生的信息資料。
遺傳資源的特殊性體現在自身特性和環境影響力兩個方面。一方面,遺傳資源本身包含了特定物種所攜帶的物種特性和自身性狀,這些珍貴信息來源于物種在漫長演化過程中的積累。從生態中心主義的視角出發,對遺傳資源進行保護本身就是對生態環境的基本尊重[2]。另一方面,遺傳資源是開啟其他生物資源寶庫的鑰匙。借助科學研究和技術手段,我們有能力對遺傳資源進行研究,進而了解和保護其他生物資源。隨著工業化的不斷推進,生態環境變化的發生速度和表現形式都變得更加復雜和難以預測,這種突變為我們針對其他生物資源開展保護工作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對于那些原生境、自然棲息地遭到嚴重破壞的生物來說,保留和保護相關遺傳資源將為種群的生存提供新的機會,因此對于遺傳資源的保護和研究就顯得更為必要。而目前我國立法的保護客體覆蓋面比較狹窄,集中保護野生的、瀕危的物種,達到的保護效果較為有限,資源流失現象并未得到明顯遏制。
同時應當認識到,物種之間的交流是遺傳資源不斷變化的基礎,而最能體現遺傳資源活力的部分并非來自實驗室和儲備庫,而是誕生于田野,是那些廣泛存在于其自身原生境中的物種。遺傳資源的載體,如農業植物、藥草等都是在農民、社區居民長期的培育和種植過程中誕生的。這些遺產資源的組成部分都浸透著世代培育者的汗水與智慧。然而目前我國遺傳資源保護科普工作仍然沒有有效作用于這些與遺傳資源接觸最為密切的群體,這種現象也造成了我國在收集、研究、利用等多方面的損失。
2 我國遺傳資源保護的科普現狀
隨著社會進步,國家政府對于科普教育工作愈發重視[3]。我國于2002年正式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標志著我國的科普工作正式納入法制化軌道。此后我國先后出臺多部相關法律法規,不斷完善科普具體制度、細化科普程序,牽引我國科普工作走向深入。目前在遺傳資源保護科普方面,我國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諸如孟山都大豆等嚴重危害我國遺傳資源安全的生物剽竊事件不會再次發生。但是目前我國遺傳資源保護科普工作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目前我國遺傳資源保護科普理念有待更新,科普隊伍有待進一步壯大,科普激勵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
2.1 我國遺傳資源保護的制度梳理
目前我國遺傳資源保護領域相關法律針對性較差、缺乏系統性和連貫性,專門保護法律的缺失導致法律保護客體覆蓋面較為狹窄。到目前為止,我國已加入《名古屋議定書》《波恩準則》等,并出臺了相關的法律法規承接其要求,但從立法保護的客體和調整的法律關系上看,現行立法所提供的保護是不完整、不直接的。現行的法律體系針對農民權的規定不夠具體和明確,同時缺乏對藥用植物遺傳資源所有權救濟的制度性安排,不利于遺傳資源保護科普工作的開展。我國農民權至少應當包括保護農民在育種方面的傳統知識和實踐做法、事先知情同意權利、公平的惠益分享權利[4]。而將農民權用制度的手段加以明確和固定,是進一步向遺傳資源的貢獻者和保護者進行科普和教育的基本前提。
同時,我國目前的遺傳資源保護科普工作理念有待更新,這種理念上的漏洞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源自我國遺傳資源保護觀念的偏差。從立法上來看,我國目前缺乏具有針對性的、系統的遺傳資源管理單獨立法,長期以來采用針對遺傳資源物質性載體的法律規范遺傳資源,這容易導致實踐中對于遺傳資源信息化屬性的忽視,不能起到良好的保護效果。而目前我們對于遺傳資源的無體性、信息屬性認識愈發清晰,立法思路開始發生積極轉變,與之配套,我國遺傳資源保護科普工作也應當秉承正確的科普思路,著重分析遺傳資源可復制性等的信息化屬性,引起種植者、培育者的重視。正因為遺傳資源具有信息化屬性,對遺傳資源進行生物剽竊往往更加隱蔽,更難防范。因此在開展科普工作時應當注重宣傳,使得種植者、培育者充分了解到每一物種所承載的生態價值,在遺傳資源收集、獲取的最基層形成嚴密的保護防線。
2.2 我國遺傳資源保護科普實踐現狀
目前我國遺傳資源保護科普工作在廣度和深度兩個維度存在問題。首先,遺傳資源載體的一部分同樣是廣大藥農、畜牧業從業者等的重要生活來源。目前這些群體對于遺傳資源保護了解程度較低,同時群體的行為也在受到相關交易市場的影響。在市場的驅動下,人類不科學的采集方式和不考慮植物繁衍能力的過量攫取導致野生物種個體的大量消亡,而個體的大量滅失則直接引發其遺傳資源的毀滅。如目前獲取許多野生植物的藥用價值往往是以毀滅整個植株為代價的,諸如杜仲、降香黃檀的藥用價值存在于莖皮,而紫斑牡丹、黃牡丹的藥用價值存在于根,對這些野生植物的大量采集加劇了該物種的萎縮。其次,對市場的高度依賴導致那些人工培育載體所承載的遺傳資源同樣面臨保護困境。由于市場自身的波動性和變化性,在市場形勢向好的情況下,培育者出于迎合市場的考慮往往選擇廣泛培育利潤空間較大的單一物種。在重視資源開發利用的法律體系下,那些沒有展現出經濟價值的物種很難得到應有的研究和保護。上述的種植模式不但限制了其他物種生長的空間,而且加劇了物種單一化趨勢,降低了生態系統抵御風險的能力,危害物種多樣性。而單一化的、缺乏基因交流的培育模式則降低了物種的抗風險性,對生物多樣性保護造成了不利影響[5]。
目前遺傳資源保護的科普不能針對上述具體矛盾進行化解,故無法達到良好的預期效果。只有通過科普工作,向基層培育者充分宣傳其在遺傳資源保護負有的義務,才能對抗畜牧業、種植業市場發生的盲目飼養、盲目種植行為。只有通過科普將基層培育者相關權利充分講解和宣傳,才能促進基層培育者積極參與到遺傳資源保護的進程中來。而我國遺傳資源保護科普的主要群體在培育、收集方面能夠起到較大作用,因此通過高度完備性和創新性的科普手段對抗資源流失風險是具有較高可行性的。
3 我國遺傳資源保護的科普對策分析
在環境法視角下,通過制度進一步明確公民在保護我國遺傳資源方面的享有的權利和應當履行的義務。通過科普教育工作,一方面激發公眾參與的熱情,提高公眾參與的質量,另一方面拓寬公眾參與的渠道,鞏固科普教育所獲成果。以針對我國遺傳資源保護開展的科普教育為手段,既賦予公眾參與保護我國遺傳資源保護的有力手段,又明確他們作為遺傳資源傳承人無法推卸的責任,從國家層面的技術保障手段完善和公民層面的相關保護知識輸入兩方面入手,推動我國遺傳資源保護科普工作進一步走向深入[6]。
3.1 完善我國遺傳資源保護公眾參與制度
通過法律手段規范公眾參與制度是塑造法律觀念、建構法律制度、保障公眾參與權利的法定化與現實化的必然要求[7]。高質量的公眾參與是開展我國遺傳資源保護工作的關鍵。通過科普工作提高公民素質是提升公眾參與質量的關鍵。公民素質主要包含有權利意識、責任意識、公共精神等[8]。我國遺傳資源豐富,許多遺傳信息載體本身來源于社區居民的生活范圍內,與當地人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9]。對遺傳資源進行保護既是保護我國自然資源的需要,又切實關系到相關生產者的自身利益,因此在我國遺傳資源保護領域的科普工作主要障礙并不存在于動力機制層面,現階段將公眾參與制度化法治化是我們需要完成的主要目標。
具體來說,目前應當健全我國遺傳資源保護的實體規范,明確程序要素,提升公眾法律意識,同時落實農民權保護制度,形成培育者與利用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模式[10]。目前我國公眾參與的自覺性、主動性以及理性化程度較低,參與意識較為薄弱[11]。因此我們應該以科普教育為主要手段,重點培養公民的主體意識,強化公民的法治思維,提高公民在遺傳資源保護過程中的參與度。應當借助信息交流平臺,為公民創造便利參與、反饋及時、得到充分安全保障的社會管理參與平臺。
3.2 建立我國遺傳資源數據庫
遺傳資源保護工作的落實需要借助高效的技術工具。公眾參與遺傳資源保護工作的前提是建立高效的管理體制,提供開放的信息交流平臺。在硬件建設方面,需要搭建便利溝通的信息交流平臺,使得保護工作落到實處。平臺應當具備安全性和便利性兩個主要特點。平臺安全性構建方面,應當將數據庫的信息出入庫過程置于國家監管之下。一方面保障了這種交流行為的合法性,用制度手段杜絕了生物剽竊事件的產生;另一方面也能夠保障入庫信息的準確性和有序性,最大限度節約制度運行成本。從平臺便利性角度來看,我國遺傳資源保護數據庫以現代科技手段對不同物種的遺傳資源進行了保存,并且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遺傳資源數據庫的建立相當于為物種提供了云上互動的機會,以技術手段彌補了單純在原生境保存生物樣本的缺陷。我國遺傳資源數據庫應當成為一個為遺傳資源收集利用和互動提供便利的虛擬場所,通過信息互動實現瀕危物種復壯,防止我國自然資源流失。
同時,依法建立入庫登記制度和出庫申請制度。有效發揮數據庫的技術援助作用,積極將數據庫向進行科學研究、開發利用的科研機構、組織和個人開放。在數據庫運行維護過程中,應當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確保符合條件的申請人能夠及時獲得所申請的數據庫信息,以達到激勵資源保護和促進資源開發的目的。
4 結語
我國遺傳資源保護工作不僅需要社會各界廣泛的參與,而且需要在時間維度上持續不斷的努力。我國遺傳資源儲量豐富,相關培育人員在遺傳資源保護領域能夠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在目前工作的基礎上彌補漏洞,積極開展遺傳資源保護科普工作,能夠對我國遺傳資源保護工作起到巨大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