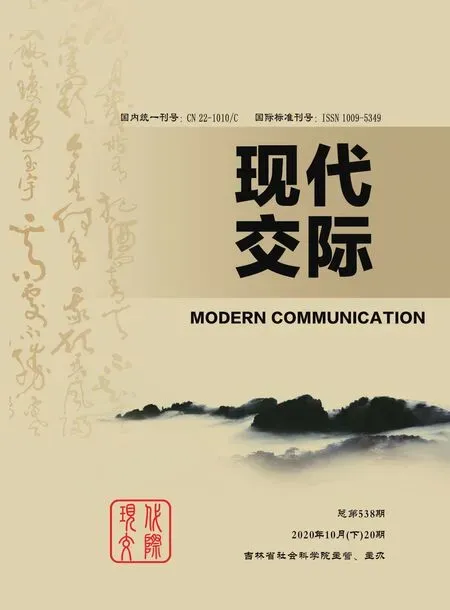現實悲苦與荒誕命運
——張藝謀電影和余華小說的兩種“活著”
王 芳
(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文學院 廣東 珠海 519000)
死亡主題是先鋒作家創作時關注的重點。生存與死亡之間的聯系與沖突,貫穿人類生命的始終,是人類在探索生命價值時繞不開的話題。死亡是生命的盡頭,讓人感到畏懼與恐慌,死亡亦是人類生命存在的證明。死亡直逼生命在現世的生存價值,迫使人類尋求生命的終極真實,故而先鋒小說在此基礎上進行價值探索,以死亡為媒介希求尋得人性的發現和生命的價值。
長篇小說《活著》是先鋒作家余華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初探死亡主題的嘗試之作。在小說中,有明顯的中西文化碰撞與對接的烙印與劃痕。作家所接受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想,與扎根在他血肉中的中華傳統民族思想和文化價值發生了不自覺的碰撞,顯示出中國先鋒作家對死亡的民族化價值探索。在小說中,余華旨在對死亡作形而上層面的詮釋與反思,體現了他對現代生命哲學的理解與書寫。而電影《活著》則與小說所表現的內容完全相反,電影則聚焦更貼近生活的現實批判與歷史反思。
張藝謀是極具傳奇色彩與爭議的藝術家,他以攝影師身份出道,憑借1984年執鏡陳凱歌導演的《黃土地》時所展現的獨特鏡頭藝術感,斬獲當年金雞獎最佳攝影獎。攝影師的生涯讓張藝謀積淀了對鏡頭獨具特色的掌控能力,為張藝謀的導演生涯奠定良好基礎。張藝謀的電影生涯并未局限于攝影師這一固定身份之上,他的導演身份更受世人矚目。張藝謀于1987年創作出《紅高粱》這部有別于以往所有中國電影的、具有鮮明個人藝術風格的作品,問世之初就在整個中國影壇,甚至世界影壇引起了轟動。張藝謀的電影作品帶有鮮明的民族色彩和個人特色,具有極其鮮明的“張藝謀式”的獨特敘事藝術特點。張藝謀的作品在國內和國際斬獲各類大獎無數,好評無數,與之相對的,也不乏批判的聲音。電影《活著》便是張藝謀轟動一時且飽受爭議的作品。
電影《活著》由張藝謀執導,由蘆葦和余華共同擔任編劇,于1994年由年代國際有限公司出品。縱觀張藝謀的電影作品,《活著》無疑是最具張藝謀特色的代表作之一,亦是中國當代電影史上的一座豐碑與高峰。解讀電影《活著》不僅能使我們更加了解張藝謀的藝術創作模式,更能通過研究張藝謀電影《活著》與余華原著小說之間的聯系、分裂、重構,從而發現小說作品電影化的一種獨特表現模式,并得以體會文本中內在深厚的思想價值。
一、故事情節的差別
1.小說《活著》:關于人類荒誕命運與無可避免的死亡
余華小說《活著》的格調是相當荒誕和冷峻的。
余華在書中探討和表現的,其實是關于人類生命和命運的終極關懷。余華書寫的是人類無法掌控的一種獨屬于命運的神秘力量,正如福貴一家人的存在與死亡都是形而上的“荒誕”二字的呈現。小說名字是“活著”,書中卻從始至終充斥著主人公周圍生命的消亡,即與“活著”完全相對的“死著”。在余華的小說中,福貴一家人的消亡更像是一個符號,是生命的一個自然的、無可逆轉的流動過程,而現實背景只是為語境服務的遠景。
在余華的小說中,依照福貴的回憶,他年輕沉迷賭博,以致散盡家財,自己家的宅子都被龍二奪走,一家人只好搬至破舊的茅草屋。自此之后,福貴一家人仿佛陷入了現實殘酷和荒誕命運的漩渦。父親身亡,家珍被丈人接走,家庭破碎,福貴還需要想盡辦法賺錢來維持生計、供養老母。生活艱難,但福貴眼前并非一點希望都沒有。家珍回歸家中,讓福貴感受到了一點生活的希望和溫暖,他盡其所能努力地干活。本以為生活雖艱難卻能平靜度日,但是變故又生,福貴突然被抓了壯丁,一走又是漫長的幾年光陰。軍隊中槍彈無眼,福貴能活著回來已是奇跡。福貴回到家,卻發現老母病亡、女兒高燒之后成了啞巴。故事到這里,福貴及其一家人的命運呈現出有一定規律的起伏波動,那就是:生活中一旦望見了一點明亮,接踵而來的便是灰暗與慘淡。
福貴因賭博散盡家財,宅子被抵給龍二,卻意外在土改時躲過被槍斃的命運,還分到了自己曾經種過的五畝地。家財豐厚時,福貴整日賭博,家珍整日以淚洗面,在福貴固執不聽勸告時,家珍回了娘家,在福貴住進茅屋后帶著兒子又回歸了這個家,和福貴一起贍養老母……
凡此種種,我們都能看到這仿佛就是永遠無法被定義和掌控的宿命,抑或被稱作“命運”。“幸運”與“不幸”雖然在當下看起來明確,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任誰也不能準確預測未來將會是什么模樣。
之后,福貴一家人的命運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兒子因抽血過多夭折了,血液供給的對象是縣長夫人,而這個縣長正是福貴當年在軍隊的朋友春生;女兒鳳霞死于難產大出血;女婿的死更加令人瞠目——被夾在水泥板中喪生;外孫苦根死于吃了過量的煮毛豆。發生在福貴身邊的這些死亡事件,除了母親、妻子是病死之外,其他幾乎皆是意料之外的災厄。苦難伴隨著灰暗的基調和沉痛的宿命而來,讓人只能緘默。
小說的結尾,幾乎所有的人都死了,只有福貴活著。
沉郁與荒誕,是小說《活著》帶給人的最直觀的體會與感受,亦是整部小說的風格與基調。所有人都死了,主人公福貴還活著。福貴還“活著”,應和了小說《活著》的書名,卻也傳達出一種“為了活著而活著”的悲哀。《活著》中關于生存與死亡的主題意蘊,與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顯示出一定的重合,福貴的一生實際已具備了一定的哲學啟示意義。海德格爾曾說:“作為向其死亡的存在者,此在實際上死著,并且只要他沒有到達亡故之際就始終死著。”在余華冷峻的文字背后,是對人類死亡的無邊際的復雜想象,是對荒誕、不可控的命運的刻畫與書寫。
2.電影《活著》:關于個體在殘酷現實中的茍且偷生
在保留小說主要人物和人物關系的基礎上,張藝謀對《活著》做了很多方面的改編,而情節的改編也給整部電影造成了與小說完全不同的風格基調。因此,較之小說,電影《活著》展示出的審美面貌和思想內涵也都產生了變化。
以1949年這一時間點為界限,電影《活著》和小說的大致情節基本類似,我們主要關注電影中1949年之后故事發展與小說情節的區別。
第一個關于 “死亡”的情節:有慶的死。
“大躍進”開始后,福貴強逼著整整熬了一夜的有慶上學,有慶卻被塌了的墻砸死,而撞塌墻的區長正是當年與福貴共患難過的春生。在小說中有慶的死因是獻血過多而死,本就荒謬,加之余華文字冷峻而沉靄的文字風格,讀者在閱讀時都會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汗毛倒豎的荒誕之感。被倒塌的墻砸死和獻血過多而死,雖然都是意外,死因也皆與春生有關,卻讓我們明顯地感覺到,對比“獻血過多而亡”這種死因,“被墻砸死”這種死法實際上讓觀眾少了一點荒謬的感覺。
第二個關于“死亡”的情節:福貴女兒鳳霞的死。
在電影和小說中,鳳霞都是因為難產大出血而死,唯一不同之處就是電影中鳳霞的難產是因為沒有人能對鳳霞大出血的情況做出診治。在這里,張藝謀為鳳霞的慘死增添了更多時代色彩,這是電影想重點突出的,那就是渺小個體在時代的殘酷現實中的無能為力。電影突出的時代背景,并非小說的主題。
第三個關于“死亡”的情節:故事的結尾。
在小說中,故事的結尾只有福貴一個人活下來了。也許福貴是有最多理由、最多可能被死神帶走的人,可是其他人都死了,卻只有他一個人活下來了。命運無常,這種無意義的“活著”,某種意義上同樣也是死亡的一種形式。
電影的結尾卻與小說完全不同。
電影的結尾,是多年之后這樣一個場景:暖烘烘的陽光灑在福貴一家人身上,福貴和女婿二喜、外孫饅頭圍在臥病的家珍的床邊,幾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氣氛很輕松。多么溫暖的一幕,守得云開見月明,福貴一家人經歷如此多的苦難,卻仍有機會圍坐在一起閑話家常。電影的畫面也變得略微明亮了一些,不再是完全的沉郁陰暗的基調。在電影《活著》之中,在張藝謀的鏡頭中,我們能看到一點光亮。福貴一家人的命運,不像小說那樣以悲劇結尾,仿佛望見照進烏云的陽光,看到了一點希望。
二、小說和電影之間的敘事角度差別
1.小說《活著》:第一人稱下的冷峻、平靜敘述
《活著》這部小說實際有兩個不同的敘述者,一個是作品開頭的民歌收集者,也就是“我”。“我”漫步于鄉野田間,本為收集民歌而來,卻遇到了一位老人,也就是故事主人公福貴。老人福貴飽經滄桑,向“我”講述他從前的故事。于是小說主要情節就此展開,作品的敘述者在“我”和富貴之間不斷切換。《活著》講的主要是福貴的故事,也由福貴來敘述。“我”作為來到鄉野漫游的年輕人,更多時候只是以聆聽者的角色獨立于福貴的故事之外。
在老人平靜的回憶和講述中,讀者望見了從前屬于福貴一家人的荒誕而殘酷的過往,樁樁件件都令人唏噓不已。老人的眼神溫和淡漠,敘述從容緩慢。有些回憶荒誕,有些回憶悲痛至極,但是老人的情緒都十分平靜,仿佛這些事情并非是發生在他身上的一樣。在老人福貴的講述過程中,“我”作為敘事者之一也會伴隨老人回憶而進行一些思考,在“我”思考的同時,讀者也被剝離開來,從而在閱讀時得以理性思考。這就是一種“間離”效果,即讓讀者和文本產生一定的間距,引導讀者獨立冷靜地思考。讀者就像書中的“我”一樣,接觸這些記憶時只覺震撼和悲痛,卻又能剝離出自我進行思考。
余華的文字帶給人一種疏遠又冷靜的感覺,又處處是對生命的哲思,加之小說第一人稱有限敘事的視角轉換,《活著》這部小說整體上都使人觸動卻又不沉溺在故事中,從而得以對余華真正想傳達的——關于生命、關于命運的題旨進行獨立思考。
2.電影《活著》:第三人稱下的動情、細致敘述
張藝謀是攝影師出身,他對鏡頭的掌控能力是非常強的,且具有相當明顯的個人特色;在《活著》這部電影中,更是將他獨特的鏡頭藝術感表達得淋漓盡致。電影《活著》的整體色調雖并非明朗清亮,但確能讓我們感受到一絲微光,這不僅緣于張藝謀對情節的改編,還來自電影獨特的敘事節奏和敘事角度。
電影以鏡頭記錄故事,鏡頭本身獨立于畫面中的人物而存在,而張藝謀在拍攝電影時,沒有沿用小說中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而消去小說中作為民歌收集者的“我”的這一角色,單純按照時間順序講述了福貴一家人的經歷。抹去了“我”這一敘事視角,觀眾在電影中也就無法感受小說所帶來的“間離”,取而代之的是跟隨鏡頭深入到福貴的故事中,得到更加直接的情感體驗。
在電影中出現了許多生離死別的場景,張藝謀沒有讓這些場景變得單調、千篇一律。無論是人物處于絕望邊緣的肢體語言,還是悲愴激昂的背景音樂,都極大地增強了生死之景的藝術感染力,讓觀眾仿佛身臨其境。觀眾在這些畫面中體驗到了強烈的悲痛,情緒隨之起伏波動,絕望之感深入每一個在鏡頭后的人的心中。正因如此,電影末尾,當福貴一家幾口人聚在一起聊天時,那種平淡卻溫馨的氣氛才會更打動觀眾,讓觀眾油然而生一種慶幸之感,為福貴一家人慶幸,也為故事仍留有一絲希望而慶幸。電影其實還是留給了所有人一點希望與光亮,整體基調也稍顯明亮與溫暖。
三、小說和電影之間的內涵意蘊差別
1.小說《活著》:對人類生存意義的哲思追問
余華這部小說名為《活著》,卻有很大篇幅在講死亡。老人福貴經歷了太多身邊人的離去,最后只剩下一頭老牛和他為伴。他回憶從前,人生階段遞進幾乎都伴隨著親人的死亡。苦難和悲哀命運令人深覺荒誕,卻并未摧毀老人的精神,老人變得平靜無爭,依然堅持活著。失去了所有生存理由,人類卻仍然“活著”,那么這種“活著”究竟是為了什么,有什么意義?這一追問實際具有海德格爾式存在主義哲學的意味。在類似于這樣的追問中,余華在思考生命存在的意義,同時也希望向我們傳遞這種對生命存在的思考和感悟。福貴一家人的生命進程和悲劇命運,承載著余華對人類生存意義的追問。更進一步講,福貴一家人的命運正是整個人類荒誕命運的象征型的縮影和符號,即使不同個體經受的苦難和荒誕命運不盡相同,但歸根結底都是生存與死亡之間的拉扯和悲劇。
《活著》這部小說擁有著敘述上縱深與宏大的架構,余華的目光始終聚焦于人類生命的終極真實,希望通過主人公荒誕一生向我們展現生命悲哀的某種常態。小說不復余華之前作品的憤怒與殘酷,因為主人公在回憶這些事情時目光平和、心情平靜,仿佛已經超越了死亡帶給他的恐懼,從而進入某種達觀超然的心境。
對于余華將福貴引向如此超然的境地的情節設置,學界歷來爭論不休。有學者給予正面積極的評價,認為這是余華對生命悲劇的正向消解,是一種超越死亡的精神力量;也有學者認為余華在此選擇消解苦難,逃避苦難,而這成為他的局限。
我們深入小說的文本和主題思想,會發現文本中存在著西方存在主義哲學觀與中華傳統哲學中的價值不相容,使作品對死亡和存在主題的渲染顯示出力量不足的問題。我們對此可持一定的寬容態度,因為小說《活著》已經展示出當代作家從以政治為主題的層面轉向了對于人性、人生等價值層面的思考;這一批先鋒作家的創作有著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值得我們更多地關注。
2.電影《活著》:特定時空下的個體生存悲劇和社會悲劇
電影《活著》展現了福貴一家人的生死悲歡,并且著重渲染了故事背后的政治元素。電影要講的其實很簡單,就是身處特定歷史時代的一家人的悲慘經歷,以這家人的苦難作為中國歷史文化的切入點并進行透視。在張藝謀的電影中,強化了對特定歷史的回顧和反思,弱化了小說中關于人類生存的哲思。
電影《活著》雖然保留了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和部分情節,但其內涵意蘊已與小說文本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方向。如果說小說是對整個人類生命的哲思和追問,那么電影《活著》就是中國特定時空下社會悲劇的陳述。張藝謀對原著進行的電影化改編,實際上是將小說進行拆解、重構之后的二次創作,故而電影整體的藝術風格和主題內涵都與小說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在電影中,無論是主要人物死因、故事發生的空間位置,都體現了張藝謀所想要表達的價值思想,那就是:回顧歷史和反思歷史,關照那些在特定時空中小人物生活的悲劇。在電影中的人物命運與社會現實深深掛鉤:有慶被圍墻砸死,根本原因是他和大人晝夜不停地煉鋼導致的極度疲倦,讓他疲憊之下只能在圍墻邊休息,導致了悲劇的發生。張藝謀的改編將故事引向了更為貼近生活和歷史的方向,他所要突出表達的是對特定歷史時期的回顧和反思。這是特定歷史時代的悲劇,是民族文化和歷史中的悲劇,電影的這一改編也體現出了張藝謀直面歷史并勇于反思歷史的氣魄。
四、結語
小說作品在電影化的過程中一定會有所刪改,在不同的歷史時代背景下,影視改編的特點也不盡相同。20世紀90年代的電影改編,更多的是對時代與歷史的反思,包括《活著》在內的張藝謀的多數作品。
小說《活著》和電影《活著》雖然擁有相似人物設置和部分相似的情節,但實際上,無論是從整體風格基調、敘事手法還是題旨意蘊層面來看,這已是兩個內涵相去甚遠的文本。小說基調沉郁,電影基調微亮;小說敘事由第一人稱敘述,產生一定的“間離”效果,而電影以第三人稱講述,較易使人產生一定的“移情”效果;小說意在闡發對整個人類命運和生命意義的追問,而電影著重刻畫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社會悲劇和個人悲劇命運。
余華小說和張藝謀電影向世人呈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活著》,雖然都是“活著”,向世人傳遞了兩種不同的生命體驗和精神文化。二者對比,小說中的“活著”實際是“死著”,主人公受制于死亡和命運的掌控而無法反抗,看似平靜淡遠的態度背后更多的是人類對不可抗力命運的無奈和妥協。余華所追求的是“真實”——生命的真實、死亡的真實,這已實現了從現世關照到形而上層面的終極關懷的思想境界的提升。張藝謀電影扎根于歷史現實,敘事重點在于如何展現特定時空之下小人物的生存悲劇,電影的末尾,張藝謀也并未完全打碎主人公“活”的希望,沉郁之中仍有微亮的光芒,我們仍然看得到主人公真實“活著”的生存狀態。
無論是閱讀小說還是觀看電影《活著》,讀者和觀眾都會被深深震撼與感動,這是源于“活著”這兩個字本身所具有的厚重的分量。
正如余華在《<活著>韓文版序》中所說:“作為一個詞語,‘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里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叫喊,也不是來自進攻,而是忍受,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人類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終有一天會面臨死亡,那么“生存”與“死亡”就是人必須直面的真實。無論是電影還是小說,最根本的價值都在于闡發對于個體生命存在意義的思考,在當今浮躁喧嘩的社會,啟迪現代人更多地思考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活著”二字也由此具有了直擊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