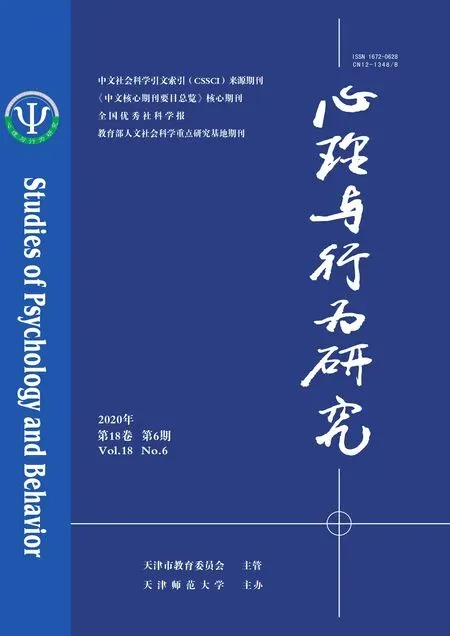關于疫后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個人思考 *
張建新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社會心理服務的定位實際上可理解為兩個方面:一方面與我們平常理解的心理健康服務相關,另一方面則是大家講到的社會治理。現在的問題是,為什么要把社會心理服務與社會治理連接起來、放在一起提呢?我以為大家可能會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在當前的情況下,做好社會治理的問題已經變得迫在眉睫。其中又有兩個方面,一是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思想中形成了一種物質主義的文化,人們公開追求私利,謀求相對于他人的優勢地位。這樣的信念對人們的行為造成了深刻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也造成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破壞。所以一些違法亂紀的行為頻發,甚至一些嚴重的群體事件也時有發生。這是要思考和促進社會治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二是新冠疫情后,會持續不斷地出現后續的負性心理效應。這也是整個社會在疫情過去、回歸正常生活之后,進行社會治理和提供社會心理服務時要考慮的非常重要的一點。但在以上兩點之間,我認為是有一個相對的先后次序的。我們通常說“通則不痛,不通則痛”。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中的“痛”點體現在人們的心理健康方面,而“通”則要我們在社會治理上下功夫。就是說,如果通過社會治理,我們的社會生活和人們的心態順和了,就會出現一通百通,許多心理健康的問題就會得到相應的緩解和解決。所以心理學,特別是社會心理學,要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和社會治理中,抓住“通”這個關鍵點,為政府和民眾提供一些科學可行的治理方向和治理方案。
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國的社會結構的基本框架。以清末民初時期為例,可以看到整個的社會架構分成了兩個層面。從中央到郡縣地方的政府架構,它是社會治理的上層架構。相對應的,社會基層(農村中的宗族村落,或者城鎮中的大家族)是非常重要的底層社會治理結構。上層的政府層面,流動的官員為整個社會傳播了精神文化,而在基層社群層面則生活著相對比較固定的群體。連接上層和下層社會結構的是被稱為士人的知識分子群體(如農村的族長、秀才、舉人等,城市中的私塾老師等),他們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在這樣的過程中,儒家的文化理念就廣為傳播和扎根,因此它在整個社會治理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基層治理中,它是一種準則,可以起到規范人們行為的作用,同時在政府層面,也是對官員的約束教條,因而也是國家和地方社會治理好壞的判斷標準之一。
我們再看當下的社會,基本上還是兩個層面,一是政府的管理層面,二是老百姓工作和生活的社會層面。我認為心理學介入社會治理,最主要的切入點是在社會層面的基層架構之中,如城市社區、學校、工作單位以及農村鄉鎮等。
心理學應以怎樣的理論框架和視角介入社會心理服務和社會治理呢?回顧清末民初以來我國民眾所認同的大眾心理學,它有兩個基本點。第一就是它接受了進化論觀點:人是從生物人、社會人到文化人一步步進化過來的。顯然,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對我國的心理學思想有著非常巨大的影響。從生物人到社會人再到文化人,控制需要、歸屬認同需要、以及對價值觀等精神共識的需求分別成為人們行為的重要推動驅力。第二就是我們心理學家習以為常的觀點,即人的心理結構是由“知”“情”“意”三個基本元素構成的,它們在社會治理的每個層面中都表現出不同的心理功能。
在我國的心理學研究中,有關“知”(認知、思維)方面研究很多,如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科學等。對于“情”的一面現在也投入了很多研究,特別是災難和疫情發生之后,對人們心理健康的服務更多地是從這方面入手進行的,比如,調整認知化解抑郁情緒,適當運動降低焦慮情緒,等等。但相對而言,對于“意”這方面的研究,也就是對需求、動機、目標等的研究,相對要薄弱很多。剛才提到的生物人的控制需要、社會人的歸屬認同需要,以及文化人的追求超越精神的目標都可以寬泛地歸入到“意”的概念范疇之中,因此,“意”的心理意義便與社會治理密切相關聯了。
所以從“意”的心理視角,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社會治理。傳統社會的底層民眾都基本遵從著遠近親疏尊卑這樣的父慈子孝、夫唱婦隨的行為規范,從而滿足了人們對歸屬認同的需求。在整個社會層面,人們都存在有一種普遍的敬畏,人們常常說的“天怒人怨”,“人在做,天在看”等等。這表示在人們內心存在著這樣一種超越的“天”的力量,也滿足了文化人對精神共識的追求。但儒學發展到宋明理學后,也出現了“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念,壓抑了個人的私欲,特別是讓人們對自己小環境進行控制(按自己意愿影響環境)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總體來講,中國傳統社會中個體的控制感相對較低。但因為它是個熟人社會,所以認同感又相對較高。就文化的連接性而言,儒家的理念和人們對“老天有眼”的敬畏形成了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和對社群的塑造,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的社會治理,使中國社會結構千年來都處于一種相對的穩態之中。與中國社會不同,當下的西方社會屬于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結構。對于社區中個體成員和家庭之間的連接,政府基本上不能也不愿去做很多管理的工作,而是將這一職責交給了法律,或者交給了社區教堂和宗教。一個社區就可能建有一所教堂,人們通過周末教堂的禮拜儀式,獲得一種底線思維、一種超越世俗事務的精神共識。所以從大眾心理學的角度看,西方人的個體控制感較高,較少受政府干涉,出現所謂“不自由、毋寧死”的追求。在陌生人之間和個體與社會之間,因為個人主義文化和宗教起著連接作用,整體社會的精神需求能夠得到較好的滿足。
若將中國現在的社會治理與我們傳統社會、或與西方社會進行縱向和橫向的大致比較,就會發現基本的情況大致是這樣:中國社會的整體控制程度非常好,比如新冠疫情發生后,中國社會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勢頭,便是政治制度優勢的充分見證。從另外一方面看,在社區單位中,個人大多傾向于接受安排和調動,個體主觀能動性發揮的空間較少,因而個人控制需求的滿足相對較低。另外,社群關系(特別是城市中的人際關系)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基本上都不屬于熟人社會,而是一個由陌生人組成的社區,所以人們的歸屬認同感也大大降低了。比如,個人的朋友很少來自社區,鄰居彼此之間少有來往,更無情感的交流。從整個社會層面看,儒家學說對人們的約束力相對也在逐漸弱化之中,如社區中核心家庭數量占了多數,幾代同堂的情況在城市幾乎消亡。所以總體的變化趨勢顯示:與傳統社會相比,我們的歸屬認同感下降了,舊有的精神共識影響力亦在下降,而新的精神尚未成為人們真正的共識;社區治理中的個人控制感比較低,連接陌生人的信任感比較低,各家自掃門前雪,社區公共意識薄弱,再加之超越的精神共識影響力下降,所以無論基層社區組織和上層社會管理體系中,都面對著凝聚力不足、個人化導致的心理問題頻發等問題。
從以上分析,可以從“意”的角度發現,我們社會(區)治理中存在的心理學問題,那就是,在社區生活中個人控制需求較少得到滿足,缺乏作為主人的積極能動性,因而心理獲得感(主動作為的收益,而非被動接受的收益)也相應降低。另外社區的歸屬認同感較低,大家心之向往大多指向所生活的社區之外的人群。這就帶來了一種缺乏共識、意見分歧、難有作為的治理難題。當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近9000 多萬黨員深入到社會組織的每一個細胞中,由于他們的存在,我們的整個社會和整個國家就團結一致,運作效率極高。這當然是我們制度的優勢。但社會畢竟是由一個個的獨立個體組成的,從上面提到幾個需求層面看,若每個人的需求得不到較好的滿足,要想達到“人心齊、泰山移”的社會治理整體效果,可能就要付出較高的社會成本;而若每個人的相應需求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大家勁往一處使,則社會管理和治理的成本就可能降到更為合理的水平。從“意”的心理學角度來講,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和社會治理是可以、也應當受到心理學中關于個人、人際和群際層面知識的啟發的。
所以,疫情之后我們應該怎么辦?這個問題對于心理學,對于社會心理學都是一個挑戰。或許可以從上面講到的三個層面入手:讓人們有更多的個人控制感,使人們能夠主動參與社區的決策,發揮主觀能動性,看到美好社區也有自己的一份貢獻,從而獲得“自尊自信”;然后,要讓社區居民互相之間有更多、更有實效的互動,建立起情感連接,增加彼此之間的歸屬和認同,從而達到一個協商共管、“和平理性”的狀態;另一項任務可能就需要長期思考、研究和實施了,即要讓越來越多元化的社會一方面能夠充分表達和寬容個體私有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在大多數人之間達成一種社會共識,奔向大家共同利益所指向的未來目標。所以,心理學家也要在整體社會治理的層面進行思考,如何達成百姓認同和共鳴的精神共識。這一精神共識具體是什么?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但是,中國心理學家要想到這個問題,并且要往前推進。
前面講到“一通百通”,可以設想在社區治理層面,心理學、特別是社會心理學的介入,若能增加個人控制感,就很有可能減少人們的負性情緒,比如焦慮、憤怒等;若能增加社區居民彼此之間的歸屬認同感,就很可能加強人們的自律行為,避免各種自我中心、雙重標準引起的矛盾和沖突;而最后,若能推出一種超越性的價值和精神共識,那么我們的群眾就會更為自覺自愿地求同存異,人們的行為就會找到一個道德和精神的底線。那么,新時期的社會治理,就將會在社會基層平臺上得以實施,取得低成本、高效果的成就。其實,社會心理學在這方面已經開展了不少的探索研究,比如關于黨群關系的建設,多元主體的民主協商,社會信任的公民參與,等等,這些都是很好的研究方向,也為基層的社會治理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考。在疫情過后,社會心理學應該在這一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心理學的“知”“情”“意”三元素對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貢獻,剛才各位專家多有涉及,比如一些宏大理論架構,實際上就是從“知”的角度做出的思考和建議。還有多位專家講到評價社會治理體系能否達到很好效果的標準問題。當然,我們可以從“情”的角度來建立相關的心理健康和社會和諧的標準等。我今天所講,主要是從“意”的角度,也就是從需求滿足、動機引導和目標設定方面,來思考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和社會治理問題。“知”“情”“意”就是心理學,包括社會心理學家,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和貢獻的三個心理學的切入點:正所謂“以‘知’搭臺、從‘意’入手、依‘情’觀效”也。
注:2020 年6 月,由華中師范大學、中國社會心理學會、中國心理學會聯合主辦的“社會治理體系中的心理建設”高端學術論壇在線召開,本文系作者根據論壇中的講話記錄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