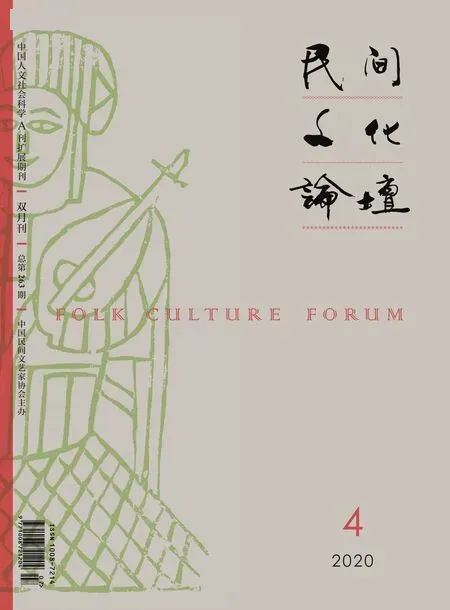修行中的“身體感”:感官民族志的書寫實驗
——以豫東地區S念佛堂的田野考察為中心
孫艷艷
一、挽救一次失敗的田野
S念佛堂建于2000年,最初它只是村里的一座小規模的家庭念佛堂。2002年開始擴建為豫東鄉村地區規模較大的一座由居士創建與主持的佛堂,包括佛堂本部、安養院、診所、超市、菜園、制衣作坊以及環保酵素作坊等。筆者在考慮博士論文選題時,曾于2015年寒假來這里做了一次短暫的預調查,后又于2016年暑假與2017年清明法會期間在此共進行了將近兩個月的田野調查。
S念佛堂創建人本明居士a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人物姓名均做了匿名處理,年齡均以2016年的時間為統計標準;文中人物的來源地也均作了匿名處理。已71歲。他最初在D城市設立念佛道場,后應其母親及跟隨母親念佛的信眾的請求,返回河南老家建立了該念佛堂。b佛堂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本明居士退休前所工作的D城市的信眾與常來佛堂修行的信眾的捐款。同時佛堂自身也自力更生,農凈并重(與農禪并重類比),修行與勞動一體化。與都市寺院發展網絡、微信等平臺不同的是,該念佛堂自給自足,不主動化緣,僅靠信眾間的口耳宣傳。本明居士在念佛堂的運轉中大量采用軍事化管理措施,這也是該念佛堂與其他念佛道場的不同之處。很多居士之所以選擇到這里修行,就是因為這里管理嚴格,有一整套較為完善的規章制度。c這套規章制度通過“初級培訓班”的形式傳達給初來的信眾。每個初次來這里的人,前三天都要先接受初級班的培訓。初級班培訓在念佛堂東廂房一樓的“小佛堂”進行,最初負責培訓的是一位70多歲的女居士,只教一些繞念佛和拜佛的動作以及進入二樓大殿繞念佛的規矩等。2016年春開始,改由來自G省的一位年輕女居士小蘭負責培訓工作。小蘭居士的培訓工作主要依據一份內部資料,即念佛堂內部有關規約制度,內容包括“一日常規”、修學規約、日常規約、掛單規約、念佛堂共修規約、寮房規約、齋堂規約、法物流通處規約、衛生間規約,領眾修學組職責、督查員職責、接待人員職責等等,這些規章制度大部分都已打印出來貼在各個部門或殿宇門口的墻面上,其具體內容非常繁復瑣碎。其中“一日常規”除了對日常生活秩序的規定外,還包括對信眾身體的規訓。信眾在念佛堂里的行立坐臥都有具體的要求,如“行走時,步履宜穩重徐行,從容舒緩”“立不中門”“坐必直身正體,不得仰斜”“睡眠不伏不仰,右臥如弓”等;在禮儀方面也有要求,如見人鞠躬九十度,動作要緩慢;出入念佛堂要向佛像打問訊禮,出入大門要向接待室的居士行鞠躬禮等等。這些規約對信眾日常生活和修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規定。
整個念佛堂的生活節奏主要由日常念佛與節日法會組成。念佛堂踐行常年佛七,d“佛七”不是法會,佛教徒一般以7日為一個周期,在此期間集中精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常年佛七”即每天都集中精力,專心念佛。沒有周末或節假日。“常年佛七”的形式是在大殿里邊走邊念佛號“阿彌陀佛”,每天從早上4點起床到晚上10點休息,中間的18個小時幾乎被安排得滿滿的,早中晚3個時段分別只有半個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e念佛堂日常課誦作息時間表:早晨4:00起床;4:30—6:00念佛(繞念);6:00—6:30清掃;6:30—7:00早齋。上午7:30—9:00念佛(繞念);9:00—10:00聽法;10:00—11:20念佛(繞念)。中午11:30—12:00午齋;12:00—13:40午休。下午14:00—15:00念佛(繞念);15:00—16:00聽法;16:00—17:20念佛(繞念)。晚上17:30—18:00藥食;18:30—21:30念佛(繞念、拜念、止靜)。22:00安板(即打板,提示該休息了)。除日常念佛外,每年的3個節日即清明、中元和冬至期間會舉行三時系念法會。f清明法會的持續時間是7天,中元法會是半個月,冬至法會只有3天。法會的目的主要是“護國息災、超度亡靈”。法會期間如同廟會一樣,非常熱鬧,周圍鄉鎮的村民也會參加。g平時在佛堂大殿參加常年佛七的居士基本維持在三四十人左右,如2016年7月23日早課,領眾2人,女眾21人,男眾12人,共35人;24日早課,領眾2人,女眾25人,男眾13人,共40人。而法會期間,人數可達五六百人。我曾參加了其中時間較長、較為隆重的中元法會和清明法會。
與其他研究者在田野調查早期常遇到的難以進入田野或難以取得研究對象的信任不同,筆者面臨的困境則是過于“投入”田野。筆者不但與研究對象同吃同住同修行,而且研究對象從一開始就把筆者看作與他們一樣的修行者,很輕松地接納了筆者的到來及作為研究者的身份。由于必須遵循佛堂緊湊的時間安排,筆者不得不把大部分時間花在繞佛與念佛(或稱“繞念佛”)這一佛堂的主要修行實踐中,并需要不斷克服由于作息規律不同導致的困倦。
成功的田野調查的標準通常是“進得去,出得來”,當以這一標準來衡量筆者的田野調查時,常常感到困惑與迷茫,有時恍然不知自己到底是在做調查,還是在修行;或者是把自己困在了佛堂里,感覺做了一段失敗的田野。后來,由于博士論文換題,這段田野調查經歷也就被擱置了起來。當筆者從另一個視角即感官民族志的角度來重新觀照這一段田野經歷時,發現筆者當時的做法與感官民族志所倡導的理念與方法論卻有著某種程度的不謀而合。a張連海:《感官民族志:理論、實踐與表征》,《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在修行道場這樣受限的環境下,筆者無法成為傳統民族志范式中的那種以研究者為本位、想方設法從研究對象那里獲得調查資料的“索取者”,而只能成為“分享者”,b參閱趙曉榮:《主體間際分享:“他群”“我群”互動的田野》,《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即與研究對象分享自己的修行體驗與困惑,從而獲得他們的一些指導或他們的親身經驗與教訓。此外,佛堂踐行“止語”修行c止語修行也有場合與程度之分,即在正式的念佛修行場合,如大殿,齋堂等處,不能說話;在寮房或菜地干活時則可以說話;其中有部分人踐行嚴格的止語修行,在任何場合都不與他人說話,他們會在胸前掛一個止語牌,別人看到牌子,就不會上前跟他們說話,以免打擾了他們的修行。,在訪談也受限的情況下,研究者的其他感官必須變得更為敏銳,以捕捉語言以外的信息。當筆者翻看當時所做的筆記時,發現在這一過程中積累較多的是關于身體感受與情緒的比較瑣碎而又微妙的文字。通過梳理呈現這些材料,或許可以體現感官民族志的某些理念,筆者嘗試以民族志的書寫來拯救這一段“失敗的田野”。d夏循祥在分享其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經歷時曾提出,“以民族志文本來挽救失敗的田野作業”或“用寫作來證明田野沒有失敗”,并指出,“一次田野是可以被反復利用的,一次田野是可以用多重視角和多個理論框架來進行知識生產(或再生產)的。只要你真的做過田野作業。”見夏循祥:《如何拯救失敗的田野作業?》,王雨磊主編:《博士與論文》,廣州:新世紀出版社,2019年,第58頁。
對身體的發現與關注影響了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它也由此成為跨學科研究的一個重要對象。身體研究有兩個典型路徑,一是福柯(Michel Foucault)開創的身體話語分析路徑,強調“身體是權力與歷史刻寫的對象”e彭牧:《民俗與身體:美國民俗學的身體研究》,《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另一路徑強調身體本身的肉體性與能動性。后者不僅認為身體是一種技術和社會實踐,而且注重實踐中的身體感知或感覺及其對文化的意義,這種路徑逐漸發展為感官人類學(Sensory Anthropology)。感官人類學,又稱感覺人類學,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它“假設人的感覺不僅是一種生理也是一種文化活動。視聽觸味嗅不但是把握自然的手段,也是傳遞文化價值的孔道”f[加拿大]康斯坦絲·克拉森:《感覺人類學的基礎》,《國際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
在感官人類學及其民族志的理論觀照下,本文接下來將以S念佛堂的田野調查為核心,圍繞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修行過程中的“困(包括對困的克服、克制)”與“哭”這兩個充滿張力的身體感覺或情緒展開,進而考察信眾的身體感覺與修行實踐及其文化觀念的關系。
二、“困”與“哭”:修行中的身體實踐
在佛堂調研期間,筆者最主要的一個身體感受是困,也因此對其他居士不斷壓縮睡眠時間進行修行的苦行精神及其體現出的強大意志力表示由衷敬佩。此外,給筆者更大觸動和震撼的是居士在法會期間撕心裂肺、哭天搶地式的痛哭。居士在日常修行實踐中的隱忍、克制與法會期間唱佛號環節中的情緒噴發式的痛哭形成強烈對比,以致剛開始筆者都無法將不同情境中的同一個人聯系在一起。
而這兩種富有張力的身體感與情緒,與佛教的修行理念及實踐方式有著緊密的關系。佛教在苦行精神的原則指引下,一方面激勵信眾將身體作為修行的障礙與渠道,不斷挑戰身體的極限,去駕馭身體,信眾的身心也因此一直處于緊張的斗爭關系中;另一方面則在法會所營造的合理抒發情感的氛圍中,給被壓抑的情感一個發泄渠道。二者一張一弛,使信眾的身體、情感與修行實踐保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還需指出的是,在民族志的呈現過程中,研究者自身的身體感受與經驗也占據一定的位置,而且研究者通過嘗試與研究對象的身體感覺產生“通感”而推動了田野的進程與研究的進一步展開。
(一)困
繞念佛是常住念佛堂的信眾們最主要的修行方式。信眾在日常生活中踐行一種禁欲或克制的生活方式,這種苦行精神集中體現在他們的念佛實踐中。
與通常的“計數念佛”不同的是,S念佛堂的居士們主要是“計時念佛”,即以念佛時間的長短來衡量修行的進度。從早上4點到晚上10點,除了吃飯、如廁之外,都應該念佛,這是念佛堂對修行人的基本要求。在念佛堂規定的念佛時間之外,部分信眾還會通過起得更早或睡得更晚來延長修行的時間。如接待室的一位居士已有76歲,每天晚睡早起,從凌晨一點鐘起床拜佛到早晨6點鐘。
在這種環境與氛圍中,筆者發現田野調查最大的困難不是“止語”,甚至不是長時間的共修,而是瞌睡。在筆者的田野筆記中,有很多描述困感的文字,現摘錄幾則如下:
2016年7月21日早上在小佛堂繞佛(初級班的學員還不能進大殿),四點半到六點,一個半小時,一直都是一個動作一個聲調,困死我了。但跟在培訓老師后面,不敢停下來,只得忍著,使勁睜大眼睛,或使勁掐自己的手,想盡辦法打起精神,但還是困得要死。
7月23日第一次去大殿繞念佛,困得很,抹風油精、按穴位,掐手的方法都不管用。由于誤會了小蘭居士在初級培訓班的講解,以為累了就可以在角落里的椅子上坐坐休息一會兒,卻被負責管理佛堂的一位主任叫去單獨談話,這才知椅子是給身體有疾病的老年人提供的,年輕人不許坐。并被批了一頓:老年人都在努力堅持,你作為年輕人卻堅持不了;早課不允許下殿,自覺對治昏沉狀態。
7月24日,早課還是困,昨晚沒休息好,硬是死撐下來的。早課結束后,聽見有人發出了一聲長長的嘆息聲,聽得很清晰,扭頭看到新來的兩個女孩,她們說,眼睛都睜不開了。
新來者的這種難以阻擋的困感與那些睡眠時間更少的常住居士的苦行表現形成了一定的對比。其實對筆者而言,早起或睡眠時間少還不是困的唯一原因,繞念佛的形式與節奏本身就是一種“催眠術”。
佛堂設立初級培訓班的目的就是教新來者繞念佛動作,使他們到大殿參與共修時能與大家保持統一的節奏與步調。信眾念佛的節奏是緊跟廣播里一位老法師的念佛節奏:“阿、彌、陀、佛”,一字一頓,一字一步,如此大家不僅念佛一致,步調也一致,甚至走路的姿勢也一致。兩位敲法器的領眾人員,帶領男女在大殿里的一排排拜墊中呈S形穿行。大家步調緩慢而穩定,念佛號也平緩單調得仿佛四個字均在一個聲調上。本來走著念佛相對于坐著念佛來說,有對治昏沉的考慮,同時也可健身,但是這種悠緩的念佛聲調與單調的步調對初習者而言,卻不僅使人頭腦昏沉,而且容易使人身體僵硬。
念佛過程中的困感是如此強烈,筆者一直很好奇那些常住居士是如何克服身體困倦的。通過觀察發現,他們也會困,比如有一次筆者看到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的督查員苗居士在法會的念佛環節時打瞌睡。不過,他們對困的解釋則反映了佛教的某些理念,即認為困不是一種身體的生理表現或本能需要,而是因為冤親債主前來打攪所致,是一種業障a“業障”:佛教術語,指妨礙修行的種種障礙或罪惡。的表現。當筆者向一位常住居士請教如何克服昏沉時,她認為:“長時間繞佛,貴在堅持,犯困昏沉時,告訴自己能多堅持會兒就多堅持會兒,這個時候的堅持,消業障最快;這時的困是業障習氣,是冤親債主前來打擾,這時若放棄,下來休息了,就如了他們的意。”b受訪人:來自Z省的居士,四十多歲,學佛十余年;訪談人:孫艷艷;訪談時間:2016年7月23日;訪談地點:S佛堂。
雖然居士們對犯困的解釋相似,但對治昏沉的動力與方式卻各不相同。如對老年人來說,克服昏沉的動力是對于往生的迫切希望;而對年輕人來說,則更傾向于講究念佛方法。下面將分別以同屋住的四位老奶奶與一位年輕女孩為例,并輔以其他居士的體驗,來描述念佛堂居士在念佛修行過程中的身體感覺與認知觀念。
1.老年人克服困的動力
筆者第二次來念佛堂時,同屋居住著4位70歲以上的老奶奶,還有一位在大殿負責督查與領眾的中年婦女苗居士和一位年輕女孩小楠。筆者和小楠睡上鋪,四位老奶奶與苗居士睡下鋪。
筆者下鋪的老奶奶來自W市,72歲。第一天晚上她就命令筆者睡覺時不許動,并教我“吉祥臥”臥姿,以免打擾她休息。她常坐在床前以一種哭腔抱怨:“阿彌陀佛咋不來接我呀!”另一位是“俏奶奶”,70歲,她頭發長長的,編兩個辮子再交纏用發卡挽起來,有一種傳統風韻,也顯得干凈俊俏。她說她從念佛堂開始建的時候就來這里了,見證了念佛堂的發展。之前她一直在接待室工作,現在退下來了。她過年過節也不一定回家,因為兒女要上班,也很少來看她,她早就把念佛堂當成家了。
第三位是“修止語”的奶奶,73歲,豫東X縣人。用她自己的話說,她的“腰快要彎到地上了”,而且不是往前彎,而是往左彎,走起路來很費勁。即便如此,她還是堅持每天繞念佛,大殿角落里的椅子就是專門為她這種有特殊情況的人準備的。這位奶奶從2008年開始在家念佛,由于常被家務事牽絆,兩年前來這里專心念佛。她很少說話,一起住了那么久,筆者也只聽到她說過幾句話而已。她說,“我一天都不想活,你知道我每天活得多痛苦,老苦、病苦、死苦都受過了,天天都想走往生c“往生”,佛教用語,即俗稱的“死亡”。那條路。人老了,就跟田地里該拔掉的草一樣,早該走了。”“親情不如道情,道友可以天天在一起修行,吃住都在一起;家人反而遠在天邊”。筆者離開念佛堂之前,曾小聲地問過她念佛的感覺,她的回答簡潔有力,“念佛念得感覺下半身都沒有了,感覺不到了,逍遙自在。”
最后一位奶奶來自豫東S縣,71歲。她以前也在家念佛,來念佛堂的時間還不到一年。她常說,“快該走了!”俏奶奶批評她,“成天想著死,功夫不到,咋往生呢!”這位奶奶念佛很精進,常在大家下了晚課d晚課為晚上六點半到九點半持續3個小時的繞念佛。,洗漱休息之后,還會去大殿里念佛,有時念到凌晨一點多才回來休息,偶爾也會因弄出聲響而引起室友的不滿。有一次筆者問她,每天睡那么少,不困嗎?她說:“也困,沒你困得那么狠,我們跟你們年輕人不一樣,我們是后面有鞭子打著呢,不努力就往生不了,就要繼續在六道輪回里受苦。”e受訪人:豫東S縣奶奶,71歲;訪談人:孫艷艷;訪談時間:2016年8月17日;訪談地點:寮房。她在中元法會結束后就要離開佛堂了,因為她老伴已經打了幾次電話催她回家幫忙秋收。他們的兒子兒媳在外地打工。老兩口七十多歲了,還要留守在家種地。或許也正是因為留在佛堂念佛的時間不多,她才會如此珍惜和勤奮吧。a對老年人來說,經濟問題是個大問題。豫東S縣的奶奶介紹說,在念佛堂常住的生活費是每月300元,包括吃住,但這不是佛堂的硬性規定,佛堂規約里表示,不主動向信眾化緣。一般信眾會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或憑自己發心向法務流通處捐錢,多少不定,雖然是憑自己發心,但若是一直不交,也會被人看不起。過了70歲就可以申請去安養院那邊住,但是那邊要的錢多,每個月600元生活費,這是佛堂的硬性規定。如果生活不能自理的話,需要找護工伺候,一個月需要兩三千的費用,大部分老年人都負擔不起。與我同住的4位奶奶,雖然都已超過70歲,但只要還能自理,她們就寧可住在佛堂本部。
繞念佛近乎一種苦行,但很多老年人通過不斷的堅持,身體已逐漸適應了這種節奏,甚至能從中體驗到一種享受的感覺。老年人念佛固然是為了順利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但很少有人確信自己能預知時至,順利往生。因此,求往生的目的固然重要,但修行過程中的身體感受與變化更為重要,念佛不僅可以使她們擺脫老年孤獨,而且如“修止語”的那位奶奶所說,念佛還能讓她感受到“逍遙自在”。這種身體體驗或許才是真正激發她們堅持修行的直接動力與自信心不斷增長的來源,同時也是“他們判斷自己修行是否出現階梯性提高的重要依據”b謝燕清:《信仰的計量化——可行、可信的念佛往生》,陳進國主編:《宗教人類學》第七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32頁。。
2.年輕人克服困的對策
與老年人的苦行不同,筆者同屋住的小楠每天只參加念佛堂的早晚課與下午的繞念佛,上午則在村里租的房間里讀經。她不僅對佛法有自己的理解,對于念佛本身也講究一定的方法。
小楠31歲,初中學歷,19歲開始接觸佛法,從此,“其他的事不想干了,就想念佛。”c受訪人:小楠,31歲;訪談人:孫艷艷;訪談時間:2016年8月22日;訪談地點:寮房。父母受她的影響也開始學佛并支持她在這里修行。她曾向筆者描述她的念佛體驗:
念佛時感覺很清凈,內心沒有雜念,是空的。在大殿繞念佛時,走著走著,會感覺自己很輕很輕,像沒有了自己一樣,感覺很歡喜,法喜充滿,這是較為低層次的感受;高一點的體驗是,會走著走著眼前出現一片光,很殊勝;有時能聞到一種香味,不是花香的香味。d受訪人:小楠,31歲;訪談人:孫艷艷;訪談時間:2016年8月22日;訪談地點:寮房。
不過,真正吸引她的并不是這些體驗,“真正的甜頭是每天念佛都很快樂,很清凈。念的時候可能沒有太大感覺,念完之后,感覺特別歡喜。若是三天不念佛,整個人就不行了,煩惱就起來了。必須每天念佛,這是最快樂的事情。”e受訪人:小楠,31歲;訪談人:孫艷艷;訪談時間:2016年8月22日;訪談地點:寮房。小楠的這些體驗與感受是在念佛方法的基礎上達到的,她也熱心地向筆者傳授了她的念佛方法,即印光法師的十念法,念佛時在心里按三三四或兩個五來記數。她特別強調:
十念法最關鍵的地方不在記數,而是專心致志地念佛……在落實這個念佛法的時候,攝耳是最關鍵的了。當你靜心聽自己的念佛聲,就能把注意力集中起來。真正攝住耳朵的時候,其他的感覺就不在你的感覺之中,比如我的鞋子磨腳,但念佛投入之后,就感覺不到腳疼。f受訪人:小楠,31歲;訪談人:孫艷艷;訪談時間:2016年8月22日;訪談地點:寮房。
與老年人念佛求往生的目的不同,小楠更為執著于通過念佛達到清凈無雜念狀態或禪定狀態,進而獲得自在往生的把握或能力。筆者曾對她的選擇與追求表示不解:“佛教不是教育人看開、放下,積極樂觀地生活么?你怎么年紀輕輕就求往生?”她表示:
我計劃念佛三年修成“功夫成片”a“功夫成片”:佛教用語,表示念佛念到心中時時刻刻只有佛號,沒有雜念,且這種狀態能長久保持,即達到了“功夫成片”的境界。的境界,意思不是要三年后往生,而是有往生的把握。如果佛說,你走吧,你的緣分盡了,我就跟佛走。如果他說,你今生還有緣,還有事情沒有完成,那我就留下來……這樣的話,人生就很自在了,在剩下的時間里,就不會有煩惱了。反正對我來說,生死的事沒有解決,我都沒有心情去干別的事情。b受訪人:小楠,31歲;訪談人:孫艷艷;訪談時間:2016年8月21日;訪談地點:寮房。
一旁的俏奶奶則不同意小楠的說法,認為,“這是偏見!你們年輕人不是應該為眾生服務嗎?天天光念佛有啥用?”小楠并不接受這種說法,而是堅持己見:
3年之后,我念佛達到一定境界后,可以度很多很多的人,你知道嗎?先潛修多年,然后再出來弘法。我又沒玩,也不是在混日子,我有自己的計劃和目標。c受訪人:小楠,31歲;訪談人:孫艷艷;訪談時間:2016年8月21日;訪談地點:寮房。
念佛堂里像小楠這樣的女孩有十多個。如一位來自P市的大學生小夏,她畢業后工作了一段時間,然后辭職來到這里。為了學佛,她不但頂住父母的壓力,而且在糾結了兩三年后狠心與男朋友分手。她來念佛堂沒多久,就被訓練敲法器d繞念佛時大家也會互相觀察、比較。督查不僅監督大家,也會選擇年輕一些的人進行重點培養,教他們敲法器。法器包括木魚和引磬,兩個人手持法器在繞佛隊伍的最前方邊敲邊走邊念佛。敲法器的人通常一個姿勢保持不變,持續一個半小時或三個小時,很考驗人的體力。也因此,這一工作一般會選擇年輕點的人擔任。偶有年輕人過來,只要在念佛堂住上一段時間,負責領眾的居士就會教她/他練習敲法器。小楠也敲過法器,她說,她晚課敲法器連續3個小時,結束時腿都站不穩了。,后來就一直堅持在念佛堂領著一眾中老年人念佛。法會期間,我們都在“牌位組”e“牌位組”:念佛堂舉辦法會時,常住佛堂里的年輕人都要參與,有會務組、牌位組等,牌位組成員主要負責為前來參加法會的信眾寫牌位,牌位上寫的一般是信眾已逝親人,或導致自己生病的眾生的名字。信眾相信,通過邀請祂們參加法會,可超度祂們,使祂們離苦得樂,也可使信眾的身體恢復健康。此外,信眾寫牌位后,一般都會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去念佛堂的法物流通處交一定的“牌位款”,否則被邀請的“亡靈”將無法進入法會現場。“牌位款”也成為念佛堂收入的一種渠道。寫牌位,也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小夏念佛時采用的是呼吸法,即“用丹田呼吸一口氣,念兩句阿彌陀佛,兩聲換一次呼吸,以此類推,這樣可以把妄想給擠掉”;并強調要“用丹田的氣息來念,若是用肺部的呼吸去念的話,容易心口疼。”f受訪人:小夏,25歲;訪談人:孫艷艷;訪談時間:2016年8月12日;訪談地點:參加法會的路上。她也感覺念佛時心特別清凈,但沒有見光聞香一類的感應。
因為年齡相仿,筆者與這兩位女孩建立了很單純的友誼。通過與她們的交流,特別是關于念佛體驗與念佛方法方面,筆者也嘗試調整自己的心態,用她們教的方法去念佛,發現身體感受也逐漸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首先,筆者不再東張西望地觀察別人,眼皮只往下看,腦子就沒那么累了;并注意調節身體和走動的節奏,盡量使腰椎不那么累。除此之外,筆者也開始學習有意識地控制妄想,學著去屏蔽一些東西,專心聽佛號,這時突然發現佛號的聲音很響,很有力,可以震到心里去。當刻意訓練自己靜心聽佛號時,或把注意力集中到耳朵、聲音、內心上時,人就不再感覺那么累,也沒那么困了,煩惱也漸少,頭疼的毛病也輕了,慢慢地,腳步輕了,身體也輕了。筆者開始學習享受這個繞念佛的過程了,甚至覺得早課一個半小時太快,還沒覺得累呢,怎么就結束了呢。
當筆者自己體驗到念佛的微妙感受后,才終于理解苗居士的抱怨與感慨。中元節法會持續半個月,期間會有7天的打佛七。苗居士抱怨這個打佛七打得不過癮,“這里繞念佛一個半小時就結束了,念佛剛進入狀態,聽經時間就到了;不如平時過癮,特別是晚課一連3個小時的繞念佛,其中最后一個小時最管用。”a受訪人:苗居士,50歲左右;訪談人:孫艷艷;訪談時間:2016年8月23日;訪談地點:寮房。原來,那些常住念佛堂的居士,大都是已適應并享受這里生活節奏的人,并沒有筆者所想象得那么痛苦。
筆者剛來這里時,感覺最無奈、最無聊的事情就是繞念佛。那時每天繞念佛要么困得要死,要么妄念紛飛,無聊、緩慢、身體僵硬、腿疼、腳疼,半個小時都難以堅持;而且常常東張西望,看別人的各種狀態,看窗外的風景,看墻上的鐘表,總之,心不在佛號上,還常把佛號聽反了,許久都扭轉不過來,本來是“阿、彌、陀、佛……”,硬是聽成了“陀、佛、阿、彌……”完全體會不到念佛的妙處,也不能理解那些或遠或近投奔而來的信眾為什么在這里堅持做著如此無聊的事情。可以說,最初的我只是一個“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敏感的調查者,整天忙著觀察他們,想著如何構思論文,根本沒有真正嘗試以一種“感同身受”的方式去理解他們。當筆者嘗試放下論文和調查任務,以與他們相似的心境念佛時,真正的理解才可能達成。
不過,對這些年輕女孩放下萬緣、長期堅持修行的心境,筆者還是難以企及。中元法會結束后,半個月的熱鬧突然又回到單調平淡的念佛堂日常,我總有一種難以抹去的失落感,無法再平靜地回到那種單調沉悶的修行實踐中,早課繞佛時又變成了夢游。而小夏在法會結束第二天就開始敲著法器領眾繞念佛了,她臉上的沉靜與投入,既讓我佩服,同時又感到窒息。法會結束第三天,我再也沒有勇氣去大殿繞念佛了,突然就想回家了,于是迅速地辦了離單b掛單、離單,均為佛堂用語,表示信眾在佛教修行場所登記居住或離開。手續。當坐上去往高速路口的公交車時,我感覺自己像是從監獄里逃出來,貪婪地呼吸著外面的新鮮空氣。
(二)哭
雖然筆者曾努力以常住居士的心境或念佛方法去體驗他們的念佛感受,嘗試克服身體的困倦這一“業障”,去尋找那超越沉重肉身的清凈的心境,但最后的“倉皇出逃”卻徹底暴露了我難以掩飾的強烈而真實的身體感受。
常住居士們雖然各自都有著自由的精神世界,能夠感受念佛的微妙體驗或逍遙自在的境界,但念佛堂對人的身體與精神的規訓,在總體氛圍上,則是沉悶和壓抑的。念佛修行被視為一種苦行,他們的座右銘正是“以苦為師”,如不斷地壓縮睡眠時間以念佛修行,視身體為精神超越的障礙或“業障”,身心時刻處于緊張狀態中。這種苦行的修行方式不僅“嚇跑”了周邊的村民,甚至也“趕走”了一位曾在此掛單常住的比丘尼。c2016年的中元法會時,我還幫這位出家師父念祈請文。2017年清明法會時她已離開佛堂,去了H省的一座寺院。據居士們說,這位出家師父常常一個人偷偷地哭。因為這里的居士們都那么拼命苦修,作為居士榜樣的出家人,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在佛堂常住的居士多是外地人,他們要么是迫切求往生的老年人,要么是對佛教與人生有著獨特思考的年輕人,要么是患有嚴重或罕見疾病、尋求另類醫療的患者,他們各自都頂著來自世俗社會的壓力,懷著超越世俗與自我的期待,希望能在這里改變“命運”或“涅槃重生”。因此,堅持苦行的修行方式,不僅是該念佛堂所提倡的理念,也是居士們自己主動的選擇與追求。但是,人的身體不可能一直處于緊繃的狀態,該念佛堂在不斷鼓勵信眾苦修的同時,也提供了另一種讓信眾盡情發泄情緒的途徑,這主要體現在“三時系念法會”中。其實,法會活動本身就是對念佛堂日常修行實踐的調節,而這種調節不僅體現在時間安排的變化與修行內容的變動上,還體現在對居士情感的處理技術上。
1. 法會中的哭
三時系念的全稱是“中峰三時系念”,其儀軌文本是由元代國師中峰禪師編纂而成。三時指“早晨、日中、日沒三個時間段,系念指將心系于一處 ( 往生彌陀凈土)”a謝燕清:《三時系念與凈空派居士道場——以臨江凈空派某居士道場為例》,陳進國主編:《宗教人類學》第四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85頁。。但在佛堂,三個時間段被合并,改為在午后集中進行。b如2016年的中元法會開始那天上午會有一個簡短的午供儀式,下午的三時系念法會的時間安排是:第一時2:30—5:00;第二時5:30—7:00;第三時7:20—9:30,每一時的間隔會有半個小時左右的休息時間,法會共持續7個小時左右。舉辦三時系念法會時,佛堂負責人會從大寺院邀請出家師父來主持,稱為“主法法師”。法會在與念佛堂本部相距只有百米左右且建制規模相似的“公民德道教育堂”舉行。法會的儀式過程分為“起香、三時法事、回向三個大的階段,每一時法事也均由誦經、稱名、白文、行道、懺悔、發愿、唱贊七個部分組成。三時法事結構相同,層次清晰,循環遞進。”c謝燕清:《三時系念與凈空派居士道場——以臨江凈空派某居士道場為例》,第189頁。
限于篇幅,法會的具體內容與過程暫不詳論,在此只重點描述每一時中都會有的“懺悔”環節。首先是主法法師唱一句、大眾跟唱一句。然后進入主法法師與大眾共同念佛號階段,最初念六字佛號“南無阿彌陀佛”,是以一種悠緩悲切的哭調反復唱,把人們的情緒充分調動起來,居士們很快就會出現淚流滿面、泣不成聲、悲慟大哭或磕頭時用頭撞地的激烈場面。邊唱邊哭持續十多分鐘后,主法法師放高聲音把六字佛號轉到四字佛號即“阿彌陀佛”,一改剛才的悲戚綿柔,也不再哭泣,而是突然變得慷慨激昂,念佛聲也變得鏗鏘有力,且越來越快,異常急促。d信眾稱念六字佛號的悠緩悲切似乎是在表達對阿彌陀佛的熾烈感情,稱念四字佛號的急促有力則好像在表明自己堅定的信念。快速念佛同樣持續十分鐘左右后,主法法師突然放慢速度,拉著長音念一句“阿……彌……陀……佛……”大家才停下來,進入下一個環節。第一次參加法會時,那些平時踐行嚴格苦行的常住居士在“六字稱名”階段悲慟大哭的反常表現把筆者震撼到了。
“公民德道教育堂”的正殿也是三層,法會在二樓大廳舉行,由于人多,一樓和三樓設有多媒體投影,可以觀看二樓法會的現場直播。法會第一時,我在三樓通過大屏幕看現場直播,除了看屏幕,也比較留意觀察人們的表現。當看到負責初級班培訓的小蘭一邊念佛一邊淚流滿臉地大哭時,不禁目瞪口呆。
小蘭大概三十歲左右,以前在北京工作,她在網上看到S念佛堂的介紹后,就放棄了工作來這里。她讀過大學,普通話很好,對佛法也有一定的的理解,本明居士就安排她在念佛堂初級班做培訓工作。培訓之余,她早起晚睡,踐行苦修,經常在小佛堂拜佛。她不茍言笑,除了講解念佛堂規則時比較溫和外,其他時候總是板著臉,比較嚴肅,對人很嚴格,我平時也有點怕她。因此,在法會的懺悔環節中第一次看到她痛哭時,實在有些驚訝。
法會第二時,筆者轉到了在二樓的法會現場,懺悔環節中的集體痛哭帶給人的感受更為強烈。在我旁邊的一位18歲的女孩念佛號時聲音很洪亮,法會過程中的很多佛經她都會背誦,懺悔時她也和那些中老年居士一樣,哭得很厲害。另一邊有位奶奶在唱誦佛經環節一直都是悶悶的、很難受的樣子,她好像不識字,所以不會讀手里拿的經文,但到了唱念六字佛號環節時,她就從坐著的凳子上下來,跪到地上,哭得很悲切;轉到急促地唱誦四字佛號時,她也特別投入,幾乎是扯著嗓子賣力地喊。
法會第三時,我又跑到一樓,通過大屏幕跟隨二樓的現場直播進行唱念。同樣到了懺悔稱名時,攝影師特意給正在痛哭的本明居士一個特寫鏡頭,那一刻,念佛堂的“卡里斯瑪式”權威人物與大家一樣地淚流滿面,沉浸于法會所營造的悲情的情緒與氛圍中。
2. 痛哭的原因
中元法會共進行半個月,除了中間7天的共修(即繞念佛、讀《地藏經》與聽法穿插進行)外,其余7天每天的安排也都一樣,即上午繞念佛,下午與晚上進行三時系念法事,每天每一時的懺悔環節,都會有人痛哭。后來我已經見怪不怪,甚至有些懷疑他們的痛哭是否有表演的成分,或者說是否連“哭”這種本能的情緒性的身體表現也是文化規訓的結果。
不過,看到那些居士真切痛哭的場景,又很難將之與演員的表演聯系起來。如佛堂里一位不僅晚上加班、早上也是兩點多就已起床念佛的中年女居士,在懺悔環節哭得簡直是淚如雨下。另一位在裁縫部門工作的中年女居士,平時看起來很文靜,在懺悔環節時卻哭得很激烈,她趴在地上磕頭并使勁地把頭往地上撞,好像不能自抑。
若論表演,主法法師本人的表現其實是最具有表演性的,而且其表演的效果會直接影響到大眾的情緒和法會的殊勝程度。如有些主法法師哭唱佛號時,聲音有些怪怪的,會影響大眾情緒的抒發。而那些聲音嘹亮、聲調與哭腔都比較自然懇切的主法法師,則會帶動大眾很快地投入并自然地抒發情感,也能很好地營造莊嚴肅穆的法會氣氛。
法會中的“哭”也會成為大家討論的話題,甚至成為判斷法會效果是否殊勝的標準之一。筆者無意中聽到一位居士提到其他地區的一座念佛道場舉辦三時系念法會時,信眾“哭得比這還厲害,還有人專門遞紙”。
人們為什么會哭?我小心翼翼地問身邊的居士們。來自Z省的一位居士表示,這是因為阿彌陀佛太慈悲,自己已成佛,還回來苦口婆心地度眾生,卻還有很多人不相信,想到此,不由得流下眼淚;也有人可能是太想念阿彌陀佛,每天都在念祂,那種對阿彌陀佛的敬仰、熱望與等待,在這適當的場合里,統一集體發泄;當然也不排除信眾對自己以往所造罪業的真誠懺悔;再加上悲情的音樂和帶著哭腔的念佛聲,信眾之間相互感染,以致哭成一片。
其實,對于法會中人們痛哭的表現,如果看到他們平時念佛修行的努力刻苦的神情,那些早晚課上的堅持與忍耐,可能就不會覺得詫異了;如果能理解他們每個人的人生遭遇,那些飽含辛酸的苦難經歷,那些身體或記憶深處的隱痛,或許也就可以理解他們在這一刻的百感交集與奔涌而出的淚水了。
因此,酣暢痛哭這種激烈奔放的情感抒發方式與前述“困”所體現的苦行方式看似截然相反,實則相輔相成。只不過后者更多是以行動與意志來表達對宗教終極目的的向往與追求,前者則是以更為直接的方式表達或宣泄同樣的情感。二者一張一弛,既調節了信眾修行實踐的節奏,又微妙地保持了信眾身心的平衡。
三、余論:“身體感”與感官民族志的書寫
本文的民族志材料既呈現了文化對身體的規訓與刻寫,同時也呈現了具有肉體性與能動性的身體對文化的重塑,并重點呈現身體在被動的形塑與能動地創造或重塑文化的過程中所伴隨著的豐富鮮活的細微感受。這與感官人類學以及“身體感”研究的理念有所呼應。
感官人類學是基于對西方社會中的“視覺中心主義”與“文本中心主義”的批判而產生。a張連海:《感官民族志:理論、實踐與表征》,《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余舜德指出,感官人類學最顯著的貢獻在于指出“感知的內涵不只是生理的現象,亦是社會討論(或爭論)的結果,與社會階級、消費及政治的過程有密切的關系,因而亦是歷史過程的產物。”b余舜德:《身體感與云南藏族居家生活的日常現代性》,《考古人類學刊》,2011年第74期。他同時也指出了感官人類學的不足:“感官人類學將生病的感官經驗或單一的感官獨立出日常生活的層次的研究方式,較難符合人類學從日常生活層面之探討來奠定文化理論的基礎之要求。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并不單獨使用個別感官,而是整合不同的感官傳來的資訊,以便能夠隨時make sense of 周遭的狀況”。這也正是“感官人類學尚未受到人類學主流肯定最重要的原因。”c余舜德主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竹:臺灣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頁。有鑒于此,余舜德結合認知與感官人類學,提出“身體感”這一概念,來重新思考人類學的文化理論。
“身體感”一詞強調的是“身體經驗”,而非較狹義的感官經驗,它指“人們經驗身體內在與外在環境的感知項目,這些身體感知項目由幾種不同的感官知覺結合而成……身體感的項目于人們的生長過程中,于身體長期與文化環境的互動中養成”。d同上,第 15 頁。簡言之,“身體感”主要指“無法詳細區分五感(視覺、嗅覺、聽覺、觸覺、味覺等感官經驗)的一種統合的、和諧一致的身體經驗”。e張珣:《日常生活中“虛”的身體體驗》,《考古人類學刊》,2011年第74期。如饑餓感、舒適感、潔凈感、骯臟感、煩、虛、威等身體感項目,都是多重感官的結合,“而且這類多重感官的訊息常與文化的隱喻結合,更是形成文化意涵的基礎。”f余舜德主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竹:臺灣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4頁。
但如何描述和研究這種身體經驗與感覺呢?這也是感官民族志在田野工作以及書寫過程中所要反思的問題。對此,余舜德認為,“個人主觀經驗的內涵常難以詳細闡述,亦可能呈現相當高的歧異性”,因此,身體感的研究,并不探究“研究對象各自主觀經驗的內涵”,而是探究行動中“有經驗能力”的身體所呈現的表示身體經驗的身體感項目、由此所形成的感知方式以及嵌入感知方式中的主體性。g同上,第 16 頁。由此,關于身體感的研究就擺脫了狹義的感官體驗,將身體體驗與文化認知或觀念聯系起來,成為一個可以廣泛使用的分析框架。h張連海:《感官民族志:理論、實踐與表征》,《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在實踐操作方面,張連海指出,感官民族志特別突出研究者自身的體驗及其在研究中的作用。研究者不僅要與被研究者同處一個“地方”共同生活和實踐,而且在實踐活動中,研究者要“盡量模仿他者的行為,體驗同樣的感覺節奏和物質實踐,在自身體驗與他者體驗之間保持相似性與連續性”,進而產生“通感”;或以啟發式訪談激發被訪者的多感官體驗敘事等等,以此嘗試無限接近于理解和呈現他者的身體感覺,進而分析其身體感項目及其感知方式。a張連海:《感官民族志:理論、實踐與表征》,《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如研究者以學徒工的身份進行田野調查,即是展開感官民族志研究的一種重要方式。而在表征風格上,感官民族志寫作“反對僅使用冷冰冰的語言”,提倡“分析性話語與感性話語、具身形式與邏輯形式”的有機結合,“目的是創造一個盡情享受他者世界的敘事”b同上。。
本文可以說是感官民族志的一種書寫實驗,但研究者在做田野調查時并沒有這種理論自覺,只是田野過程以及所獲得的田野材料本身與感官民族志的理念有某種程度的契合之處。在民族志的呈現中,本文重點突出了居士在念佛修行中圍繞著“困”這一身體體驗以及對“困”的克服所體現出的苦行精神,并著重描述了居士在法會活動中的“哭”這一激烈的情感表達方式。可以說,“困”與“哭”均不屬于視聽觸味嗅五種身體感官中的任何一種,但都涉及到余舜德所界定的“身體感”,同時也涉及到與身體密不可分的情感,并體現出不同的情感處理方式,如對“困”的克制,體現的是一種理性、隱忍的情感,“哭”則是一種較為直接的抒發情感方式。這兩種身體感與情感是居士修行實踐過程中較為真實的表露,我們可從中更真切地了解居士這一群體的某些身體感受與訴求。
在宗教和民間信仰研究領域中,處于“修行”實踐中的身體經驗正逐漸得到關注。c如[美]威廉·詹姆斯:《宗教經驗之種種》,尚新建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年;David J. Hufford, The Terror That Comes in the Night:An Experience-Centered Study of Supernatural Assault Traditio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2;David J. Hufford,“Beings without Bodies: An Experience-Centered Theory of the Belief in Spirits,”in Barbara Walker(ed.),Out of the Ordinary: Folklore and the Supernatural,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1-45;彭牧:《從信仰到信:美國民俗學的民間宗教研究》,《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陳進國主編:《宗教人類學》第七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孫艷艷:《“經驗中心研究法”的理論與方法意義——基于對哈弗德超自然信仰研究的探討》,《文化遺產》,2019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研究均聚焦于被研究者的具體的身體經驗與感受,雖有學者注意到研究者的身份與個人性的立場對研究的影響dDavid J. Hufford, “The Scholarly Voice and the Personal Voice: Reflexivity in Belief Studies,” Western Folklore, 1995(1).,但較少關注田野實踐過程中研究者自身的身體感受。龔浩群在調查泰國城市中產階級的佛教修行實踐時,報道人所說的“如果你要理解修行帶來的生命的改變,就必須親自實踐”e龔浩群:《身心錘煉——泰國城市中產階層的佛教修行實踐》,陳進國主編:《宗教人類學》第七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213頁。,這一說法恰好可以用來提醒研究者,“只有以‘體知’的方式,反思自身的各種身體感覺,才能真正把握身體性的文化知識與實踐,特別是宗教實踐。”f彭牧:《民俗與身體:美國民俗學的身體研究》,《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
總之,研究者自身的體驗與感受在理解研究對象身體感受與修行實踐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研究者不僅嘗試與研究對象產生“通感”,而且通過感性細膩的書寫,在盡可能深入呈現研究對象的生活與生命經驗的同時,也希望引起讀者的移情性參與,激發其親切感和“通感”,以此更好地理解研究對象的身體感覺與精神世界,并達至更多的相互理解與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