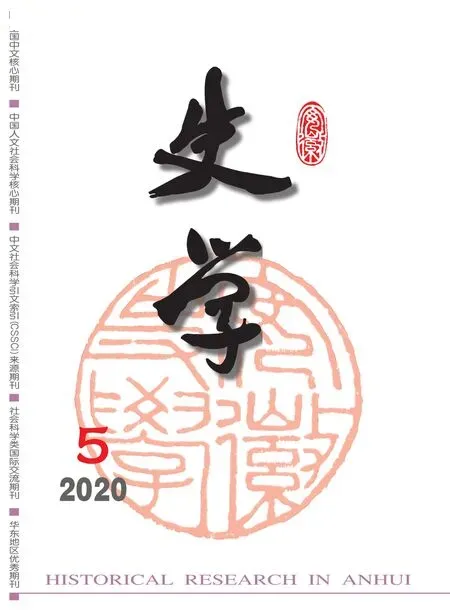從王恭廠災的神異化書寫看明末政治及社會生態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 300350)
公元1620年,明神宗和繼立為君的明光宗相繼崩逝,明熹宗朱由校年少登極,改元“天啟”。此時的明王朝,社會危機此伏彼起,已處于搖搖欲墜之勢。天啟六年(1626年)京師的王恭廠火藥災,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突發的。有關天啟六年王恭廠災的研究,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研究成果頗豐。(1)參見耿慶國、李少一等主編:《王恭廠大爆炸——明末京師奇災研究》,地震出版社1990年版;劉志剛:《天變與黨爭:天啟六年王恭廠大災下的明末政治》,《史林》2009年第2期;梁國堅:《明天啟六年王恭廠災變之氣象成因探析》,《自然科學史研究》2008年第1期;李樹菁:《明末王恭廠災異事件分析》,《災害學》1986年12月創刊號,等。但諸多成果主要集中于關注王恭廠災的成因,以自然科學的視角對其突發的原因進行解讀。本文擬將這次災變與當時特殊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相結合,以時人對王恭廠災的神異化書寫為視角,管窺明末衰世下的政治環境狀況和時人的恐慌心理,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天啟衰世及王恭廠災
王恭廠災雖說是一個獨立的災變事件,但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狀況有著極為緊密的聯系,是在明末天啟年間特殊的社會環境下發生的一次對政治和社會均產生重要影響的災變。
(一)天啟年間的衰頹氣象
明熹宗沖齡踐祚,時有高攀龍、左光斗、楊漣等多位萬歷、泰昌舊臣進行輔佐,似有一番振作氣象。明熹宗初即位,即上諭百官,稱“朕奉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以亂朝政,特茲再加申飭。以后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2)顧炎武撰、嚴文儒等點校:《熹廟諒陰記事》,《顧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頁。在萬歷后期黨爭日熾的政治背景下,又開始出現“眾正盈廷”的良好局勢。但這種良好勢頭終是曇花一現,熹宗之昏聵無能隨之暴露無遺。明熹宗是在乃父光宗朱常洛登極一月突然崩逝之際即位的,未來得及接受正規、持久的皇儲教育,加之性好頑劣,治國理政非其所能。據明末宦官劉若愚所記,“圣性又好蓋房,凡自操斧鋸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監、內官監辦用”,以至“端拱于上,惟客、魏之言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3)劉若愚:《酌中志》卷14《客魏始末記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2、70,74頁。朝政逐漸被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所把持,權傾朝野,一片烏煙瘴氣。《酌中志》對其有詳細的記載,魏忠賢把持朝政之后,“凡出外之日,先期十數日庀治儲偫于停驂之所,賚發賞賜銀錢,絡繹不絕。小民戶設香案,插楊柳枝花朵,焚香跪接。冠蓋車馬繽紛奔赴,若電若雷,塵埃障天,而聲聞于野。有狂奔死者,有擠蹈死者,燕京若干大都人馬,雇賃殆盡。”(4)劉若愚:《酌中志》卷14《客魏始末記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2、70,74頁。
與此同時,地方民變蜂起,尤以江南地區為甚。天啟年間(1621—1627年),南直隸就發生多次民變,著名者有徽州黃山之變、揚州鹽商之變以及蘇州緹騎之變,時人驚呼“國朝三遭大變,皆屬古來所未有”。(5)張怡撰、魏連科點校:《玉光劍氣集》卷1《帝治》,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36頁。土地兼并日趨激烈,農民破產流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一觸即發。更令朝野擔憂的還是敗報頻傳的遼東戰事。此時,崛起于遼東且已然形成氣候的滿洲貴族,多次出兵騷擾明朝邊地,逐漸成為與明廷分庭抗禮的強大地方勢力,隨即建立與之對峙的獨立政權。天啟元年,“大清兵入渾河。甲寅,圍沈陽。”(6)夏燮撰、沈仲九點校:《明通鑒》卷77《熹宗天啟元年》,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048頁。而后隨著遼東重鎮沈陽的失守,明廷日益轉為戰略被動狀態。次年,“大清兵入廣寧,凡四十余城皆下,遂進克義州而還。”(7)夏燮撰、沈仲九點校:《明通鑒》卷78《熹宗天啟二年》,第3074頁。至天啟五年,努爾哈赤遷都沈陽,以沈陽為大本營,進窺明朝內地。至此,遼東主要城池盡失,邊防告急。
天啟年間,門戶日開,閹黨專權,社會動亂,邊備吃緊,明王朝已是積重難返,盡顯衰頹氣象。王恭廠火藥災正是在這種政治環境和社會狀況下突發的,隨之對時政的憂慮和對末世的恐慌感一直籠罩在時人心頭。
(二)王恭廠及災變概況
天啟六年,京師發生了一次駭人聽聞的災變事件,即為人所熟知的王恭廠火藥災。從時人的記載來看,這次災變極為罕見,波及范圍廣,傷人無數,破壞性大,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后果。
這次災變的發生地王恭廠,是明朝設于京師專司制造火藥的機構之一,與盔甲廠、琉璃廠等同為工部下屬機構。明遺民史玄記載道:“京師諸火藥局以王恭廠為大,舊在城西南包家街”(8)史玄:《舊京遺事》卷2,清退山氏鈔本。,具體位置在“宣武門里,順城墻往西,過象房橋,安仁草場,至都城西南角”。(9)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頁。同時,其與盔甲廠一起,“兼領專掌修造軍器”。(10)何士晉:《工部廠庫須知》卷8,明萬歷林如楚刻本。其中,設“掌廠太監一員,貼廠、僉書十余員。轄匠頭六十名、小匠若干名。營造錢糧與盔甲廠同。”(11)劉若愚:《酌中志》卷16《內府衙門職掌》,第123頁。《春明夢余錄》亦載,“凡京營火器所用鉛子火藥,系工部王恭廠等預造,以備京營領用。”(12)孫承澤撰、王劍英點校:《春明夢余錄》卷31《戎政府》,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476頁。由此可知,王恭廠作為專門制造火藥的機構,內部設員完備、職責明確,與王朝國家的軍備供需有著密切的聯系。
時人有關王恭廠災的記載頗多,現采擷部分記載以窺其概貌。天啟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火藥局也。是日雷震,火藥自焚,地中霹靂聲不絕,煙塵障空,白晝晦冥,被災及暈仆死者無算。”(13)夏燮撰、沈仲九點校:《明通鑒》卷80《熹宗天啟六年》,第3157—3158頁。這次災變,波及范圍極為廣泛,“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變相同”(14)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卷2《丙寅五月初六紀異》,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3頁。,且“遵化去京三百里,皆聞其聲”(15)楊士聰著、于德源校注:《玉堂薈記》,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頁。,致使京師“平地陷二坑,約長三十步,闊十三四步,深二丈許”。(16)吳長元:《宸垣識略》卷7《內城三》,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頁。明人金日升在其《頌天臚筆》中記載更為詳細,王恭廠災發生后,“俄頃,有聲如震雷,西北起,振撼天地,黑云乘之簸蕩,壞民居室,數里無存。巨石從空飛注如雨,男女死者以數萬計,驢馬雞犬皆盡斷臂、折足、破額、抉鼻者,枕籍街衢咸滿。”(17)金日升:《頌天臚筆》卷22《附紀》,明崇禎二年刻本。
此次災變破壞性極大,由此在當時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在傳統社會,災變往往視為“神怪之譴”,對其賦予神異色彩,王恭廠災相關的神異化記載也隨之紛至沓來。
二、明清時人對王恭廠災的神異化書寫
王恭廠災及災變前后頻發的各類異象,在時人的筆下盡顯神異,不論從書寫方式,還是從所記災變時人的心理狀態來觀察,都與一般的水旱災害大相徑庭。
(一)時人對王恭廠災前后相關災變的認識和書寫
天啟年間為明朝多事之秋,各類災異迭發。王恭廠災突發之前,見諸于各類記載中的有關異象俯拾皆是,且多被賦予神異化色彩。
據《明季北略》記載,天啟四年(1624年)二月,“天黃,日淡無光,次日亦然。見日旁有黑日蕩磨。是晚,聞空中叫嗥,如千軍萬馬突臨之狀,又若萬炮競放,聲震天地,舉邑驚惶。”(18)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卷2《辛酉七年紀異》,第71—72、72、73頁。天啟六年五月,各類異象更是接踵而至。“五月朔,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門,官吏輿從俱各昏迷。有一皂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乃在廟管門。”(19)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卷2《丙寅五月初六紀異》,第75、75、74—75頁。又據《天變邸抄》載,天啟六年五月初二夜,“鬼火見于前門之樓角,青色熒熒如數百螢火。俄而合并,大如車輪。”(20)佚名:《天變邸抄》,轉引自耿慶國、李少一等:《王恭廠大爆炸——明末京師奇災研究》,第8頁。著名史學家談遷也將其所見之異象收入《國榷》中,說道:“玄武門火神廟守門內臣,聞樂音三疊出自廟中,見有火球滾出騰空而去。眾方屬目,俄東城聲如霹靂,天地昏黑。”(21)談遷撰、張宗祥點校:《國榷》卷87《熹宗天啟六年》,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5326頁。這類富于濃厚神怪色彩的災變事件,在王恭廠火藥災爆發之前可謂數不勝數,史料記載也是隨處可見,此不贅述。火藥災突發之前的諸多異象,被視為重大異變即將到來的前兆,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正是時人心理層面恐慌焦慮情緒的生動寫照。
與之相較,王恭廠災發生之后的一連串神怪事件記載,更能凸顯時人內心揮之不去的恐慌感。王恭廠災發生后,朝天宮火災起,“遙見紫衣神排空而起。先是,正殿一向鎖閉,不爇香火。至是,突然火從正殿起,延燒毀前后兩殿,并廊房一百一十間。”(22)張怡撰、魏連科點校:《玉光劍氣集》卷28《徵異》,第1004頁。同日,“廣昌縣地震,搖倒城墻,開三大縫,有大小妖魔日夜為祟,民心驚怖。”(23)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卷2《辛酉七年紀異》,第71—72、72、73頁。又據朱祖文《北行日譜》載,“嚴秀道經錦衣衛,見黑氣一道從衛前起,直透空中,風不能動”,數日后,“聞皇極殿前階石費帑金如千,經年累月而始至者,大工方特之告成,甫及殿忽斷”。(24)朱祖文:《北行日譜》,明崇禎二年張世偉刻本。除了諸多有關異象的書寫外,天啟末年,多地還發生大風、地震等災害。同年八月,“江南有拔木之風,古今少見”,十一月,“南京陵寢地震。二十五日,寧夏地震,六月、九月俱震,半年三震”。至七年,“正月十八日卯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南,以至東北,房屋傾倒,傷人無數。”(25)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卷2《辛酉七年紀異》,第71—72、72、73頁。
(二)對王恭廠災的神異化塑造和描繪
王恭廠災發生于明末衰世,且隨之伴生諸多異象,再加上其爆炸本身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和財物損失,明清之際許多人不論目睹還是耳聞,都對其極盡渲染。災變發生的前一夜及當日黎明,似乎就有種種征兆。在京師都城隍廟中,“初五夜,道士聞殿中喧嚷叫呼,絕似唱名之聲”(26)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卷2《丙寅五月初六紀異》,第75、75、74—75頁。,至六日黎明,多人見到“東城有一赤腳僧,沿街大呼曰:‘快走!快走!’”而更為人所驚異的是,“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發,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大驚,墮馬,傷額。方在喧嚷間,東城忽震。”(27)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卷2《丙寅五月初六紀異》,第75、75、74—75頁。在這些異象出現不久即發生了王恭廠火藥災。
對于此次罕見災變,《明熹宗實錄》記載道:“王恭廠之變,地內有聲如霹靂不絕,火藥自焚;煙塵障空,椽瓦飄地,白晝晦冥,西北一帶相連四五里許房舍盡碎。時廠中火藥匠役三十余人盡燒死,止存一名吳二。”(28)《明熹宗實錄》卷71,天啟六年五月戊申,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明實錄》校印本,第3420頁。可見這次火藥爆炸的巨大破壞力。與官方記載不同的是,在時人筆記和文集中,這次災變多呈現神怪化色彩。明代散文家劉侗在記明代北京風俗掌故的專書《帝京景物略》中對王恭廠災有頗為詳細的記載:
天啟六年五月初六日巳刻,北安門內侍忽聞粗細樂,先后過者三,眾驚而跡其聲,自廟出。開殿審視,忽火如球,滾而上于空。眾方仰矚,西南震聲發矣。望其光氣,亂絲者,海潮頭者,五色者,黑靈芝者,起沖天,王恭廠災也。東自阜成門,北至刑部街,亙四里,闊十三里,宇坍地塌,木石人禽,自天雨而下。屋以千數,人以百數,燔臭灰瞇,號聲彌滿。死者皆裸,有失手足頭目,于里外得之者,物或移故除而他置之。(29)劉侗、于奕正著,孫小力校注:《帝京景物略》卷1《城北內外·火神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頁。
從這段記載來看,王恭廠火藥爆炸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傷害,且頗顯神秘氣氛。除此之外,亦有更為離奇之事出現。“長安街空中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頭,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云。石駙馬街有大石獅子,重五千斤,數百人移之不動,從空飛出順城門外。”(30)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卷2《丙寅五月初六紀異》,第76、76、73頁。更有甚者,“凡死傷盡裸露,衣服飄掛西山之樹,昌平教場衣服成堆”(31)談遷撰、張宗祥點校:《國榷》卷87《熹宗天啟六年》,第5326頁。,“圓弘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人衣飾盡去,赤體在轎,竟亦無恙”。(32)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卷2《丙寅五月初六紀異》,第76、76、73頁。震聲甚至震動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聲如雷鳴,中外恐懼”。(33)朱長祚撰、仇正偉點校:《玉鏡新譚》卷6《筑城》,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86頁。
三、災變神異化所見明末政治及社會生態
一定社會現象的產生必然基于所處時代特定的社會環境,且往往與王朝政治環境變化有著密切的聯系。明末王恭廠災的突發,且被時人賦予神異化色彩,毫無疑問,這是在明末衰世下災變的伴生現象。天啟年間,明王朝已然積弊叢生,政治混亂,加之兵連禍結、各種災變不斷,這種社會環境正是催生神怪言論的沃土。
(一)對閹黨專權形勢下政治亂象的怨憤與指責
自萬歷中后期開始,明朝政局日壞,黨爭熾烈。至熹宗登極,司禮監掌印太監魏忠賢在除去王安、魏朝等政治障礙后,與熹宗乳母客氏沆瀣一氣,專擅朝政。在這種形勢下,朝臣逐漸分化為兩大派,一派以顧秉謙、田爾耕、崔呈秀、魏廣微等人為代表,史稱“閹黨”;一派是以楊漣、左光斗、高攀龍等為代表的東林黨。在東林黨與閹黨政爭進入白熱化階段時,震動京師的王恭廠災爆發。此時,明熹宗也頗感震驚,遂傳諭“內閣即示工部、督察院并巡視科道及巡城御史兵馬、本廠監督主事:‘速赴王恭廠巡看救火,不許稽遲。’”(34)《明熹宗實錄》卷71,天啟六年五月戊申,第3419—3420頁。同時,熹宗敕諭群臣修省,稱:“朕以渺躬,御極值此變異非常,飲食不遑,栗栗畏懼。念上驚九廟列祖,下致中外駭然,朕當即齋戒虔誠,親詣衷太廟,恭行問慰”(35)《明熹宗實錄》卷71,天啟六年五月己酉,第3422頁。,希圖以修省的方式消弭災變。
但是,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不但視災變示警為無物,不遵上意進行修省,反而加緊迫害和打擊政敵。廠災突發之時,欽天監周司歷奏占:“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地中洶洶有聲,是謂兇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亡。”(36)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卷2《丙寅五月初六紀異》,第76、76、73頁。其占應直指魏忠賢、客氏專權亂政。魏忠賢稱之為妖言惑眾,將欽天監官杖責致死。在災變迭發之時,東林黨人周宗建上疏彈劾魏忠賢,“疏入,珰恨之,卒被逮。備受慘毒,夜半囊沙以死。”(37)張怡撰、魏連科點校:《玉光劍氣集》卷5《敢諫》,第224頁。清人張怡對之頗為同情,他在《玉光劍氣集》中記載道:“時謂公初逮時,京師地震,入獄就勘,王恭廠雷火,再出訊,下冰雹,歿之日,朝天宮災。”(38)張怡撰、魏連科點校:《玉光劍氣集》卷5《敢諫》,第224頁。很明顯,張氏將災異之譴歸于閹黨專權,視之為有違天意之舉。
王恭廠災突發之時,熹宗雖下詔修省,但因昏聵無能,在閹黨的簇擁下,深信“東林邪黨盈朝。或陷朕于不孝,或棄祖宗封疆”(39)李遜之:《三朝野記》卷5《天啟朝紀事》,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頁。,這無疑助長了閹黨的囂張氣焰。“甲子以來,逆珰肆惡,兇焰益熾。恣殺忠良,天日為之無光,是以市曹怨鬼長號;褫奪冠裳,國士因而無色,系之旦夕身家莫保。海內震動,災異迭見,人心恐懼,寢食相忘。朝廷屢下修省之明詔,逆珰全不轉念于天警。”(40)朱長祚撰、仇正偉點校:《玉鏡新譚》卷5《災沴》,第77、79—80、80頁。明人朱長祚此段言論當是天啟末年多數人對閹黨痛恨心聲的吐露。災變出現后,南京兵部尚書王永光曾兩次上疏明熹宗,將災變視為天怒,其因由則是閹黨越權用事,擾亂視聽。其疏云:“上天一怒,而地震如雷,萬象傾覆;再怒,而祝融為虐,朝天宮付之烈焰矣。以四方輻輳之地,半屬丘墟;千官呼祝之壇,盡為灰燼。”(41)朱長祚撰、仇正偉點校:《玉鏡新譚》卷5《災沴》,第77、79—80、80頁。他認為之所以出現如此罕見的災變和各種異象,是上天對人間政治失和表示不滿以災沴譴告,這種思想正是對王恭廠災及相關災變進行的神異化描繪所要傳達和傾吐的。由此時人感嘆道:“是時逆珰殘暴,信手殺人,彈章一人,立為齏粉。懸贓破產,復殺其妻子,株累無辜,以觸天心震怒,災異薦臻”(42)朱長祚撰、仇正偉點校:《玉鏡新譚》卷5《災沴》,第77、79—80、80頁。,對閹黨把持下畸形政治的不滿和痛恨之情可見一斑。為了避免正面抵觸和批判閹黨竊權亂政,時人在書寫災變狀況時多對其進行神異化描繪,以表明內心對閹黨肆意殺戮而不修省的深惡痛絕。
(二)對衰世背景下混亂社會狀況的心理恐慌和困惑
若從這次災變的慘烈程度來看,“火驟發沿近屋舍,因而象房震倒,群象驚逸出,不可控制”(43)高汝栻:《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15,明崇禎九年刻本。,且“有同伴頭去比肩無恙,有從空墜人頭及須發耳鼻,大木遠落密云,石獅擲出城外”。(44)吳偉業撰、李學穎點校:《綏寇紀略》卷12《虞淵沉上·火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頁。由此可見,這次災變造成的后果遠較一般的地震、火災嚴重,在普通小民看來,是懼怕和憂慮的。京城無數百姓罹難,“市覘之男女老幼,負者兩人肩者,扶而掖者,或已斃,或尚流血。擁而號泣者,聲徹于道。”(45)薛岡:《天爵堂文集》卷7《紀丙寅五月六日京師所覯異變始末》,明崇禎刻本。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時人頗迷信鬼神之說,認為“自天地神祇,以及圣賢忠烈沒而為神者,皆是也”,且“夫有物則有鬼神矣”。(46)龔煒撰、錢炳寰點校:《巢林筆談》卷6《鬼神》,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64頁。人們多對廠災的發生因由不明就里,往往出于主觀臆測,并融入豐富的想象,將之視為“神怪之譴”,與深入人心的神鬼觀念相結合來解釋這場災變,并進而借其表達內心的恐慌。
當然,時人這種反映在災變神異化書寫方式中對衰世的恐慌,不僅來自于神鬼觀念作用下對致災之由的主觀臆測,還主要基于當時真實的社會環境狀況。據《舊京遺事》記載,“國家十世宴清,京師數百里之間,物無夭札,民不疾厲。神熹之年,始不戒于火,而天降之滅,風霆變化,日有其事,然在于今而尤烈。”(47)史玄:《舊京遺事》卷2,清退山氏鈔本。至萬歷、天啟年間,京師各主要國家機構的管理日趨松懈,上行下效,使得整個社會環境日益走向混亂。京師各衙門官員玩忽職守,規制松弛,以致監管不力。京師如此,更遑論地方官府了。明朝時期的北京乃宸居之地,四方輻輳,軍民雜處,三教九流多混跡于此,到了明末更顯魚龍混雜。據陳寶良的研究,明朝時期的北京城內,“專有一批不務生理的喇唬,他們三五成群,非華衣不穿,非美饌不食,宿娼買奸,百無禁忌”(48)陳寶良:《中國流氓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頁。按,所謂“喇唬”,清人解釋即“詐騙之匪也”。喇唬這一類不務正業的流氓惡棍,在明朝京師以及地方大邑普遍存在,時常口稱圣號,大白天在街上倒地撒潑,引人圍觀。喇唬在明初雖有零星的出現,但怯于明太祖所行高壓政策,人數不多。至正統以后,喇唬勢力在各大城市重新崛起,并在社會上逐漸擴大,至成化、弘治時期達到極盛。至明末,以喇唬為代表的流氓群體更成為擾亂社會秩序的淵藪之一。,成為社會的亂源之一。有關王恭廠災的各種奇異事件的記載,正基于明末混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在王恭廠災發生后,“焦頭爛額、四肢不全者甚多,男子尚有單裈、婦人皆無寸絲掩羞。”(49)朱長祚撰、仇正偉點校:《玉鏡新譚》卷6《筑城》,第86頁。且更為離奇的是,凡受災死傷者皆裸露,而“圓弘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人衣飾盡去,赤體在轎,竟亦無恙。”(50)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卷2《丙寅五月初六紀異》,第76頁。當廠災發生之際,京師流氓、惡棍,甚至不法軍士,多趁機制造混亂,襲殺平民,奸淫婦女,行罪惡不法之事。無疑,在災變迭發之時,人為制造的混亂更加劇了整個社會的不安和恐慌。
(三)王恭廠災下政治預言與災異天譴說的一度興盛
天啟初年,明熹宗仰賴楊漣、左光斗、劉一燝等文臣及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安的聯手努力,雖一時出現升平氣象,但這只不過是政治混亂和宿弊久積之后出現的表象,隨之而來的是更為嚴重的政治亂象。閹黨把持朝政,大肆迫害和打擊政敵;又遇遼事大壞,在滿洲鐵騎的步步進逼之下,明軍節節敗退,迨至遼陽失陷后,“廣寧至三岔河幾三百里無人煙”。(51)李遜之:《三朝野記》卷2《天啟朝紀事》,第42頁。在這種衰象已現的局勢下,王恭廠災爆發,京師震動。與此同時,各種水旱災害不斷,且持續時間長,南北兩京皆地震,因此時人多將這一系列災變視為國變之示警。從對王恭廠災及相關災變的神異化書寫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時人對明王朝國家政治前途的失望與憂慮。尤其是在明朝滅亡之后,明遺民在記述天啟間王恭廠災及其相關變異之時,因對國破家亡、改朝換代有著切身的體會,由此他們更相信天啟間的巨大災變是上天之示警,是昭示明朝走向末世的征兆。
值得注意的是,王恭廠災突發之際,各類災害并作,時人多歸咎于閹黨的竊權亂政和倒行逆施,“說者為魏忠賢殺戮忠良之感,猶六月飛霜之異,上天示警焉”。(52)朱長祚撰、仇正偉點校:《玉鏡新譚》卷5《災沴》,第79頁。很明顯,這是在指斥閹黨亂政引發了上天的譴告,是逆天之舉。而歷經明清易代的人們更有著深刻的感悟,基本上都認為王恭廠災預示著明朝氣數已盡,是天命即將轉移的預兆。當李自成攻占北京,清朝入主中原之際,這種災變預警更為人深信不疑。由此不難理解,明清人多將王恭廠災進行神異化書寫,除了有其痛恨閹黨專權下的黑暗政治和揭露社會現狀的目的之外,還凸顯著政治預言和災異天譴的因素,意在印證明朝滅亡并非偶然,而是一種在天譴預警下的必然結果。“熹廟登極以來,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無不疊見,未有若斯之甚者。思廟十七載之大饑大寇,以迄于亡,已于是乎兆之矣,而舉朝猶在醉夢中,真可三嘆”(53)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卷2《丙寅五月初六紀異》,第76頁。,正是這種心理因素的生動寫照。極為巧合的是,至崇禎帝即位時,正舉行登極大典,“諸臣方呼拜,忽天鳴,竊心異之”。(54)談遷撰,羅仲輝、胡明校點校:《棗林雜俎》智集《登極天鳴》,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72頁。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朝行將滅亡之際,“甲申三月十三日,孝陵夜哭,都人喧傳。張藐山先生聞之嘆曰:雖訛言,亦其應也。”(55)談遷撰,羅仲輝、胡明校點校:《棗林雜俎》智集《孝陵夜哭》,第93頁。這些有關政治預警異象的出現與天啟年間王恭廠災變如出一轍,且不論其真假虛實,如此記載,毫無疑問是對這些末世徵應進行渲染,以突顯災異譴告在王朝興衰更替中所扮演的特定角色。
以異象為表征的政治預言及災異天譴說與王朝統治秩序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古人通常認為“異常現象的首要起因是人的精神狀態或社會行為”(56)[英]胡司德著、藍旭譯:《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頁。,且多流露出時人對現世社會的不滿、懷疑與批判。(57)參見余焜:《明中葉異象頻發及其因素探微——以成化、弘治時期為中心的考察》,《寧夏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這種思想雖說產生于心理層面且不乏迷信成分,但人們往往將其運用于具體的政治運作中,以解釋王朝統治的合法性以及天命歸屬問題。這種思想還常與災異天譴說相結合,甚至摻雜進鬼神觀念,以表達某一特定時代背景下人們內心對王朝統治的認可抑或否定態度。在天啟衰世背景下,王恭廠災突發之際,這種災異預言甚囂塵上,即是很好的明證之一。
結 語
在“天命論”影響下的傳統社會,多種災害的來臨多使人產生畏懼恐慌心理,尤其是當一些與自然規律和人們內心所愿相悖的奇異災害突發之時,人們往往視之為“天譴”。這類災害,明清時人通常稱之為“變”,以異象視之,并賦予其濃郁的政治色彩。而這些被視為上天譴告而降下的災變,又往往預示著人間社會的混亂和失穩,尤其在王朝政治亂象頻生以致行將崩潰之際,人們多借此來傳達內心對現實政治的不滿情緒,同時揭露和批判混亂的社會狀況,從而很自然地流露出身處王朝衰世內心的困惑與恐慌。
其實,不論是天命觀還是自然規律,都是人類借助于外部秩序來解釋社會秩序的參照,傳統社會中正是將代表上天意志的宇宙秩序和規律與人間社會狀況統一于同一秩序范疇之內,并將上天意志的表達作為解釋人間社會統治秩序的衡量標準。這種思想觀念在明末王恭廠災突發之際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應用,時人對王恭廠災的神異化書寫,賦予災變神秘離奇的色彩,將之視為“天譴”,旨在表達對閹黨把持下的黑暗政治秩序的不滿和痛恨,以及社會混亂狀態下內心對王朝前景的擔憂及恐慌。不難推知,對衰世局面的恐慌和對政治前途的憂慮,是深植于生活在明末人們心中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富含神怪色彩的災異天譴說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也頗為流行,在明末多事之秋為人所深信不疑,尤其是王恭廠災發生一二十年后,明王朝轟然傾覆的歷史巨變,似乎正成為印證這種災變徵應的現實依據。我們且不論這種災變神異化書寫下的種種怪異事件是否真實存在,這種歷史現象的產生必然基于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且滲透著時人對所處時代現實政治和社會狀況的真切認識和關注。透過這一歷史現象,時人困惑和不安的心理世界也大致展現在我們眼前,這為我們認識和研究晚明社會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