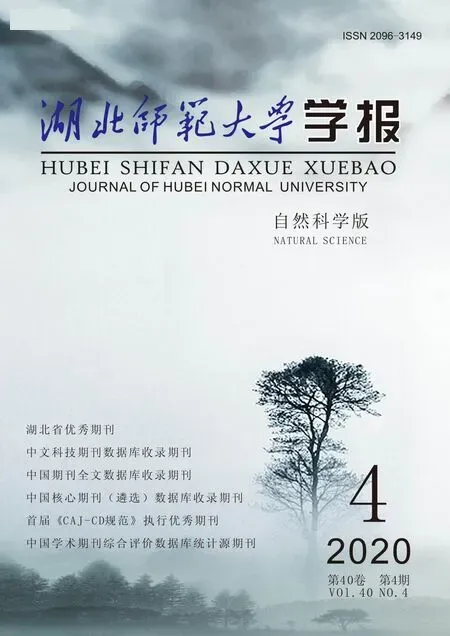三峽庫區三個養殖鱘魚物種微衛星多態性分析
張潤鋒,焦明靜,2,柯年峰,3
(1.湖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國家級生物學實驗教學示范中心,湖北 黃石 435002;2.思源實驗學校,湖北 丹江口 442700;3.竹溪縣第一中學,湖北 十堰 442300)
全世界已發現27個鱘魚物種[1],大多數物種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列為瀕危或極危物種(IUCN, 版本2019.3查詢2020.3.16)。歷史上有幾個鱘魚物種,如達氏鱘(Acipenserdabryanus)、中華鱘(Acipensersinensis)和白鱘(Psephurusgladius),曾廣泛棲息于長江中上游及其大多數支流[2]。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這些物種是長江上游漁業捕撈的重要對象[3]。然而,由于水壩建設、棲息地環境惡化和過度捕撈等原因,在過去幾十年里這些物種的自然群體急劇下降[4,5]。20世紀80年代,為了挽救長江中的鱘魚物種,這些物種被列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并開始禁止在長江中捕撈鱘魚[6]。同時,相繼啟動了最大的國家保護計劃,并從2000年開始長江上游實行禁漁期制度[7]。一些鱘魚物種在孵化場實現了人工孵化,并將人工孵化幼魚放流長江以恢復種群。
位于長江三峽庫區的宜昌被譽為中華鱘的故鄉,是中國鱘魚人工繁育最大基地之一。自然群體和養殖群體的多樣性為鱘魚適應變化的環境提供了必須的基因型范圍。雜合度豐富的群體中個體在生長、生殖和疾病抗性方面優于雜合度低的群體[8]。鱘魚群體遺傳學研究可以為鱘魚物種的管理、可持續發展和保護提供有用信息[9,10]。微衛星已經應用于鱘魚種群結構、親魚鑒別等方面,以保護鱘魚多樣性和維持人工繁育近交最小化。本研究利用微衛星遺傳標記分析長江三峽庫區三個人工養殖鱘魚物種歐洲鰉(Husohuso)、達氏鱘(Husodauricus)和雜交鱘(Acipenserschrencki♂×Husodauricus♀)的遺傳多態性。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研究樣本采自湖北天峽鱘業有限公司(宜都市紅花套鎮,宜昌)。隨機采集147只7齡以上的鱘魚魚鰭組織,包括83只歐洲鰉、38只達氏鱘和26只雜交鱘。
1.2 PCR分析
按照試劑盒使用指南,利用QIAGEN DNA Mini Kit(Qiagen, 美國)從魚鰭組織提取基因組DNA.1%的瓊脂糖凝膠電泳檢測提取DNA的質量。利用8個微衛星遺傳標記[11,12]對三個人工養殖鱘魚群體進行多態性分析。微衛星遺傳標記引物由北京奧科鼎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
PCR反應在96孔Bio-Rad MyCycler(Bio-Rad,美國)進行。采用混合加樣法,即根據每一個反應體系所需的各組分量和PCR反應的個數,將各反應組分所需總量計算出來,加入1.5 mL的EP管中,輕微震蕩充分混勻后瞬時離心,再分裝到每個加有模板DNA的PCR管中,瞬時離心,冷啟動擴增。最終,15 μl的PCR反應體系包括0.4 U的Taq DNA聚合酶(Tiangen, 北京)、上下游引物各0.4 mM、四種dNPT各0.25 mM、2.0 mM MgCl2和1 ×Taq反應緩沖液。擴增反應包括95 ℃預變性2 min,30個循環(94 ℃變性30 s,退火30 s,72 ℃延伸45 s),72 ℃延伸10 min.微衛星標記引物序列、退火溫度見表1.

表1 本研究應用的微衛星遺傳標記的引物信息
1.3 微衛星分析
取每個個體PCR擴增產物7μL和pBR322/MspIladder(Promega, 美國)4μL,加至8%的聚丙烯酰胺凝膠(29∶1 acrylamide∶bis acrylamide, 1 × TBE buffer),先300V高壓電泳15min,然后200V電泳2h左右。
電泳結束后,將凝膠轉移到盛有蒸餾水的托盤中,用蒸餾水沖洗2次。加入10%乙醇固定10 min,棄去固定液。加入0.1% AgNO3溶液,放在脫色搖床上輕微搖晃15~30 min后,將硝酸銀溶液倒掉,用蒸餾水沖洗2次,每次15 s.加入2% Na2CO3溶液(用前加2mL甲醛,混勻)顯色,待條帶清晰后將溶液倒掉,然后加入4%乙酸溶液停止顯色。對凝膠拍照。
1.4 數據統計分析
每個DNA條帶大小通過與pBR322/MspIladder(Promega, 美國)比較估計片段大小。根據每個個體片段大小和有無來統計每個群體在各微衛星位點上的基因頻率和基因型頻率。利用在線軟件iMEC(https://irscope.shinyapps.io/iMEC/)計算期望雜合度(expected heterozygosity,He)、有效等位基因數(effective number of alleles,Ne)和多態信息含量(polymorphic information content,PIC)。因為鱘魚微衛星遺傳標記的多倍體特性,Hardy-Weinberg平衡無法計算[13],故本研究未計算。
2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應用8個微衛星遺傳標記評估三峽庫區天峽鱘業有限公司人工養殖的歐洲鰉(H.huso)、達氏鱘(H.dauricus)和雜交鱘(A.schrencki♂×H.dauricus♀)三個群體的遺傳多態性(表2)。微衛星是一類在基因組中隨機分布的短的(2-5堿基對)串聯重復序列,呈現孟德爾共顯性遺傳。與傳統的遺傳標記等位酶相比,微衛星標記易于區分,遺傳多態性豐富,可應用PCR技術和非致死組織(魚鰭、血液、糞便、羽毛等)進行分析。對于瀕危動物的遺傳分析而言,利用非致死組織則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微衛星遺傳標記已經成為鱘魚種群結構和近交程度評估的有效工具[14~16]。本研究所應用的8個微衛星遺傳標記中,3個微衛星遺傳標記Spl-101、Spl-117和Spl-173在3個人工養殖群體中擴增到彌散的PCR產物,而其余5個微衛星遺傳標記得到高度多態的PCR產物。
在本研究中,歐洲鰉、達氏鱘和雜交鱘3個人工養殖群體的5個多態微衛星標記分別共得到42、38和29個等位基因,平均等位基因分別為8.4、7.6和5.8.總體而言,三個研究鱘魚群體的多態性指標均較高(表2)。三個鱘魚群體歐洲鰉、達氏鱘和雜交鱘的平均期望雜合度分別為0.8280、0.8482和0.7563.三個鱘魚群體平均多態信息含量從低到高依次為雜交鱘0.7099、歐洲鰉0.8056和達氏鱘0.8288.遺傳研究表明,遺傳多態指標PIC接近0.5的群體被認為在遺傳上中度分化[17,18],PIC大于0.6代表著群體具有高度多樣性[19,20]。在本研究中,三個鱘魚群體的平均PIC均高于0.6,所以可以推定三個群體具有豐富的遺傳多態性。三個研究群體之所以具有高度多態性,部分歸因于歐洲鰉、達氏鱘和雜交鱘的染色體的多倍性特征。同時,三峽庫區“公司+漁民”的漁業養殖模式可能是遺傳多樣性的另一個來源。這種漁業養殖模式鼓勵漁民將養殖5年左右的鱘魚出售給公司進行繁育與魚子醬加工。因此,不同來源的鱘魚形成新的群體,提高了群體的遺傳多樣性。本研究使用的魚鰭組織即隨機采集自這些新的群體,這些都極大提高了本研究觀察到的3個人工養殖鱘魚群體的遺傳多態性。

表2 三個人工養殖鱘魚群體的遺傳多態性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