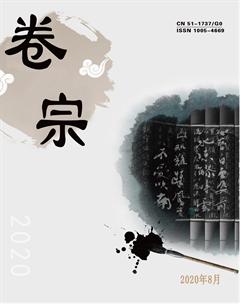巴金文藝思想的繼承性與創(chuàng)新性研究
趙譚兵?黃昕?鄧陽
摘 要:巴金的創(chuàng)作風格統(tǒng)稱為芾甘體,芾甘體反映出巴金一系列的文藝思想,這些文藝思想的形成顯然受到了古今中外文藝思想的影響。本文旨在以中國古代批評史為切入點,以巴金為樞紐關聯(lián)古代文論與當代文學,為巴金文藝思想尋根溯源,同時呼吁當代文壇完成巴金文藝思想再繼承與再創(chuàng)新的歷史使命,為當代文壇注入新的活力。
關鍵詞:芾甘體;巴金的文藝思想;繼承與創(chuàng)新
1 文學武器論與教育說
巴金的文藝功用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文學是戰(zhàn)斗的;二是文學是教育的工具。
“我要拿起我的筆作武器,為他們沖鋒,向著這垂死的社會發(fā)出我的堅決的呼聲‘I accuse”。在巴金的代表作《家》中,他拿起手中的筆作武器,制造了一個又一個悲劇,成功塑造了高覺新等個性鮮明的人物,憤懣地批判著封建大家庭的罪惡、封建禮教對人的摧殘,將利刃直接指向了整個封建制度。巴金的創(chuàng)作中也不乏歌頌光明的作品,如《日》通過寫飛蛾撲火與夸父逐日的故事,熱情地贊美了那種追求光與熱、英勇無畏的獻身精神。巴金緊跟時代的步伐,用筆下真實的文字充當精神的武器,批判現(xiàn)實、歌頌光明。這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國古代詩論的第一篇專論《詩大序》提出的“美刺說”。“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美”即歌頌,“刺”即諷刺。在先秦時期,人們已經(jīng)認識到文學具有批判與歌頌的功能,而在漢代《詩大序》中演變成了“美刺說”,從美與刺兩個角度對文學作品進行評價。東漢劉勰的《文心雕龍》也繼承了儒家“順美匡惡”的思想,在《時序》篇中以為“周南勤而不怨”是“姬文之德盛”的表現(xiàn),“邠風樂而不淫”是“大王之化淳”的象征;在贊美的同時,也有批判的傾向,“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
巴金認為,文學是教育的工具。“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中的“教化”,便指的是文學的教育功能。西晉陸機的《文賦》中說:“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這是在闡明文章的作用很大,原本是許多道理的憑借;將衰敗的文王武王之道繼續(xù)弘揚,文章能夠宣揚教化使之不泯滅。中唐韓愈提出的“文以載道”,提出的“道”便是用來教育人的,只因時代性的不同,巴金文中所載的“道”便不同,同樣是說文學的教育功能。
2 “兩個一致”
“我說我的寫作如同在生活,又說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寫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兩個一致”是巴金文藝思想的靈魂,貫穿其中的核心其實就是一個“真”字,在這一點上巴金繼承了我國自《詩經(jīng)》以來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講求故事的藝術真實與情感的熱情真摯。
這種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是源遠流長的,從先秦時期老子提出的“美言不信”之說;到西漢太史公書寫《史記》的實錄精神;到東漢王充在《論衡》中疾虛妄的思想,反對為文虛假失實,再到中唐詩人白居易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觀點,主張文章與現(xiàn)實緊密結(jié)合;再到北宋文學家王安石提出的“有補于世”、“以適用為本”的文學主張;再到明代李贄提出的“童心說”,他認為文學都必須坦率地表露作者內(nèi)心的真實情感,回歸文學的初心。
2.1 寫作同生活的一致
這里的“一致”指的不是完全的相同,而是相對的“一致”,否則文學會淪為現(xiàn)實的照相機,而失去藝術的活力,這就涉及文學理論中經(jīng)常要提到的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的問題。
巴金曾指出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內(nèi)容“都是可能的,卻不全是實有的”。巴金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會有天馬行空的想象,而是貼近現(xiàn)實的創(chuàng)作,符合人物的性格邏輯,筆下人物塑造能夠達到“什么樣的人物就有什么的行為”的境界,都是按照現(xiàn)實規(guī)律與邏輯來安排的,但不完全是現(xiàn)實生活的照搬。巴金巧妙運用想象的手法,使得筆下的生活雖然游離現(xiàn)實在卻貼近現(xiàn)實,符合美的藝術標準。在陸機的《文賦》中有提到藝術構(gòu)思的想象活動,形容為“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在想象力活躍或靈感來臨時進行藝術構(gòu)思。在劉勰的《文心雕龍·神思》中,所謂“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巴金也的確達到了“神與物游”的藝術境界。
2.2 作家同人的一致
作家同人的一致,簡而言之,探討的是“文如其人”的問題。“文如其人”的命題,最早的完整表述見于蘇軾的《答張文潛書》,“子由之文實勝仆,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這里是說,從字里行間便能窺見一個人的性情與為人,即作文章要吐真言,不可作違心之語。巴金繼承了這種思想,在前期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窺見他的熱情與青春的活力,而后期他陷入了深沉的思索與反思,這與他的經(jīng)歷與心態(tài)密切相關,這是一種人與文相和諧的狀態(tài)。情感的熱烈與不可遏制是巴金其人的突出特點,也是其文的突出特點。在《<病中集>后記》中,巴金說:“我不靠駕馭文字的本領,因為我沒有本領,我靠的是感情,對人對事我都有真誠的感情,我把它們傾注在我的文章里面,讀者們看得出來我在講真話還是撒謊。”西晉陸機的《文賦》中提出所謂“詩緣情而綺靡”的詩學觀念,以巴金的散文詩《日》為例,巴金批判繼承了其思想,注重情感的表達,反對綺麗的文風,追求樸實無華,歌頌了英勇無畏的獻身精神,表達了作者對抗戰(zhàn)勝利的熱切期待之情。這種情感的真實表達與南朝文論家鐘嶸提出的“自然英旨”之說何其相似,不作無病呻吟,完全是“情動于中而形于言”。
3 “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
巴金是偏重文章內(nèi)容的表達,而輕視形式上的技巧,提出了著名的論斷“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但是所謂的“無技巧”并不是真的沒有技巧的運用,只是作者已經(jīng)將技巧融會貫通,在準確表達內(nèi)容的同時已經(jīng)悄然地使用了一些創(chuàng)作技巧,達到了一種寫作上爐火純青的境界。總體上來說,其文達到了內(nèi)容與形式的統(tǒng)一。先秦孔子曾提出,“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文”即文章的藻飾,“質(zhì)”則是指內(nèi)容,強調(diào)文與質(zhì)相互配合,內(nèi)容與形式相互映襯。文章太偏重于形式,就容易形成形式主義文風,如齊梁時期的宮體詩、初唐時期的上官體;而太偏重于內(nèi)容,容易忽略形式美,而顯得文字樸實甚至索然無味,如宋代興盛的哲理詩,這也是巴金作品的局限性所在。
以上對巴金文藝思想進行了梳理,并結(jié)合古代文學思想將兩者有機地聯(lián)系起來,我們發(fā)現(xiàn)巴金文藝思想是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大膽創(chuàng)新的,而處于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更是要繼承和創(chuàng)新前輩的文藝思想,這是我們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參考文獻
[1]巴金著.巴金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2]孔穎達疏.毛詩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劉勰著.文心雕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陸機著/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0.
[6]蘇軾著.蘇軾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楊伯峻注.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
作者簡介
趙譚兵(2000-),男,湖南湘潭人,湖南理工學院漢語言師范專業(yè)18級本科生,《“芾甘體”與寫作實踐研究》(趙譚兵、黃昕、鄧陽)項目主要負責人,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