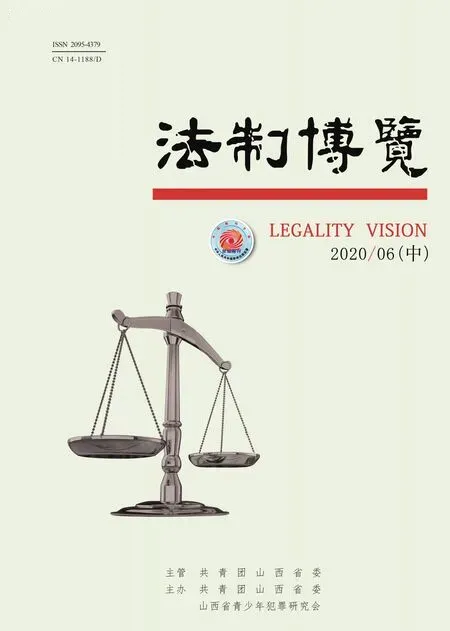《野生動物保護法》修改思考*
——從保護優先原則的視角
王 偉
貴州大學法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再次修訂已經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2020年的立法規劃中。本文擬從保護優先原則的視角出發,對《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改提出建議。
一、保護優先原則的解讀
保護優先原則是2014年修改的《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環保法》)所確立的基本原則。2016年7月《野生動物保護法》在修訂時,第四條正式將“保護優先”作為野生動物保護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但是保護優先的涵義到底是什么,立法并沒有做出明確規定。
學術界展開了對保護優先原則涵義的研究。早期的研究著重從環境保護同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角度來解讀保護優先原則的涵義,認為保護優先原則是對之前“經濟發展優先”的糾正,是指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二者發生不可調和的沖突時,應優先考慮環境保護。《環保法》修改后,學者們嘗試用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等不同的方式對保護優先原則進行解讀,基本認同保護優先實際是指對環境的保護行為應優于對環境的開發利用行為。“保護”從詞義上解釋一般指避免行為對某種對象造成侵害。與資源的開發利用相對比,“保護”其實就是限制對某種資源進行開發利用。根據《環保法》第2條的規定,“野生動物”屬于“環境”的范疇,因此對野生動物實行保護優先,可以解讀為對野生動物實施的保護行為優于對野生動物實施的開發利用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優先”并不是意味絕對禁止“開發利用”。任何行為,甚至是保護行為,都不可避免地會對生態系統的原真性造成干擾,對環境造成影響,所以法律需要建構的底線是對環境的影響何種程度是能夠被容忍、何種程度是可以被接受的。因此,當野生動物資源處于被剝削性開發利用或者開發利用會帶來嚴重的生態問題或公共衛生安全問題的時候,應該絕對禁止對野生動物進行開發利用。其余情況,在維持野生動物資源種群數量質量、維護生態平衡進行有效保護的情形下,可以在法律規定的限度內,合理開發利用野生動物資源。
二、野生動物保護實行保護優先的正當性
(一)野生動物保護實行保護優先是維護國家生態安全的戰略需要
生態安全是指一個國家擁有能夠充分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持續健康穩定的生態系統。生態安全是我國國家總體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為國家經濟安全、社會安全等其他安全要素提供自然基礎,是其他安全要素得以實現的前提條件和基礎保障。野生動物在生態系統中是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野生動物實行保護優先,有利于維護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和統一性。
(二)野生動物保護實行保護優先體現了生態文明建設的價值訴求
黨的十八大提出將生態文明建設全面融入國家的各項建設中,要求在新的歷史時期,把可持續發展提升到綠色發展的高度。黨的十九大進一步強調要推進綠色發展,建設美麗中國。生態文明建設,要求我們正確理解與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優先、和諧共生、永續發展是生態文明的價值訴求。良好的生態環境能為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和保障,所以生態文明強調建設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共生、平衡、互養、和諧、相互制約的關系。而人與動物的關系是人與自然關系典型的體現,保護野生動物,維護生物多樣性,做到人與動物的和諧共生,是對生態文明建設價值訴求的良好體現。
三、《野生動物保護法》貫徹保護優先原則出現的偏差
1988年頒布的《野生動物保護法》立法宗旨中,針對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保護以及對野生動物資源合理利用的問題,法律將二者是放在同等重要地位的。并且從法律規定的內容看,對野生動物利用的規范還占據了相當的篇幅。2016年《野生動物保護法》修定的時候將立法的重心落在“保護”上,以回應中央提出的構建“人與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在立法宗旨中刪除了“利用”的字眼,強調保護野生動物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生物多樣性以及生態平衡,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但是,《野生動物保護法》在具體條文中并未禁止對野生動物以盈利為目的的開發利用,對于“保護優先”的貫徹出現了偏差,致使法律實踐中留下了野生動物進一步被不合理利用的空間。
(一)法律保護對象尚存空白
根據規定,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所保護的對象有以下幾類:第一類是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包括國家和地方兩級的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統稱為珍稀、瀕危的陸生和水生的野生動物;第二類是“三有”動物(即具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第三類是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以下簡稱CITES公約)附錄一和附錄二的野生動物。對第一和第二類野生動物保護我國實行名錄制。法律在保護對象范圍的規定上存在以下幾個問題:首先,將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限定為“珍貴、瀕危”,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立法者是將野生動物看作資源,而不是將野生動物看作是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必要組成部分進行保護的觀念;其次,將具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水生”野生動物和“非重點”保護的一般動物排除在法律保護的范圍之外。對這一部分的目前在法律上屬于空白地位的野生動物,由于不在法律保護之內,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監管,因此會帶來一些風險,例如損害生物多樣性、公共安全及公共健康。
(二)野生動物保護管理體制不健全
我國由縣級以上林業草原、漁業主管部門分別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陸生和水生野生動物的保護工作。這樣分離的管理體制帶來的問題是影響了野生動物保護法律的有效實施。其次,造成現有野生動物保護名錄劃分不明,在管理實踐中存在沖突的問題。例如像龜、鱉等部分兩棲類動物,目前還沒有明確到底是將其按水生野生動物進行管理,還是按陸生野生動物進行管理,這給管理實踐帶來了難題。陸龜類、鱉科類等龜鱉目物種,將其納入了《國家保護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但是同樣是龜鱉目物種的山瑞龜,卻被納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公約附錄水生動物物種核準為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和《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中》的水生野生動物。這樣分別進行管理的管理體制,影響了保護優先原則的實施。
(三)野生動物保護法律制度的設計偏重于“鼓勵”野生動物的“開發利用”
1.野生動物保護名錄制度的欠缺
我國《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自1989年實施以來,僅在2003年進行過一次微調。名錄目前存在所保護的野生動物種類范圍、數量過窄的問題。并且,與相關國際公約的規定存在一定的沖突。按照規定,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公約中,所禁止或限制貿易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名錄,經主管部門核準,可以按照我國的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進行管理。我國加入了CITES公約,該公約附錄一或附錄二中有些動物可能與我國分布的同科同屬的野生動物的保護級別不一致;還有一種情況是在我國國家重點保護動物名錄中沒有與其相對應的同科同屬的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或國家二級重點保護動物,要想對國外引進的這些野生動物(如綠樹莽)進行保護,但沒有可以參照的物種,致使保護這類野生動物的目的無法實現。名錄與相關國家公約未完全一致造成的后果是可能導致在野生動物保護法律實踐中出現偏差,一是影響立案,如公約附錄二的動物,按最高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應我國的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但在中國將其列為“三有”動物(例如畫眉)的話,就可能就達不到刑事立案標準;二是影響量刑,某個物種在中國列入的是“三有動物”,但在公約中是附錄二動物,如果獵捕該種物種,按“三有動物”對待就是非法狩獵罪,而按珍稀瀕危物種看就是非法獵捕珍稀瀕危動物罪,二者的量刑完全不一樣。這樣是不利于野生動物的保護的。
2.狩獵制度的欠缺
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規定,除因“科學研究、種群調控、疫源疫病監測或其他特殊情況外”,禁止獵捕、殺害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即現有的狩獵制度,對于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三有”動物以及其他野生動物,只要有狩獵證,就可以獵捕、捕撈。同時現行的法律沒有規定年度休獵或休漁制度,也沒有劃定禁獵區(禁漁區)、禁獵期(禁漁期)的規定,這對于生態系統平衡的維持是不利的。同時,狩獵證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核發,也降低了取得狩獵證的難度,可能會導致對野生動物的利用加劇,不利于野生動物的保護。
3.人工繁育制度的欠缺
我國《野生動物法》規定,人工繁育可以是為了“物種保護”的公益目的,但是,如果取得許可證,也可以是為了“經濟目的”而進行人工繁育。同時還規定,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經科學論證,就將其納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之后在調整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時將這類物種排除。同時經合法人工繁育(即取得人工繁育許可證)得到的這些動物及其制品實行專用標識制度,目的是保證合法人工繁育得到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可溯源性”,以起到打擊遏制非法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交易、利用活動的作用。但人工繁育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專用標識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是對野生動物商業利用的一種推動和促進,因為它表露出對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商業利益肯定和引導的一種價值追求,偏離了保護優先原則對野生動物進行保護的要求。
我國目前人工繁育野生動物,很多時候是出于商業目的。按照《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規定,對于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要實行強制檢疫。但是目前我國沒有專門的針對野生動物的檢疫標準。盡管《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了經營使用野生動物要有檢疫措施,但是目前我國動物檢疫標準是農業部門制定的,主要是針對的是家養動物,對于大多數野生動物而言,由于缺乏對其所攜帶的病毒以及所傳播疾病的研究,同時野生動物種類太多,不可能逐一分門類制定檢疫標準,因此野生動物檢疫時只能按照其最接近的家養動物檢疫,所以檢疫的嚴謹性和準確性就打了折扣。同時,有一些野生動物(例如土撥鼠)是沒有可以參照的檢疫標準的。所以,在檢疫缺失的狀況下,很難判斷并保證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是否安全。
同時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商業利用過程中,還會帶來一些其他問題,如利用野生動物的皮毛產業所造成的環境污染,以及商業利用時野生動物遭受的痛苦等。此外,部分商業性馴養繁殖野生動物(如牛蛙)存在外來入侵物種問題,威脅生物多樣性,極易造成生態安全問題。因此,人工繁育制度存在的欠缺,使保護優先原則在野生動物保護中未起到應有的作用。
4.放生制度的欠缺
《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了野生動物放生制度,要求選擇適合放生的當地物種,避免對生態系統造成的危害。但是沒有規定主管部門對放生行為的管理引導,現實中經常出現一些百姓不當的放生行為給生態系統造成損害的事例。
(四)與相關法律不銜接
《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條規定“其他水生野生動物的保護適用《漁業法》的規定”,但是我國《漁業法》甚至《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并沒有規定“其他水生野生動物”的分類分級保護名錄,沒有對國家重點水生保護野生動物名錄進行銜接、補充或完善。《動物防疫法》僅將動物的概念界定為家畜家禽和人工飼養、非法捕獲的其他動物,將非法獵捕的野生動物完全排除在動物檢疫制度之外,助長了對野生動物的非法獵捕的風氣,并且還帶來嚴重的公共衛生安全隱患。《傳染病防治法》只規定了人畜共患傳染病的防治,對于疫源性動物的禁食、禁售問題沒有規定。我國《刑法》中堵截針對野生動物的犯罪行為實施的鏈條出現脫節。食用、虐待、加工、持有野生動物等行為沒有犯罪化。《野生動物保護法》與相關法律的不協調,影響了保護優先原則的實施,不利于野生動物的保護。
四、堅持保護優先原則:《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完善建議
對于《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改,應堅持保護優先原則,改變以往過于重視野生動物資源開發利用,而輕視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保護的傳統,制度的設計上一定要與保護優先原則相呼應。
(一)擴大法律保護的范圍
野生動物是生態系統中不能缺失、不可替代的環節,任何一種野生動物在生態系統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所以為貫徹保護優先原則,維護生態平衡和國家生態安全,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擴大《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保護對象勢在必行。除去一些經過科學論證,明顯對人類有害可以不用保護的野生動物(最典型的就是老鼠)外,其他一切野生動物都應該納入立法所保護的范圍來,才能維護整個野生動物物種之間的生物鏈的完整性,維護生態安全。2020年2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6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全面禁止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在現有《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基礎上上,將禁食的野生動物的范圍擴大,該《決定》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立法權的一種具體形式,其與法律具有同等的效力,《決定》的出臺為法律上合理界定“野生動物”的概念并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擴大法律的保護對象提供了法律基礎。
(二)完善野生動物保護管理體制
建議將野生動物保護的管理職能統一劃歸自然資源部,與此同時,在自然資源部中成立野生動物保護局,主管全國的野生動物保護工作。這樣做的優點是既提高了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的法律地位,增加其權威性,又可以充分利用自然資源部現有的管理和執法力量,有利于提高野生動物保護的管理和執法水平。下一步可以適當拓展其野生動物保護管理和執法的權限,進一步加強對野生動物的保護力度。
(三)野生動物保護法律制度的設計堅持保護優先原則,堅持野生動物公益性利用限制其商業性利用
1.野生動物保護名錄制度的完善
目前,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主要有三個:即《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家公約禁止或限制貿易的野生動物或者其制品名錄》。現實的情況是,《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保護種類范圍、數量過窄,沒有及時更新和拓展,但《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種類數量卻有擴張趨勢。所以有必要將兩個部門分別制定的名錄進行整合,適當將名錄中一些二級保護野生動物的級別適時提升到一級,例如可以將在我國是屬于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穿山甲的級別提升到一級,因為其在CITES公約中是附錄一的物種。建議將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公約禁止或限制貿易的野生動物或其制品名錄以及“三有”動物合并為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和地方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并逐步減少允許能夠人工繁育的動物種類,限制對野生動物的商業性利用,只允許公益性利用,避免對野生動物的不當利用。修訂名錄時應充分考慮分類命名變化所帶來的社會、生態與健康等方面的影響。
2.狩獵制度的完善
狩獵制度應該涵蓋水生野生動物。其狩獵許可證、捕撈許可證以及人工繁育物種專用標示等發放應該由主管部門進行統一的依法公開。增加對年度休獵(休漁)的規定,以利于野生動物的休養生息。
3.人工繁育制度的完善
人工繁育養殖如果監管不到位,容易引發問題,所以應該將養殖馴養的條件、標準、程序等規定的更為詳細,更具有操作性。尤其要強調必須采取防疫、防病措施,構建從獵捕或繁育到運輸到交易直至利用的全鏈條的野生動物保護體系。
4.完善野生動物放生制度,應規定經野生動物主管部門科學論證、備案登記后,才可以將野生動物放生至野外環境。
(四)加強法律之間的協同規制
應修改完善《野生動物保護法》《漁業法》《動物防疫法》《畜牧法》《食品安全法》《刑法》等法律,加強法律的協同規制,確保無縫對接,確保保護野生動物法律的體系化、綜合化。
五、結語
野生動物的非經濟價值(如生態價值、科學價值、美學價值等)的重要性更甚于經濟價值。保護野生動物、善待野生動物,維護生物多樣性,就是保護人類自己。只有做到人與自然(包括野生動物)的和諧共生,才能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適時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堅守保護優先原則,有利于回應人民群眾關注的重大事項,為維護國家公共衛生安全和生態安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