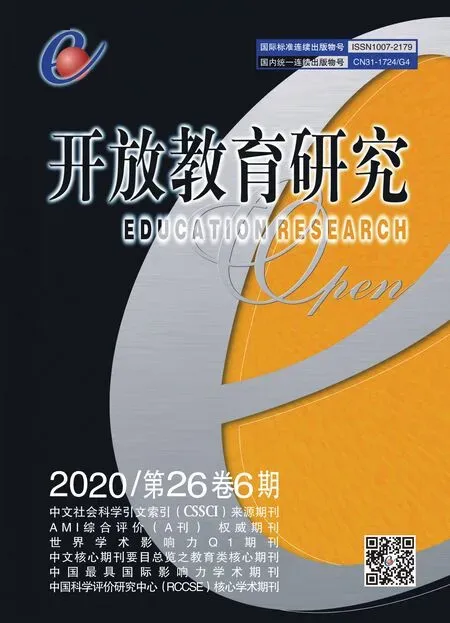利用屏播反饋提高個性化學習效率
方柏林
(艾比林基督大學,德克薩斯州,美國)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加速了網課和混合教學方法的普及。教師越來越熟悉如何利用屏播軟件開展教學,屏播技術也變得容易獲得,但教師們在使用屏播方法提供反饋上,行動是遲緩的,甚至很多老師不知道可以用這種方式批改作業,提供反饋。
本文將探討學習反饋的重要性,傳統文字反饋存在的問題,屏播反饋的優勢,以及相應的使用建議。
一、何為屏播反饋
屏播是繼播客和視頻播客之后涌現的一種信息傳遞方式。播客多為音頻,視頻播客是真人出鏡的講述,也稱頭像講述。而屏播則側重于讓受眾看到自己分享的屏幕內容,有時候這也包括講述者的頭像在視頻的某個位置,如左下角或者右下角。講述者也可不出鏡,僅有屏幕演示和講述聲音。屏播可以讓教師和學生同步交流。Zoom、騰訊視頻、CCTalk、釘釘等軟件視頻,均有視屏分享功能。當教師分享視屏時,就是在進行屏播。屏播也可以是異步的,亦即事先錄制,通過特定平臺發布,學生選擇時間收看。錄制屏播視頻的軟件包括Camtasia、 Screencast-o-matic、 Adobe Spark Video。部分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也自帶錄屏功能。
屏播早期用于軟件公司對其產品使用方法的講解。后來,隨著可汗學院(Khan Academy)等平臺的普及,老師們發現,利用教室黑板的講解,可變成在屏幕上講解的方式,向自己的班級或者更大范圍的受眾講課。于是,越來越多老師用這種屏播方式授課,尤其是同步授課。新冠疫情期間的網課,進一步普及了這種教學方式的使用。本文所說的屏播反饋,指利用屏播方式, 給學生提供作業反饋。這種教學方式,有時候被稱為veedback, 亦即視頻反饋(Sabbaghan, 2017)。視頻反饋中,有很多是基于屏播的反饋。
二、為何需要改進反饋
疫情期間的網課教學,暴露出網課中存在的一大常見問題,即學習韌性。祝智庭和彭紅超(2020)指出,網課嘗試中,由于數字化的不足,學習公平、學習效果受到影響。為提高韌性,作者提出建設技術賦能的教育生態系統建設,其中包括線下和線上深度融合的OMO教育生態。現在的教學內容越來越容易獲得,改進教學反饋的工作相對而言存在滯后。中國的課堂教學中,需要老師提供反饋的學生眾多,個體化反饋往往難以實現。
而在國際上,有效的反饋也是問題。即便在疫情前,隨著學生人數的減少和學費的上漲,許多高校已面臨生存危機,美國多所學校在疫情期間關閉。與此同時,教學和運營成本在增加,學生對教學質量和服務的需求在增長,學校面臨改進服務的壓力,以保持對潛在學生的吸引力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學校通常會裁減教職員工,聘用兼職教師替代全職教師,或增加現有教師的工作負荷。這些舉措均增加了教師的職業壓力,也損害了學習質量(Berg & Seeber,2016)。高校擴招中,教室、辦公室空間在減少,即使在面授大學中,面對面反饋的機會也變得越來越奇貨可居(Borup et al.,2015)。兼職教授有時在學校里沒有固定的辦公室,這也限制了他們,使得他們無法像過去那樣提供經常而高效率的反饋(Planar & Moya,2016)。很多原因,都對改進教師的反饋方式提出了要求。
學校在尋求改變時,通常將技術視為首選。越來越多的學校在開設混合或在線課程,利用課程管理軟件和其他技術平臺超越地理障礙,擴大學生群體,這么做可降低成本,增加收入。隨著大學在線課程的增多,質量控制的意識也在上升。對六套在線課程質量標準的調查表明,所有這些標準都有個共同主題:要使在線課程成功,必須有意義的學生與老師互動(Baldwinet al.,2018)。
缺乏這種互動,會損害在線課程的信譽和效果。現在老師可以輕松地在線發布課程內容,但教師與個別學生之間往往缺乏豐富、及時、個性化的交互。這個問題已經成為瓶頸。西部州長大學的遭遇,最能說明人們對在線課程缺乏互動的擔憂:2017年,美國教育部監察長辦公室(OIG)發布報告,要求西部州長大學退還超過7.13億美元的聯邦財政援助。其原因,是該辦公室認為課程缺乏有意義的互動(OIG,2017)。該報告聲稱(OIG,2017:2-3):
我們抽查了該校三個最大的在線項目的102門課程,審查了課程設計材料,查看每門課程的設計是否保障學生與教師之間定期、實質性的互動,這是遠程教育課程的重要指標。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在102門課程中,至少有69門課程的設計,不包括學生和老師舉辦定期的、實質性的互動,因此,這些課程不符合遠程教育的法律定義。這69門課程符合第九條函授課程的定義(34 CFR§600.2)。
傳統函授課程的特點,就是通過師生之間的書面交流開展教學活動。其關鍵的短板,是缺少面對面課程中常有的豐富互動。無論是在線課程,還是其他傳統課程,反饋均是學習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奇克云和甘森(Chickering & Gamson, 1987)的本科教育七原則之一,即是向學生提供及時反饋。加涅(Gagné, 1977)將提供反饋作為組成一堂課的九項教學活動之一。斯克利文(Scriven, 1967)提倡在教學中使用形成性評估,形成性測評包括提供反饋。有效的反饋可以鞏固學生對學習內容的吸收,糾正理解上的偏差,激勵學生改進現有作業和未來的作業。相較而言,終結性測評對學習的改進效果有限:它是對學生的學習結果作出論斷,論斷到來時通常為時已晚,學生對失誤已回天無力。美國一項全國學生參與度調查顯示(NSSE,2018),與其他教學實踐相比,學生對教師反饋及其及時性的滿意度最低。
好的反饋應該內容實在、發送及時,且會經常發布給學生(Hartshorn,2008)。薩德勒(Sadler,2010)提出,反饋能否起作用,是師生雙方的責任:教師的責任,在于反饋內容具體,溝通有效;學生的責任,是要掌握相關知識和技能,符合任務需求,了解老師的質量標準,掌握相關隱性知識,能夠充分利用老師的反饋意見。吉布斯和辛普森(Gibbs & Simpson,2004,見McCarthy,2015:154)概述了高質量反饋的六個品質,包括:有足夠的頻率和細節、著眼于學生的表現而不是針對學生本人、及時、符合測評的目標、考慮學生學習觀念,以及這些反饋“得到了考慮,促發了行動”。
三、傳統文字反饋存在的問題
傳統上,老師常以文字批注的形式給出反饋,包括在字里行間或者頁邊添加手寫批注,或電子文檔修改模式下的修改建議和評論。這些純文字反饋存在諸多問題。對很多學生,尤其是外語學習者來說,老師手書的評注,學生可能難以辨識(Dunn,2015; Morris & Chikwa,2016; Sprague,2016)。學生還抱怨老師的反饋不充分、不清楚或不及時(Cranny,2016; Cann,2014)。另一個常見問題,是溝通缺乏清晰度(Dunn,2015; Morris & Chikwa,2016; Sadler,2010)。教師有時還給出涉及圖形、圖表或計算機界面的復雜解釋與演示,或需要在較長的作業上指出相關問題,而不只是指出幾處具體問題。另外,網絡課程中,文字使用過多,文字反饋也會增加學生的認知負擔(Grigoryan,2017; Kay & Edwards,2012)。僅使用文字評論,也可能導致學生只考慮老師點出來的具體問題,而不能宏觀思考其他需要改進的問題(Bissell,2017)。如果老師以談話的方式和學生交流,則會鼓勵學生更深入地思考作業的問題,激勵他們負責完成改正。僅使用文字反饋,還存在情感方面的問題。由于缺乏視覺提示和言語修飾,一些教師批語,可能顯得過度尖刻、挖苦,超出老師的本意,挫傷學生學習積極性(Dunn,2015)。
有時候學生看到反饋后無動于衷,不作修改,不作改正,也讓老師沮喪甚至憤怒(Bissell,2017; Cann,2014)。老師的反饋如果和考試或作業的成績同時出現,學生可能只看成績,忽略老師付出了更多心血的評注。這種結果,既浪費了教師的精力,也耽擱了學生的改正,繼而傷害師生之間的關系(Bissell,2017; Cann,2014)。
純文字的反饋更耗時,增加教師的工作量,甚至有損教師健康(van Haren,2017;Cann,2014)。教育技術越來越多地被用來收集學生作業,老師也用他們來批改。這意味著教師除上課外,批改作業時需長時間坐在電腦前碼字,這會增加教師的職業倦怠。根據切爾尼斯(Cherniss, 1980,轉引自Fong, 1990:102 )的說法,當一個人在工作需求和擁有的資源之間失去平衡時,會導致角色過載(role overload),繼而導致職業倦怠、沮喪或憂郁。馮(Fong,1990:104)發現,教職員工每周平均工作花費59小時,導致數量性超負荷。教師發現學生不看自己的評注,挫折感會增加。
四、文字反饋的替代方法
文字反饋的替代方法包括使用評估量規(rubrics),將總體評估分解為詳細的標準,比如“新手” “粗通” “精通”這樣的尺度。評估量規還可針對單個標準,以0-5分的滑動標度對作業質量加以區分(Brookhart,2013)。使用評估量規,能夠將原本龐雜的評注,合并成有意義的類別,簡化提供反饋的過程。教師在評估量規的制定上要花時間,但這種工作,最終會減少后期反饋的工作量。美中不足的是,評估量規中的評注,往往難以和作業中的特定問題關聯。對于大篇幅的作業,如碩士、博士論文,量規難以指向具體問題,作用有限。
文字反饋其他替代方法還包括音頻。音頻可單獨存在,或作為文字反饋的補充。許多應用程序提供了音頻反饋的功能。例如,Turnitin是款流行的查重工具,也是批改作業的工具,其批改功能就包括音頻反饋。還有老師使用手機或者平板電腦的Notability軟件,批改學生作業。利用Notability批改作業,可以添加注釋,也可以生成音頻反饋。課程管理軟件,如Canvas,包括音頻評論功能。學生對純音頻的反饋接受度有限:與文字或視頻相比,音頻反饋缺乏預覽功能,要識別特定問題困難得多(Morris & Chikwa,2016)。
五、屏播反饋的好處
屏播一詞可以追溯到2004年,當時尤代爾征詢讀者意見,了解用什么詞匯描述談話那樣的語言,講述如何與軟件互動。當時,Camtasia公司已有一款名為Camtasia Studio的產品,可以幫助用戶制作屏幕錄像。在讀者提出各種各樣的名稱后,尤代爾決定將其稱為屏播(screencast)方法,該術語現已廣泛使用(Udell,2004)。
2004年后,涌現出各種各樣的屏播技術,包括用于臺式機和筆記本電腦的Screencast-O-Matic、Jing和Camtasia,還有移動設備商安裝的應用程序Explain Everything、 Showme等。還有多個用于同步屏播的應用程序,如Skype、Google Hangouts、Canvas Conference和Zoom,中國的相關產品包括騰訊會議、CCTalk、釘釘等。它們都有屏幕共享功能。過去,用戶需要依靠DVI圖像采集卡和專用轉換器等硬件設備才能錄屏。現在,用戶可以使用設備已有的音頻和視頻功能,在同一設備上錄制屏播視頻,無需另外增加硬件設備。相關軟件也變得易于使用。例如,蘋果電腦OS Mojave或更高版本的用戶,只要同時按Command 、Shift、 5三鍵,即可錄制屏播視頻。在iPad上,用戶也可以啟用系統自帶的錄屏功能。從技術上講,制作屏播視屏已經輕而易舉。
(一)情感利益
基于屏播的反饋對學習者具有情感優勢,包括語調更自然,更有利于師生融洽關系,也能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
1)反饋語氣。屏播視頻包含可以緩和批評的語氣。比塞爾(Bissell,2017)完成了一項針對使用Screencast-O-Matic開展反饋的定性研究后發現,學生更喜歡這種反饋,因為它更個人化。老師在給出正反面反饋時,語氣更趨委婉。拉米(Lamey, 2015)對兩個哲學班開展了定性調查,了解學生對視頻反饋的態度。學生對這種反饋絕大多數態度積極,認為這種屏播反饋更易理解,語氣更緩和,手勢等視覺輔助更有效。當然,這種正面的接受也需要時間:學生們一開始收到這樣的反饋,不大熟悉這種模式,略有不適,但隨著教師使用的增加,這種不適隨之消退。卡瓦萊瑞等人(Cavaleri,2019)研究了1040條評論,并得出結論,視聽反饋提供了對話,和個性化、多模式的互動,有利于幫助英語初學者多渠道了解老師的反饋,這樣更有可能利用反饋改正作業。
2)師生關系。提供豐富、及時和個性化的反饋還可以提高對學生的個性化關注,繼而改進教師的社交形象(Darby & Lang,2019)。多項研究發現,學生更喜歡視頻反饋,這種反饋可改善師生之間的融洽關系(Bissell,2017; Borup et al.,2015; Henderson & Phillips,2015; Marshall et al.,2020;Sprague, 2016;Turner & West,2013)。屏播視頻讓人感到反饋更個性化,更有因材施教的感覺(Bissell,2017)。使用屏播反饋更能傳達老師對學生的支持。學生發現視頻反饋更具體,更有支持性,更容易理解,也更有面對面談話的感覺。它可以提高學生的自信心(Bissell,2017),減輕焦慮感(Sprague,2016),改善師生融洽關系(Sprague,2016),并重新激發老師的熱情(Henderson & Phillips,2015)。
改善師生之間的融洽關系很重要。安布羅斯等人(Ambrose et al.,2020:157)認為,積極的學習氛圍會改善學生學習效果,而師生關系是課程氣氛的重要因素:“氣氛是由一系列相互作用因素決定的,這些因素包括師生互動、教師設定的課程基調、臉譜化印象或象征...以及課程內容和材料所代表的不同觀點”。屏播視頻讓課堂氣氛和師生互動沒有那么正式,從而為課堂營造了良好的環境。
3)學生動力。融洽的師生關系也能強化學習激勵。心理學家戴維·斯科特·耶格爾做過實驗,將44篇七年級學生論文分為兩組。對一個小組(對照組),老師給出反饋:“我給你這些評語,是為了給你的文章適當反饋。”而對實驗小組,老師留言稱:“我給你們這些評論,是因為我的期望很高,而且我知道你們能實現”(Heath & Heath, 2017:122)。最后的結果顯示,對照組中40%的人選擇修改論文,而實驗組中80%的人選擇修改論文。希思和希思(Heath & Heath, 2017:123)對這種現象評論道:
第二種留言,重新設計了學生處理批評的方式,也因而更有效。當他們拿回作業時,看到上面的糾正和建議時,他們的自然反應,可能是抵觸,甚至是不信任,覺得老師從不喜歡我。但是,更睿智的留言,則是發出不同的信息。它在說:我知道,只肯用功做事,一定能有出色的結果。批改你的文章,不是對你個人的論斷,而是鼓勵你提升自己。
綜上所述,要讓學生利用反饋改進學習,他們必須首先在乎這些建議,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些建議的提供方式和提供者。通過使用屏播反饋,教師可以與學生進行個人的、非正式和個性化的對話,改善師生關系,最終激勵學生改進功課。
(二)屏播反饋的認知優勢
除情感上的優勢外,屏播反饋也為學習者帶來許多認知上的好處。這包括更合理的認知負荷,可視化學習,以及反饋可能更及時、具體、個人化。
1)合理的認知負荷。學生以書面形式完成作業,導致學生和老師在信息處理上,文字讀寫負擔過重。屏播視頻提供了更多元化的信息傳遞方法。多項研究認識到,屏播能減輕負面的認知負荷(Grigoryan,2017)。凱和愛德華茲(Kay & Edwards,2012)對加拿大72名6-8年級的初中男孩和64名女孩調查后發現,視頻播客可以減輕初中學生的認知負擔。研究人員發現,學生欣賞分步解決數學問題的演示,覺得這樣更清晰。
認知負擔減少可歸因于邁耶爾(Mayer,2009:267-268)提出的多媒體使用原則,包括時間連續性原則(同時而不是連續顯示單詞和圖片,人們會學得更好)、模態原則(人們從圖形和旁白中學習的內容要比從動畫和屏幕文字中學習得更好)、多媒體原理(人們從單詞和圖片中學到的知識要比僅從單詞中學到的更好)、個性化原則(當單詞采用對話風格而不是正式風格時,人們會學習得更好)。
屏播通過在視覺、語言和聽覺信息之間同時分配反饋來體現上述三個原則的前三個,并且它一次也針對單個學生(個性化原則)。相對而言,如果教師與學生交流僅使用文字,則可能會使學生處理口頭信息的思維能力超負荷,從而導致認知超負荷,同時又無法充分利用學生的視覺和聽覺。屏播視頻可平衡學習者的感官和信息處理能力。
2)可視化學習。根據海蒂(Hattie, 2015)的可視化學習概念,當老師清楚表述自己的期望,學生也表述了如何理解所學知識時,學習才能最好地完成。他的可視化學習的概念并沒有涉及屏播,但屏播在視覺上易于演示,更容易促進可視化學習。屏播是一種向學生傳達教師期望的好方法。學生同樣也可錄制屏播視頻,讓老師了解他們面臨的問題。
這種可視化還表現在視頻反饋的具體明確上。凱林拜克等(Killingback et al.,2019)指出,視覺提示提供的非語言交流有助于學生理解。亨德森和菲利普斯(Henderson & Phillips,2015)的研究顯示,學生對視頻反饋幾乎都給予好評。這種好評是因視頻反饋清晰而具體。學生作業需要的改正,往往并非需要推倒重來。一般情況下,老師需要指出薄弱環節讓學生去加強,或指出特定錯誤讓其改正。屏播反饋可以讓老師點出屏幕上展示出來的具體內容。這種邊指點邊講述的反饋,對視覺藝術、音樂、戲劇、護理、職業治療和運動訓練等諸多專業至關重要。教師可以使用光標或者觸摸屏的觸摸,突顯需改進的薄弱區域和需要贊美的區域。教師在解數理化題目時,屏播反饋也是一種大聲思考的交流方式,讓學生可以直接了解教師的解題思路(Kay & Edwards,2012)。
3)反饋個性化。屏播視頻給出的特定反饋,比課堂經常會有的那種泛泛而談的點評,更能滿足個體的學習需求。首先,老師不一定針對每個學生都提供屏播反饋,而是針對具體學生給出針對性反饋,更可能因材施教。亨德森和菲利普斯(Henderson & Phillips,2015)強調,視頻反饋可能更針對學生的個體需求。屏播視頻作為一種視頻,將控制權交給學生,學習在看視頻時,可以跳過已掌握的部分,花更多時間查看他們感到特別困惑的內容。
4)多重感官。屏播視頻對語言學習者尤其有益。屏播中有屏幕演示、語音講解,甚至老師的頭像,這包括老師的表情、手勢等體態語,讓學習者可以同時得到視覺、文字和聽覺等多重感官體驗。阿里·巴特(Ali Batel,2014;Sprague,2016)開展了一項定量實驗研究,比較學習語言的學生群體。實驗組觀看十分鐘的電影,對照組閱讀相關的圖書章節,然后輪換。研究結果顯示,電影組的測試成績優于文字組。這表明多感官的電影,由于增加了視覺輔助材料,可以提高學生的理解力和學習積極性。這種多重感官刺激,還可幫助部分有特定殘障或學習障礙的學生,包括有閱讀障礙的學習者(Bissell,2017; Jones et al.,2012)。
(三)屏播反饋對老師的優勢。
對老師來說,屏播反饋也有諸多優勢,包括讓反饋過程更及時,更節省時間,這些都可以提高其工作滿意度。海蘭德(Hyland, 2013)在香港一所研究型大學使用訪談開展定性研究。研究人員從四個系選擇了24名學生,了解學生對老師反饋的看法。研究發現,高質量反饋的特點是及時、個性化、重點突出,并讓學生期望和教師保持一致。低質量的反饋則是敷衍、拖延且與個人需求無關。過去的老師反饋,往往是要等到和學生見面。由于時間拖延,見面后老師或許已忘記要反饋的內容,學生等候時間過長,也不能及時將老師反饋和自己完成作業時的考慮相關聯。利用屏播反饋,老師看完作業后可立刻開始評論,及時發送給學生。在諸多課程管理軟件中,教師可以在發布成績前發布評論,以免學生拿到成績不看老師批注和評語。
斯派克特(Spector, 2005)的研究發現,在線教學中大多數交流和協作都通過文字完成。與簡單地與學生交談相比,打字更耗時,因此網課對老師的時間要求更高。這種局限性也挫傷了老師上網課的積極性。網課更耗時間,不在于課程講授,因為教學課件錄制后可多次使用。耗時也不在于測評,機考可自動批改,更加節省時間。耗時主要體現在和學生的互動和個體化反饋上。范·德·沃德和寶格(Van de Vord & Pogue,2012)完成了一項研究,要求面授課和網課老師分別對每位學生所花時間做一日志記錄。研究發現,一般而言,面授教學花費時間更多,但在特定領域,尤其是在提供反饋、分配成績和解決技術問題方面,網課教師花費時間更多。例如,在面授課程上,老師每周批改每位學生作業所花時間是22.49分鐘,而在線教師則需47.84分鐘。記錄成績平均花費面授教師2.03分鐘,而網課教師則為4.46分鐘。解決技術問題的時間,面授和在線老師所花時間分別是0.11分鐘和0.86分鐘。
教師經常提到屏播反饋的一個好處是節省作業批改時間,最多可節省一半(Woodard,2016年)。亨德森和菲利普斯(Henderson & Phillips, 2015)聲稱,一個人五分鐘內可產生約625個單詞。也有研究者發現,一分鐘的音頻等于六分鐘的書面反饋(Lunt & Curran,2009,引用于Cann,2014:2)。同樣,坎寧安(Cunningham, 2019)提到,使用屏播反饋與使用文字相比,她平均可以節省33%的時間。這樣的節省時間不是一開始就可以實現的。有的老師一開始不熟悉屏播軟件,或是過于追求完美,不斷重錄,會耽誤時間。調整了期望值,并經多次操練使用順手之后,才開始節省改作業時間,減輕工作壓力和職業倦怠。從節省時間的角度考慮,如果更廣泛地使用屏播反饋,可消除網課建設的一個重大障礙,減少教師在線時間,改進師生互動質量,這都會激勵更多老師從事網課或者混合課程的教學。
六、使用屏播反饋的最佳做法
讀者應該注意,上述的屏播反饋優點,如節省時間和多重感官,在某些情況下也會成為劣勢。這里我們根據相關文獻研究和工作經驗,提供一些典范做法,以便能夠充分發揮屏播反饋的優勢。
(一)專注于對話,而不是信息傳遞
馬奧尼等(Mahoney et al.,2019)綜合了37項研究,發現視頻反饋在學生和老師中都具有很高的接受度,但更適合對話而非信息傳遞。如果教師希望傳遞諸如文獻引用格式之類的信息,在文字中插入資源的鏈接更容易。如果教師采用與學生交談給出反饋,效果往往更好。
(二)關注布局,而不是細節
格里戈良(Grigoryan,2017)使用混合、準實驗設計方法,對一所營利性大學一年級學生的作文開展研究的結果表明,屏播反饋更適合針對目的、聽眾這種寫作布局的宏觀部分,對語法、標點等具體環節,用書面反饋更容易。格里戈良使用寫作過程理論,聲稱當學生增加練習并在修訂中納入反饋時,寫作會得到改善。
(三)提高學生的自主性
我們建議教師“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也就是說,不把修改的方法直接給學生,而是用視頻指導學生如何思考改進的辦法。視頻具有暫停、倒退和快進等功能,學生可自主控制。在解釋問題的視頻中,學生可以反復查看,以加深理解(Bissell,2017),或是暫停視頻,自己去修改作業(Cranny,2016)。教師只需在屏播視頻中解釋、展示作業中的布局、主題或結構性問題,讓學生采納建議,自行去修改,而不是手把手幫他們解決特定問題(Hartshorn,2008) 。阿爾維拉(Alvira,2016)的研究表明,屏播視頻的使用,讓老師更多地扮演腳手架角色,這增加了學生的自主權和整體寫作效果。作者鼓勵老師,尤其是外語老師,使用口頭反饋改善寫作。
(四)促進“前饋”
通常所說的“反饋”,英文為feedback,側重于“返回”(back)已有作業去修改。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應該更多地強調“前饋”(feed forward) ,也就是不滿足于改進已經提交的作業,而是利用已有作業的反饋,促進未來作業的改進。著眼于未來的“反饋”,要求老師在給出反饋時,要有前瞻性和形成性(van Haren,2017;Brereton & Dunne,2016; Cranny,2016; Henderson & Phillips,2015; Jones et al.,2012; Planar & Moya,2016)。前饋很有用,但不要將屏播視等同于前饋。能否出現前饋的效果,關鍵是老師的反饋要及時(Brereton & Dunne,2016; Planar & Moya,2016),視頻反饋中還要有明確的指導或結構,幫助學生在未來作業中改進。
(五)關注工具包,而不是最佳工具
屏播反饋并非解決教學反饋問題的靈丹妙藥,有時甚至會限制教師。在某些情況下,僅使用文字效果更好。視頻反饋對語法和錯別字等寫作反饋,效果不及文字反饋(Henderson & Phillips, 2015)。 一些技術手段,如修訂模式、Google Docs的批注功能,以及Canvas和Turnitin的批注工具,均可放大文字反饋效果。這樣的工具可以很容易地糾正局部錯誤,如語法錯誤、文獻錯誤,以及其他不需要詳盡解釋的低層次問題。Turnitin甚至能讓老師建立常用評語數據庫,使批改過程既有效又容易。而使用屏播或其他視頻、音頻,重復使用同樣的評語則困難得多。一些教授使用文字批注進行評論,并使用屏播視頻進行難點要點解釋,這也是很好的選擇。
屏播反饋這種新方法不應替代其他反饋方法,包括基于文字的反饋。教師需要考慮的,不是如何用一種工具替代其他工具,而是著力于擴展自己的工具包,靈活選擇工具或工具組合。這一觀點來自多項研究,這些研究比較了基于文字的反饋和使用屏播的反饋。
幾項研究比較了學生對文字和屏播視頻反饋的感知差異,沒有發現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Boraup et al.,2015; Dunn,2015)。有時文字更高效:文字更易訪問,更高效,容易復制,容易編輯(Boraup et al.,2015)。鄧恩(Dunn, 2015)的研究發現,學生認為兩種反饋方法都好,但視頻反饋更詳盡,更有個性。麥卡錫((McCarthy, 2015)比較了同一課程中使用文字、音頻和視頻三種類型的總結性評估,并在線調查了學生對這些反饋方法的評估。研究發現,每種方法在成本、時間和負荷上都有自己的優勢,也都有局限性。例如,視頻反饋具有以下局限:文件大,制作工作量大,分發速度慢且需要技術工具來制作。研究最終得出結論稱:高等教育不應針對所有情況采用標準化的反饋模型。
總之,使用單一方法(例如,純文字或者純視頻),都有局限性。我們主張教師應開發他們的反饋方法工具包,包括文字、音頻和屏播。工具齊全了,教師就可以根據情況,因地制宜地選擇選擇適當的工具,例如,可在頁面上添加劃線、評注、鏈接,然后使用屏播,討論更大的問題。
(六)避免完美主義視頻
節省時間是屏播反饋的一大優勢(Cunningham,2019; Henderson & Phillips,2015; Sprague,2016; Woodard,2016),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也有老師說錄制視頻太耗時間(Borupet al.,2015)。本文采用屏播視頻的寬泛定義,包括人像視頻。對自我形象的敏感,可能會導致老師花費過多時間制作精美視頻,哪怕人像只出現在屏播視頻的一角。有的老師帶著大眾傳媒的標準要求自己的教學視頻,這是不必要也不切實際的。
誠然,具有簡單視頻編輯的能力,對于嫻熟掌握屏播反饋至關重要。這需要對老師提供合適的培訓,也需要不斷增強他們的自信心。老師錄制視頻自我形象固然重要,需衣冠整潔,環境沒有太多干擾,不影響收聽收看的質量,但教學視頻不等同于電影電視。有些教授可能對錄像有顧慮,在錄制中不斷調試背景,換“皮膚”,加“美顏”等,結果錄制一遍又一遍,直到對視頻感到滿意。后期有時候還剪輯掉中間打頓、說話猶豫的地方。這樣一來,利用視頻節約時間的優勢變得蕩然無存。
學生不一定希望教授一張口就像電視主持人一樣,語音語調和講述方式完美無瑕。讓學生了解老師的思維過程,包括他們在思維過程中的猶豫,對學習更為重要。專家可以蓄意通過大聲思考的方法,讓旁觀的學習者獲得技能。學習者也可使用此方法,暴露思路的不足。大聲思考的方法,廣泛適用于駕駛、藝術欣賞和網絡搜索的研究(Anders, 2018; Bauer & Schwan,2018;Gerjets et al.,2011; Kircher & Ahlstrom,2018)。屏播視頻的制作通常沒有腳本,它是展現專家(教師)思考過程的絕佳工具。
(七)盡量減少干擾
老師可通過多種方式給出反饋,如添加評注、使用評估量規,再加屏播反饋。當多種方法并存時,學生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另一個分散注意力的因素來自視頻的存儲和分發方式。如果教師在云端,如YouTube、Vimeo、優酷、B站發布視頻評論,學生在觀看教師視頻時,可能會被其他平臺推送的內容分散注意力。有鑒于此,教師最好將視頻嵌入課程管理系統,讓學生在學習平臺上直接播放視頻,無需離開此平臺,前往可能分散注意力的地方。
視頻多帶字幕,字幕對殘障、學習困難、外語學習者等群體很必要,故而在美國,有相關法律要求視頻提供字幕。但對其他學生來說,字幕在有些情況下會形成干擾。奧茲邁爾等(Ozdemir,2016)采用混合方法開展實驗研究,了解字幕的使用是否會干擾由多個渠道傳遞的同一條消息而造成的冗余效應而干擾學習和學生的動機。研究人員在土耳其一所大學將109名二年級學生隨機分配給使用字幕的小組和不使用字幕的小組。觀看視頻后,研究人員對兩組進行成績測試和調查。研究人員發現,兩組學生在成就和動機上沒有顯著差異。該研究的定性分析結果好壞參半:有些學生評論說字幕分散注意力,有些學生覺得看字幕更清楚,還有學生發現,缺少字幕可能會理解混淆,但多看幾次視頻就可以解決。根據媒體使用的信息冗余原理,同時加載視頻和內容同樣的文字,會導致冗余,影響信息接收效果(Mayer, 2009)。針對這個問題,建議添加可隱藏式字幕,讓學生自己選擇是否打開字幕選項。
(八)使用反饋分類元素
屏播反饋內容需組合多種要素,包括認知、情感和總體評價方面的要素。筆者在畢業論文中(Fang,2019)。訪談了多位教授,并瀏覽他們的屏播評論,了解他們在反饋中包括哪些成分。結果發現,教師至少使用了三類反饋信息:1)關注學生理解認知的認知類信息;2)關注學生情感反應的情感類信息;以及3)總體反饋。在這些類別中又有更細致的內容(見表一)。在屏播反饋中,有意識地加入這些元素,可增加反饋的可接受程度,改進反饋對學習的效果。建議教師考慮使用這些元素,并適當加以補充,讓反饋變得更有效,真正做到利用個體化反饋,促成因材施教。

表一 反饋分類
七、結 語
新冠病毒的全球流行,使人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接觸網課教學,從根本上改變了教育的格局。一些研究人員甚至認為,疫情正在加速大學教育的普及化,通過技術將學生與教師聯系起來,再將學生與學生聯系起來(Grange,2020)。在建立師生互動方面,屏播反饋可以打破網課教學的一個常見瓶頸,解放老師的生產力。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小班教學是少數,老師常帶很多學生,批改作業任務繁重,有時候老師會寄希望于家長幫忙,造成諸多社會矛盾。希望教育界拓展教育手段的創新,在考慮學生需求的同時,也能兼顧老師的難處。屏播反饋潛力巨大,如果使用得當,可以節省老師時間,且讓反饋更顆粒化、個性化,連通教與學中的毛細血管,繼而實現教學“優步化”:讓有需求的學生,和有提供能力的教學者有效銜接起來,如同互聯網+ 促成的搭車、外賣等服務一樣。